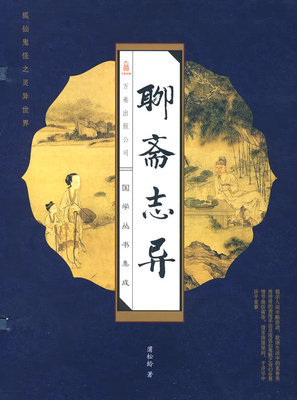科举制度为儒生们提供了步入上层的机遇,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界限,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然明清以降,以八股取士,内容限于《四书》、《五经》,程式拘于八股,科举的落后性已暴露无遗。《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都对之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露和鞭挞。从此切入,笔者比较了两作对八股科举看法的异同,审视八股科举的毒害及文人的逐步觉醒。
首先,从手法来看,《儒林外史》侧重讽刺。作者通过对形形色色的读书人的描写,指出了科举的虚伪性、残酷性、使人堕落性。作者虽把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但还是有着非常浓厚的当时社会的痕迹,虽非常夸张的讽刺了热衷科举的读书人的虚伪和无耻,但于夸张中透着写实,书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作者在原型的基础上集中提炼,使之成为典型,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仅周进、范进的形象就写尽了天下儒人的辛酸血泪。这种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使得对科举的批判更深刻更彻底,在现实和夸张之间把科举制的种种伪装统统撕破,把它的虚伪、无耻、腐败赤裸裸的暴露在我们的视野之中,从理论到实践都否定了科举存在的合理性。
而《聊斋志异》则是“以传奇手法志怪”。作者通过许多被科举制折磨而死的鬼魂形象,曲折地反映现实,对科举的不合理和摧残人才发出悲愤的控诉,这类故事往往人鬼混杂,阴阳交错。作者大量借用民间故事,写鬼写狐,想象奇特,以神怪幻异的手法写出了大量的讽喻现实的作品。这类人鬼混杂的故事构筑了一个既阴风阵阵又诗意浓郁的神话世界,把神怪幻想和现实人生巧妙结合起来,造成许多亦幻亦真的形象和画面。像叶生死后阴魂不散,不仅教恩人之子使其高中,而且自己也高中进士,直至回家看见自己的灵柩才明白自己已死去多年。这类故事使得整个作品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时于写鬼写神之间对社会弊端进行了批判,很有寓言的特点。尽管其中也有些作品使用了讽刺手法,比如《司文郎》,但是,《司文郎》中的那个靠鼻嗅文章灰烬来分辨文章优劣的瞎和尚本身就带有明显的传奇色彩。
其次,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各有其不同的深度和广度。《聊斋志异》主要揭露科举的弊端,特别是对科场的黑幕,主持考试的试官的无能和不公尤为愤激,攻击的火力很猛;由于作者长期受害,体验极深,有着切肤之痛,因而这方面的描写又是很深刻的。对受科举之害的知识分子心理状态的刻划也很见功力。比如《司文郎》即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它写一个盲僧有一种奇特的本领,他用鼻子一闻,就能准确地评判出文章的优劣。他闻了王平子的文章表示首肯,结果却名落孙山;余杭生的文章使他闻了作呕,但却偏偏高中了。他听了以后不禁大为感叹说:“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辛辣地指出这些试官不仅是瞎子,而且丧失了嗅觉能力,怎能分辨得出香臭美恶?对于这种“聋僮署篆,文运所以颠倒”的不合理的现实,作者极为愤慨,因而以嘻笑怒骂之笔,痛加挞伐。在《何仙》中,作者揭露了学使所想的全不在文章,一切付置幕客,这些人“前世全无根气,大半饿鬼道中游魂,乞食于四方者也。曾在黑暗狱中八百年,损其目之精气,如人久在洞中,乍出,则天地异色,无正明也。”由这样的人来衡文,又哪里还有公道可言?就是试官们本身又何尝高明?在《于去恶》中,鬼魂于去恶数说阴间“得志诸公,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门既开,则弃去;再司簿书十数年,即文学士,胸中尚有耶!”这岂不是为现实当中那些试官写照?而把八股文比作猎取功名的“敲门砖”,又是何等确切!不难想象,由这些人来主持考试,评定试卷,出现“英雄失志,而陋劣幸进”的现象,又何足为奇?在《三生》中,作者更借兴于唐执试卷去阴间呜冤的故事,痛快淋漓地抨击“黜佳士而进凡庸”的试官和主试官都是些见识鄙陋、有眼无珠的人,不知屈杀了多少士子,只有抠他们的眼睛,挖他们的心,才能消除人们心头之恨!
《儒林外史》则通过名式人物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态度,重点揭露科举对知识分子的腐蚀和残害以及它毒化整个社会风气之深;它所旁及的科举制度造就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科举制度孳生出大批社会渣滓和寄生虫以及对八股制艺本身的抨击等都是《聊斋志异》没有或很少涉及到的。例如,小说揭示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贪官污吏、士豪劣绅,象南昌府太守王惠,到任以后探询的第一件事就是搜刮钱财的窍门,他衙门里响的三种声音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像这样残暴贪墨的赃官,却受到上司的赏识擢拔,居然被誉为江西第一能员。高要县知县汤奉每年额外剥削所得就不下万金,饱了私囊不算,还要博一个为官清廉的好名声,以致枷死回民老师父,引起回民鸣锣罢市,他却逍遥法外,照样当他的知县。地方上充斥着这样的“父母官”,整个吏治可想而知。至于各级衙门里的走狗、爪牙,上行下效,狐假虎威,敲诈勒索,无所不为,那就更不用说了。与地方官吏勾结在一起的,还有为非作歹,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举人出身、做过一任知县的张静斋就是一个欺压佃户、巧取豪夺的地头蛇。高要县的贡生严致中更是劣迹昭彰,强关邻居的猪,强索别人并未借过本银的利息,把几片吃剩的云片糕硬说成是十分贵重的治头晕病的特效药蓄意讹诈船家以及霸占二房的产业等等,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充分暴露了这个所谓“衣冠中人”撒泼放刁、横行霸道的丑恶面目。又如,小说还描写了大批科举制度孳生出来的纨绔子弟、斗方名士、清客帮闲,流氓无赖。湖州娄中堂的儿子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因为科名蹭蹬,牢骚满腹,空疏无聊,自命风流,搜罗的那一帮门客都是像杨执中这样的假名士,权勿用这样的假高人,张铁臂这样的假侠客,结果如其表侄遽公孙所说:“半世豪举,落得一场扫兴。”杭州胡尚书的儿子胡三公子是个秀才,更是俗不可耐,家里广有钱财,却悭吝成性,生来又有钱癖,妄想学点金术,差点受骗上了大当。他所结交的景兰江、浦墨卿、支剑峰之流,会诌几句半通不通的歪诗,假托无意功名,成天拈韵赋诗,附庸风雅,居然都自命为西湖诗会的名士。实际上这些人多半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追名逐利,帮闲凑趣,他们是当时社会的渣滓和寄生虫,也是科举制度的副产品。作者的笔宛如一支游刃有余的锋利的解剖刀,伸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通过所有这些牛头马面,魑魅魍魉的形象描写,为我们勾勒出封建末世千奇百怪的巨幅图画。因而就反科举八股的内容而言,《儒林外史》显然要广阔得多(注:聂绀弩同志在《〈聊斋志异〉三论》一文中论及《聊斋》反科举制度的成就时指出:“以致可以说,《聊斋》里面有一部《儒林外史》,甚至可以说,某些地方,连《儒林外史》也不及它的痛切。”笔者同意这话的后一半,即《聊斋》反科举确有其独到之处和予人以创巨痛深之感;但《儒林外史》反映的幅度更广,这又不是《聊斋》所能包括得了的。聂文引见《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这固然因为两者的体制、创作意图、允许作者驰骋笔力的天地有别,同时也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条件和肩负的任务的不同。
第三,两者对科举的态度不同,它昭示读者从中获取的结论也有不同。《聊斋志异》揭露科举考试的积弊和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很深,但作者并没有把它归咎于科举制度本身;相反,如果革除了这些流弊,主持考试的试官遴选得当,能够识拔真才,那就不仅不用反对,而且是应该举双手加以拥护的了,《聊斋志异》中描写了一些知识分子得以从此途进身,扬眉吐气,飞黄腾达,正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它反映了作者认识上的矛盾和思想上庸俗的一面。《儒林外史》则在小说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提出:“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对八股取士制度本身提出了根本性的怀疑和否定的见解,这一观点笼罩全书,读者也不难从小说的艺术描写中得出与作者观点相一致的结论。尽管由于时代的限制,作者还不可能认识到科举产生的社会根源,当然更不可能怀疑到整个封建制度;他所标榜的“文行出处”也不能帮助他真正找到出路。但他的这种见解和勇气无疑要比《聊斋志异》奋进了一大步,而与前辈民主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同轨合辙。
《聊斋》是作者怀着一腔悲愤通过花妖狐魅等神秘荒诞化的表现手法,矛头直指考官的不公不明,以当局者的身份热腔骂世,在感性层面上进行了直接的显现。《儒林外史》则取材于现实士林,以白描的手法描摹原生态的生活,塑造了形形色色被八股科举所异化、所扭曲了的人物,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吃人的本质,是一部以局外人的姿态远距离审视这一制度的理性醒世之作。因此,《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无论是艺术性和社会性,都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尤其是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对后世文学有着很大的影响,使得科举制在人们的心中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是批判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是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崔宏伟,哈尔滨师范大学2007级古代文学高师班研究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