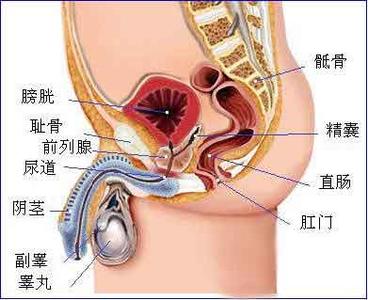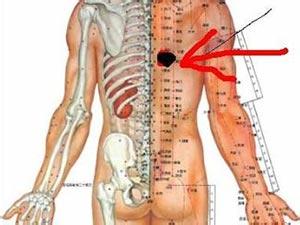哥的事判下来三天后,躺在床上的娘才起来勉强喝了点粥,娘喊:“顺子,咱家有烛台吗?”
“娘,这都啥年代了,家里还有烛台?”
“没有?那我就去买。” 娘说着就摸摸索索下了床。
“娘,要烛台做什么?要买也得我去买呀,你就在家歇着。”可娘说这烛台一定得她去买,她说只有虔诚才能感动老天。
娘是一步一颤地走到街上卖烛台店的:“我买三个烛台,一百根香烛。”我远远地跟在娘的身后,七十多的人了又有高血压的病,我怕娘有个什么闪失。

娘刚走开,店里的人就说:“作孽呀,她的大儿子犯职务侵占罪,坐了大牢,这是买了香火要请老天恕罪呢。”
娘是最怕人在背后戳脊梁骨的,她肯定听到了店里人说的话,怔怔地站在那儿,身子颤抖得厉害,眼见着就要倒下,我急忙跑过去把娘扶住。
当天晚上,娘就在院子的中央摆上三个烛台,插上香烛,虔诚地跪到了地上。
北方三月的夜,依然寒冷刺骨,到了深夜,更是在零下几十度。
娘跪在冰冷的地上,身子被冻得簌簌发抖,看娘依然颤抖着双手合十,虔诚地祈求:“老天呀。保佑我的儿子早点归来吧,保佑我的儿子早点归来吧。”
夜越来越深了,寒气袭人,我劝娘快点回屋,可娘就是不肯,她说:“不能因为自己的不虔诚冲撞了无所不在的神祗,影响你哥早点归来。”
娘要起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她叫我:“顺子,扶娘起来吧。”
我从地上拉起一直簌簌发抖的娘:“快进屋吧,天寒地冻的,娘。”说着就搀扶着她走进里屋,快到床前时,我刚一松手,娘一个踉跄坐在了地上。
我赶紧又把娘扶起来,扶她坐在炕上。
娘在寒冷的夜里整整跪了五个小时,五个小时啊,真想不出她的膝盖会是怎样:“娘,我看看你的腿。”
娘说没什么,只说有点累,可娘说着话时就把裤腿扯过了膝盖。
“娘,还说没什么,你看都开始红肿了。”我用手一摁,肿起的地方就变成了青紫色,半天都弹不起来。
连日的夜里,温度几乎都在零下几十度,但冷对娘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她每天晚上都这样跪在院子中央跪拜着: “老天啊,求求你保佑我的儿子早点归来吧,求求你保佑我的儿子早点归来吧!”
但上苍似乎一直不知道娘有事求他。
“娘,今天已是第十天了,你每天夜里在院子里跪、跪、跪,求保佑,有用吗?他在牢里知道吗?”我看夜深了,就要把娘拉起来,可娘不肯,依然跪着。没有办法,我便陪娘站在院子里流眼泪,时间一久,背上着了凉,就一个劲儿地咳了起来。
我的咳嗽引起了娘的警觉,我知道,我和哥是她的天,哥犯罪进了大牢,娘感觉天就塌了一半。
“顺子,咱起吧,我不敢听你这样咳。”娘的声音里带有很明显的惊慌。我赶紧忙把娘拉起来搀进屋里。
屋里的温度让我感到温暖了很多,走到炕前,搀扶着娘的手刚准备松开,娘就仿佛失去了支撑向地上跌去:“娘,你的膝盖?”我又赶紧把娘扶住,让她慢慢坐到炕上。
“肿得越来越厉害了。”娘坐稳后,把右手反到背后,自个捶发酸的腰。
“娘,你坐着别动,我去拿冰块来。”
“娘,你看看你的膝盖,肿得比大腿还粗,再这样下去会瘫掉的。”我一边劝说着娘,一边用冰敷过娘红肿的膝盖后再轻轻地搓揉。
“顺子,娘都入土的人了,啥事儿也帮不了你们,咱只能求求老天,保佑你哥早点回来,娘不在了,只有你们哥俩相依为命,互搭个帮手。”
我听娘这么说,眼圈儿先就红了:“娘,爹走得早,你不能再这样了,顺子没了娘,你叫顺子咋活呢。”话刚说完,又大声咳起来。
这一咳又让娘急了:“好了,好了,顺子,娘就听你的,明天不去了。”娘说着就用右手轻轻拍我的背,我看娘,突然发现娘的脸很红,发烧的样子。
白天一天过去了,晚上,我给娘红肿的膝盖又用冰敷过后,一直搓揉到发热,娘一直没有再去跪祁的迹象,我因为咳嗽得厉害,自己吃了药就先睡了。
深夜,一种异样的声音把我惊醒,我一个激灵从炕上弹了起来,跳下炕,一把拽开房门,看到娘躺倒在地上,旁边烛台的香烛还在烧着,我疯了似地几步跑到娘的身边:“娘,你这是怎么了啊,娘……”
娘“头七”刚过,我在监狱的会见室见到了我哥,他比以前瘦,可精神看上去好多了。
“顺子,你戴着孝?娘呢,娘他怎么了?”听哥一问起娘,我眼泪就止不住了。哥看着我,一会儿好像明白了什么,他站起来,从桌子对面伸过手来,疯了似的抓住我的双肩,使劲摇晃着我:“真的是娘?你说,娘怎么了?”
我气急,积聚了全身的力气,将他的手掰开,歇斯底里喊道:“都是为了你,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很久,我的心情才平静下来,告诉哥说:“娘每天都在院子里跪五个多小时,祈求老天保佑你平安,膝盖跪得发肿,比大腿还粗,娘有高血压你知道的,整整跪了十天啊,结果脑溢血……”
哥已是泪流满面,很久,哥大叫一声:“娘,孩儿不孝啊!”接着,他头一低,朝面前的桌上磕去,血就从捂着的指缝中流了出来。
文/周明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