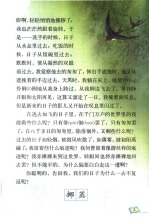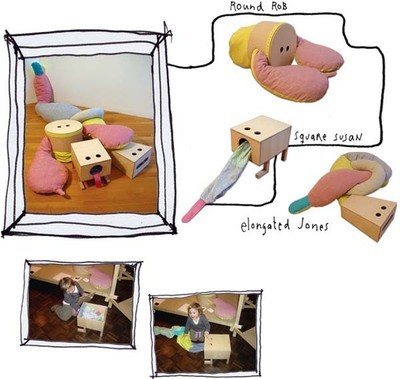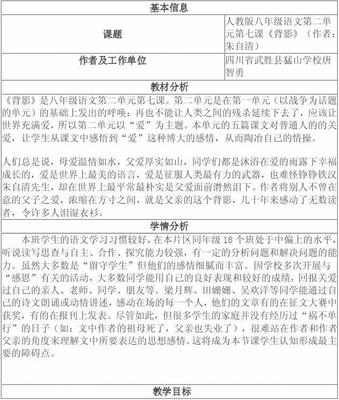白居易
不争荣耀任沉沦,日与时疏共道亲。
北省朋僚音信断,东林长老往还频。
病停夜食闲如社,慵拥朝裘暖似春。
渐老渐谙闲气味,终身不拟作忙人。
《闲意》是白居易任江州司马期间所作,描述了作者在九江期间闲适安逸的生活。在江州司马任上,白居易不仅创作了包括《琵琶行》在内的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他念佛求生净土的终极信仰。这首诗就反映了作者从一个立言建功的文人转化为一个寄身官场、栖心净土的净业行人的心路历程。
世间人所谓的幸福,用佛法的概念来解读,无非是对五欲六尘的追逐与满足。站在现世人生的角度,这种幸福观也是无可厚非的,趋吉避凶、趋乐避苦是众生本具的天性,也是我们成就“常乐我净”究竟佛果的初始动力。问题在于,由于我们凡夫德薄慧浅、知见颠倒,往往在追求幸福时做出许多背道而驰的努力,勤恳作务,到头来不是事与愿违,便是一场空欢喜。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借助佛法的智慧,对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做一个甄别。
世间之福有两种:一种称为洪福,指拥有功名富贵的幸福,世人企盼的灯红酒绿、富贵骄人的生活大多都是这种幸福;另一种称为清福,指一种平平安安、衣食无忧、恬淡安适的生活。可这两种福却很难齐聚一身,往往是洪福愈盛,烦恼越多。之所以有这样的缺憾,究其实是因为洪福是一种外在的环境和评价,而清福却是一种内在的感受和自肯。或者说,洪福的决定权来自于外部,清福的决定权却来自于内心。
南怀瑾先生在《金刚经说什么》一书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人生鸿福容易享,但是清福却不然,没有智慧的人不敢享清福。人到了晚年,本来可以享这个清福了,但多数人反而觉得痛苦,因为一旦无事可管,他就活不下去了。有许多老朋友到了享清福的时候,他硬是享死了,他害怕那个寂寞,什么事都没有了,怎么活啊!所以我常告诉青年同学们,一个人先要养成会享受寂寞,那你就差不多了,可以了解人生了,才体会到人生更高远的一层境界。这才会看到鸿福是厌烦的。”
可见,洪福很有可能只是一种痴福,洪福之福,更多的时候只是满足了面子上的虚荣,是享给别人看的。民国时上海大亨杜月笙说人生有三碗面难吃—人面、情面、场面。所谓过得好,有福,无非如此。而清福却是一种智慧,是通过对外物与自心的观察、思维与调整之后,形成的一种符合中道的和谐心态。洪福之盛,莫过于帝王之福,而清朝顺治帝却选择了弃帝位着僧袍的生活,正是因为他深切地认识到了“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
白居易在这首《闲意》诗中,描述的就是他自京都贬谪至江州司马任上时,安享清福的自在心态。江州三年,是白居易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可以说,正是在江州,他有机缘与东林寺三位上人过从甚密,这不仅抚慰了他官场失意的落寞之心,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他一生中的信仰方向—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对于一个建立了超越世俗体系目标的人来说,现世的浮沉只是一道道变换的风景,只是欣赏品味,却不能扰动内心的平静。
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四十八岁那年的春天,自江州启程赴忠州,次年夏,自忠州召还,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自此开始了他在官场上的一段顺风顺水的日子。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他确立了“终身不拟作忙人”的原则之后,可见世间的洪福,只是过去世行善的自然果报,岂是能“忙”来的,所谓“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
从追逐洪福到享受清福,这种转变是一个人阅历增长、智慧渐开后的自然过程,一位稍具思考与反省能力的老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些从容、淡泊的处事之道,这就是“渐老渐谙闲气味”的道理所在。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要有机缘接受正确的理念,也就是善知识的作用。白居易在江州的三年,远离京都那些营营作务有为法的同事朋友,与修行清净无为法的僧人密切接触,自然是尘心淡泊、道心坚固。反观我们自己,修学佛法、受持戒律,肉也不吃了,酒也不喝了,牌也不打了……在过去那些吃吃喝喝的圈子里自然成了另类,初时未获法喜,未识同修道友,在朋友的调侃乃至耻笑之中,难免郁闷、寂寞,甚至动摇道心,此时便是出尘的障碍显现之时。社交圈属于我们心所感召的依报境,当我们的心行由埋头造业转向出离轮回时,依报境自然也会随之转变,大部分朋友便会离我们而去,而新的志同道合的社交圈也会慢慢形成。此时的寂寞便是磨练我们心性的实验场,要相信德不孤,必有邻。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清福是清净之福、清静之福、清闲之福、清雅之福。享清福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懂得安闲的趣味了。六道轮转不休,其推动力就是我们内心的贪瞋痴,此生有幸遭遇佛法,先让心安闲下来,让这轮子转慢一些。“终身不拟作忙人”,这话与其说是向主流价值观宣布的诀别词,也可以说是向轮回宣示的诀别词。
清福是出世之福,洪福则是入世之福。正如南老所言:“一个学佛的人,你首先观察他有没有发起厌离心,也就是说厌烦世间的鸿福,对鸿福有厌离心,才是走向学佛之路。”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