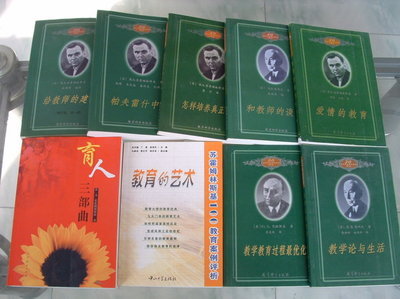《F小调第四交响曲》
第四號交響曲,被柴可夫斯基稱為「我們的交響曲」,因為這是他特別為梅克夫人所寫的。梅克夫人在這首作品中感受到強烈的舞蹈特質和情緒流洩,因此曾要求柴可夫斯基寫一份樂曲解說給她,柴可夫斯基的解說提到此曲和命運那讓人無法呼吸、無法逃於天地間的箝制有關。而同樣的,第五號交響曲也在描述命運,但卻沒有第四號那麼表面化,而是深入到潛意識的底層去了。第六號交響曲「悲愴」在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首演完九天,柴可夫斯基過世,如今我們已經可以證實,他的死因是因為與一位俄國貴族有染,而被下令自殺以避免事端擴大。而或許這三首最後交響曲,都是柴可夫斯基對自己生命終點的預言,才會這麼沉重地都以小調和命運為基調寫成。這份錄音由柯芬園皇家愛樂總監帕帕諾指揮義大利頂尖的聖西西莉亞國立音樂院管弦樂團演出(目前由他出任音樂總監)是他在零七年完成的經典,也是他少數指揮的管弦樂錄音。聖西西莉亞國立音樂院管弦樂團的弦樂部有一種非常溫暖的音色,抑制住樂曲過於煽情的傾向,而其管樂部較溫潤的音色,也適切地中和了樂曲的冷冽宿命色彩,在帕帕諾的指揮下給了柴可夫斯基這套經常被灌錄演繹的交響曲.讓人如沐春風般怡人的音樂款待。
在《第四交响曲》中,尤其是第一乐章,不仅使它成为浪漫乐派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而且也是俄罗斯作曲家第一部真正最伟大的作品。柴可夫斯基在1878年完成全曲以后,曾去信给他的赞助人梅克夫人,吐露了他原本的秘而不宣的写作计划:主题即为“命运”——“莫名的悲剧力量,阻碍了渴求快乐的心,使它无法达到目的。”这首交响曲的基本主曲鼓号曲,是非常引人注意的开场,后来又在曲中有许多重要的连接处再现,确实以音乐来再现“命运”的观念。
有了这个观念,我们便可以在第一乐章中看到一场心理剧,其中有逃避`短暂的白日梦`被命运摧毁的希望,全都以一种渐进的调性改变来凝聚并增强和声的张力。尤其特别的是,这乐章似乎是一连串尝试,想从代表命运压迫感的F小调中移开,尽量远移F调的B大调优美的圆舞曲,就是暂时的逃避。此后以F大调再现的圆舞曲,只能再回到F小调,显示所有超越困境的希望已完全破灭。
第二乐章以双簧管独奏开场,在所有的交响曲中,这是最长而且节奏没有变化的一段主题。据柴可夫斯基说,这种荒凉沉郁的况味,是要刻划寂寞和怀旧的感觉。在梦想幻灭和单调的独奏重现之前,“逃离”的主题曾一度以炽热的情感和芭蕾舞曲般的丰富达到高潮,直到梦幻消失,悲伤的独奏又再度出现。第三乐章是以拨弦方式演奏的谐谑曲,“像是当一个人已微醺`且正当精力旺盛时,脑海里掠过的许多难以捉摸的影像”,柴可夫斯基如是说:这一段如果演奏得好,微醺可以表现为欣喜,但乐曲中段开头那种无忧无虑的木管独奏,必须得到足够的刻画,再辅以反复循环的半音阶伴奏。
终乐章用了一首俄罗斯民谣:“原野上立着一棵银桦树”,当做第二主题,表现为一段令人晕眩的胜利进行曲,展现了极高的作曲技巧,而F大调(现在是乐曲本调)和F小调命运主题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音乐的尾声。作曲家也暗示,听者可以从乐章的纷乱中体会欢乐的景象,但欢乐的结尾可不是轻易达到的;命运的主题又再度出现,使此曲的主题前后一致,也给柴可夫斯基驱除心中恶魔的良机,欢乐终于以胜利的进行曲完全征服了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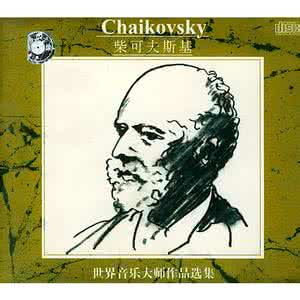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