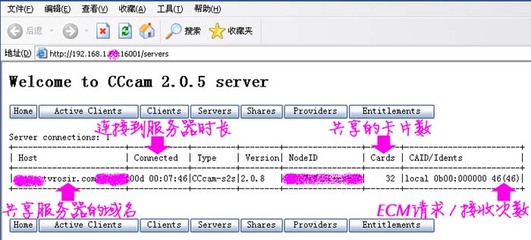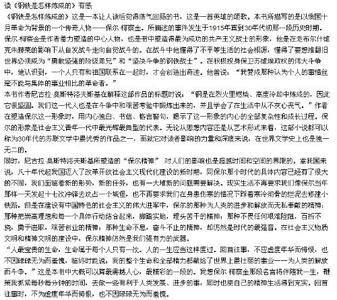人类和其他生物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人类能够使用语言沟通,甚至发展出了不同的语言、文字。那么,在进化的过程中,人类是如何学会说话的?下面爱华网网的小编带你一探究竟!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书写《人类起源》时,曾思考人类是如何学会说话的,他写道“鸟类发声在好几个方面为人类语言的发展提供了最近的类比。”达尔文认为语言可能起源于鸟鸣,这“可能产生了各种复杂情绪的言语表达。”目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以及日本东京大学的学者表示达尔文的推测是正确的。
证据表明人类语言是从动物王国里发现的两种交流形式的嫁接:鸟类的鸟鸣声,以及在其他动物种类里发现的更为实用、包含信息的表达方式。“正是这种偶然的结合触发了人类语言的发展,”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和哲学学院的语言学教授宫川茂(Shigeru Miyagawa)这样说道。
这一观点建立在宫川教授之前研究的总结上,也即人类语言具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表达”层,主要涉及句子组织的可变化性,另一个是“词汇”层,这与句子的核心内容有关。他的总结是基于其它语言学家的早期工作,包括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肯尼斯·黑尔(Kenneth Hale)和塞缪尔·杰·凯泽(Samuel Jay Keyser)。
基于对动物交流的分析,并利用宫川教授的框架,研究作者称鸟类歌唱类似于人类语句的表达层。另一方面,蜜蜂交流式的来回摇摆,或者灵长类动物简短的语音信息,则类似于词汇层。
大约5万至8万年前,人类结合了这两种表达方式形成独一无二的成熟的语言形式。“曾经存在两种先前存在的系统,就像之前是存在苹果和橘子的,只是两者恰好被放在一起。”宫川教授说道。这种现存结构的适应性在自然历史过程中非常普遍,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语言学教授罗伯特·贝里克(Robert Berwick)这样说道。“当一样新事物进化时,它往往是建构在旧事物的基础上。这种情况在进化史上并不罕见。略微改变陈旧结构就能获得根本性的新功能。”
这篇名为“人类语言层级结构的出现”的新文章是由宫川教授、贝里克教授以及动物交流方面的专家、日本东京大学生物心理学家冈上和生(Kazuo Okanoya)合作撰写的。
考虑到表达层和词汇层之间的差异,我们先来举个简单的例子,例如句子:托德看见了一只秃鹰。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产生这句话的各种变种,例如“托德什么时候看见了一只秃鹰?”这种元素的重新排列发生在表达层,使得我们能够增加复杂性并提出问题。
但词汇层仍保持不变,因为它涉及了同样的核心元素:主体“托德”,动词“看见”以及客体“秃鹰”。鸟类歌唱缺少一种词汇结构。但它们有一种美妙的音乐,这被贝里克称为“整体”结构。整首歌只有一个意思,无论是有关交配、领土占有权还是别的东西。
白腰文鸟(一种小型雀类)的歌唱能够返回之前旋律的某个部分,从而使得歌曲更多变量和更多事物的交流变为可能。夜莺能够歌唱100至200种不同的旋律。相比之下,很多其他类型的动物只有非常简单的表达方式,且没有如此强大的旋律能力。
蜜蜂能够通过视觉交流,利用精确的摇摆向同伴传达食物来源的信息;其它灵长类动物能够发出一系列声音,包含有关捕食者的警告或者其他信息。人类则结合了动物的这些系统。我们能够像蜜蜂或者灵长类动物一样交流重要信息,同时我们也像鸟类一样,具有旋律能力并能够重新结合自身语言的不同部分。正因如此,我们有限的词汇能够产生看似无限多种不同的意义。
研究人员表明,正如达尔文推测的,人类最初是学会如何唱歌,然后才试着将特定的词汇元素结合进这些歌曲里。正如文中所写,鸟类和人类语言的获得在某些方面存在“惊人的相似性”,包括人生哪个阶段是学语言的最佳时期,以及大脑哪部分与语言有关。
另一项相似性则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已经退休的著名语言学家莫里斯·哈利(Morris Halle)的见解。他观察到“所有人类语言都具有有限种重音模式,有限种节拍模式,在鸟类歌唱中也存在这样有限种节拍模式。”研究人员承认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仅仅是个假设,”贝里克教授说道,“但它能够更清楚的表达达尔文所没有表达清楚的部分,因为现在我们对语言的了解更深刻了。”宫川教授教授则表示未来将对其他物种的交流模式进行细节研究。“如果这一切被证实,那么人类语言在自然、在进化史上都是先驱。”蜜蜂、鸟类和其它灵长类动物可以作为进一步科研见解的源泉。

这篇语言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搜寻所有人类语言的普遍方面。这并不是随机的文化建构,而是基于人类与其它物种都具有的能力部分。同时,人类语言因结合了自然存在的两个独立系统而显得非常独特,这使得我们能够在有限的系统里产生无限种的语言可能性。“人类语言并非完全自由,它是基于一定的规则。”宫川教授说道。“如果我们是正确的,那么考虑到人类的自然祖先,人类的语言在能与不能方面将受到极大的约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