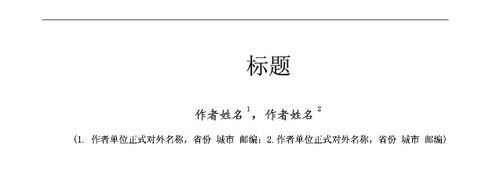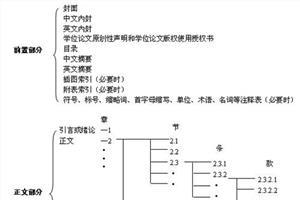《船山先生》
2015年7月11日,石头摄于岳麓书院
每次读《庖丁解牛》,总不禁想起一件小事。小时候家里吃鸡,父亲操刀,手起刀落,干净利索。有一次,父亲在不在家,奶奶替补。结果,她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准血管,在鸡脖子上反复锯了多次,仍然没有把鸡杀死。
写文章好比炒鸡,而发问如同下刀,找准血管很重要。
很多文章之所以被退稿,就是没有找准血管,即使论据再棒——如同土鸡很香,也是无的放矢。鸡都没杀死,哪里来的宫保鸡丁?
做学问,归根到底,是为了传道解惑。学术的推进与发展,其最终动力在于不断发问,那些对人类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发展,都是源于有效且持续的发问。牛顿问: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跑?爱因斯坦问:假如我追得上光速,结果会怎样?
一篇文章的立意与境界,首先体现在研究发问上。研究发问的水平与层次直接反映了作者的水平与层次。因此,每一位研究者都必须学会有效发问。
一、提一个真问题
学术灵感多如牛毛,但并非每个发问都值得深入的、系统的后续研究跟进。研究者必须对这些研究问题进行筛选,选出那些最重要的问题,继续研究。
一篇好的研究,一定建基于一个真问题。什么是真问题呢?所谓真问题,就是指它能够对应一个真实的社会疑问。
人们什么时候才有疑问呢?人们行走在路上,如果大路通天,那么,人们尽管直行即可。但是,假如有一天,人们发现,前面的路堵上了,行不通了,或者人们发现,前面有两条路,不知道哪条路更好。这时,人们就有了疑问,就需要理论来帮助人们继续前行。
苏联为什么倒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在东欧和苏联行不通了?伊万·塞勒尼(Ivan Szelenyi)的一系列研究实际上都在回答这个问题。
向左右,还是向右走?就像哈姆雷特的经典问题:To be or not to be,it is a question!要不要土地私有化?到底是要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要宏观调控多一些,还是自由放任多一些?
假如你仔细梳理学术史,你会发现,所谓的学术门派,不过是他们共同关注近似的问题,或者就某几种问题得出类似的答案。而这些问题,一定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对应着人类社会的永恒追问。
二、研究问题学术化
很多作者不太懂得学术研究与横向课题之间的区别,往往直接将课题结项书拿来投稿,结果当然很不理想。
横向课题研究提问题时,通常会非常关注现实问题,喜欢使用政策性问题作为研究发问,比如,怎么才能让“钉子户”不上访?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现实意义,但是如果放在学术语境下,这还算不上一个好的学术问题,因为它没有及时将现实问题转化为理论问题。学术研究不能停留于就事论事,而必须能够揭示一个社会因果机制。
那么,如何才能揭示一个社会因果机制呢?答案就是类型化。
学术读者不是为了听你的故事,才看你的文章,他们是为了获得一类问题的学术答案,他们还希望听听你如何解读这个故事,如何回答这个故事代表的那类问题。所以,上面的问题可以这样问:“钉子户”上访的社会动力机制是什么?
研究发问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事实层面,还要能够追问这个问题背后的类型学意义。只有通过这个类型学的考察,你的故事才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真正成为理论的“论据”。
实际上,你应该暂时搁置你的现实问题,而专注于现实问题背后的理论回答。假如你能够将这一类型的问题做一个理论性的系统回答,解决对策也就自然而然,浮出水面了。如果你已经探寻出“钉子户”上访背后的社会因果机制了,难道还不知道怎样防止他们上访吗?
三、学术发问的几个原则
第一,发问必须直抵要害。发问如杀鸡,要找对血管,一刀封喉。
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喝完酒,他找了代驾。这个朋友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公司,且已经财务自由,因此我好奇:为什么你不请一个司机,而是找代驾?
于是,他跟我讲起养一个司机的各种附带问题,包括你要处理与司机的关系,承担司机的其他支出,而且司机还不一定随时有空,等等,但是代驾不仅能够解决即时性问题,而且还没有那些额外的成本。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请代驾还是请司机的问题,实际上,这背后是一个组织与市场的选择问题:请司机是一个组织手段,而请代驾则是市场手段。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科斯(Ronald Coase),科斯精辟地指出:假如市场可以有效地解决人们的经济问题,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组织呢?就好比如说,假如你每天都可以喝到新鲜的牛奶,何必非得自己养一头奶牛呢?
威廉姆森后来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实际上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按照威廉姆斯的说法,由于有限理性、不确定性、投机性倾向和小数现象,交易双方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易成本。当市场的交易成本过大时,人们可能就会考虑市场,比如,很多大型公司会采取吞并自己的交易伙伴;而反过来,如果组织的交易成本过高的话,人们就会考虑市场外包的方式,比如,现在很多公司都采取服务外包的方式。
参考文献:Williamson,Oliver E.,Market and Hierarchies,New York:Free Press,1975。
第二,一次只问一个问题。论文与散文的区别在于:论文是高度提炼过的,必须高度聚合。一篇文章只能有一个中心,就像一个军队只能令出一门,君命甚至都可以不从。
比如,王宁:《压力化生存:“时间荒”解析》,《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这篇文章的研究问题异常凝练,翻译得通俗一点就是:时间去哪儿了?通篇文章干净利落,高度整合,一直围绕着研究发问组织行文。摘要如下:
时间荒是生活压力的一种体现,是一种令人不适的日常体验,并构成一个社会问题,但国内却鲜有关于时间荒的研究。美国学者斯戈关于时间荒的理论具有借鉴价值,但却难以充分解释中国人的时间荒的根源。有鉴于此,时间荒理论有必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加以扩展。事实上,除了斯戈所说的劳动制度和消费主义文化,中国人的时间荒还有三个根源:第一,城市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飙升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脱节;第二,制度无效率导致无效时间的大量增加;第三,中国的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使得时间荒现象成为一种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阶层为全球不平等所付出的代价。
第三,研究问题小中见大。很多作者喜欢高大全的提问方式,这样的提问方式很有抱负,也很诱人,但是却让研究难于聚焦,通常的结果就是空对空,通篇论述都悬浮在空中,并不能提出有效的社会因果机制,更不能打动读者。好的研究问题一定是能大能小、能上能下的。
比如,罗伯特·帕特南有一本经典著作《独自打保龄》。这本书的研究议题很宏大,讲美国的民主状况,但是他的研究切入却很窄,与托克维尔大相径庭。
帕特南认为,民主质量的好坏与公民社会的状况密切相关,如果一个社会的民主运作出了问题,那么,从根本上说,一定是公民社会先行出现了不良症状。帕特南独辟蹊径,通过观察人们的社区行为,比如打保龄球,来审视公民社会的状况。他发现,托克维尔当年观察到的社区生活正在逐步衰落,公民参与的热情度下降了,投票率也下降了,那些喜欢结社、过组织生活、热心公益的美国人不见了,今天的美国人不再愿意走进俱乐部从事集体生活,而是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独自打保龄,就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逝,因此,其结果就是美国人的民主参与正在日趋衰落。
参考文献:[美]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与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第四,发问要敢于质疑。学术无禁忌,一定要敢于打破常识,敢于挑战定论。只有如此,才有学术进步与理论创新。
比如,谢宇等人在2010年在ASR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质疑了人们的一个常识。人们通常认为,那些更有可能进入大学的人,读大学会获得更高的教育回报,也就是正选择(positive selection)过程。但是,谢宇等人却发现,读大学恰恰是一个负选择(negative selection)过程,也就是说,那些更不容易受到大学教育的人,其实从读大学本身获得的教育回报反而更大。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社会过程是高度选择性的,那些没有通过社会选择门槛的人,实际上反而是最需要进入大学,那些轻松迈过门槛的人,其实不读大学,照样可以有一个替代性的社会上升途径。
就拿发文章来说,那些更容易发核心期刊的作者(比如有了教授、博导头衔的作者),恰恰反而更不需要发文章,而那些发不到核心期刊的作者(比如年轻的学者、博士生),其实恰恰更需要这些文章(评职称、毕业)。
参考文献:Jennie E. Branda and Yu Xie,Who Benefits Most from College? Evidence for Negative Selection in Heterogeneous Economic Returns to Higher Educ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0,75(2) 273–302。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