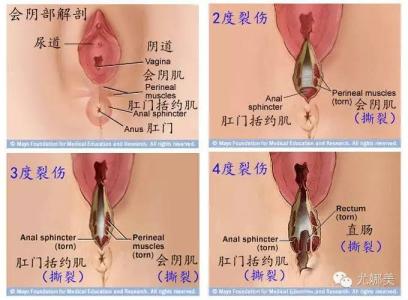年前读着名军阀冯玉祥自传《我的生活》(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年),手不释卷。姑勿论其内容是否可靠,其描述之生动、故事之曲折离奇,对军阀歷史有兴趣的朋友不可不读。
书中提到自民国成立后,冯玉祥参与剿灭起源于河南一带的「白狼起义」。白朗是当时的绿林悍匪,靠四处流窜半打半抢跟政府对抗。一般说法是,白狼是白朗这名字以讹传讹得来的,但唐德刚于《袁氏当国》(远流出版社,2002年)亦指出,白狼可能是来自「八郎」(杨家将有七郎,白狼则是某家的八郎)。无论白狼或白朗,事实是冯玉祥因为剿灭白狼有功,得到当地村民所拥戴。
固匪重民生 流匪爱私利
白狼是悍匪,冯玉祥是军阀,本质上分别不大。悍匪间中打家劫舍,军阀也要靠苛捐重税支持,好不了多少。为何村民会如此拥戴冯玉祥,却闻白狼而色变?
提出这有趣问题的学者不是史家,也不是政治学者,而是经济学家奥逊(Mancur Olson,1932-1998,其名读音如man-sa)。奥逊在政治经济学上曾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成名作是1965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今天我要介绍的不是奥逊这本成名作,而是其晚年的理论【註】。话说奥逊读到一本有关冯玉祥的英文传记,看到剿灭白狼一事,心生疑惑,不明白为何村民对两种恶霸的观感有如此大的分别。
为何村民对两种恶霸的观感有重大分别?受冯玉祥剿灭白狼一事得到啓发,奥逊的晚年都为解答问题用功。为解答问题,奥逊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为「固匪」(stationary bandit),另一为「流匪」(roving bandit)。固匪者,就如刚才提到的冯玉祥,独霸一方,有权力向村民徵税,亦有动机去赶走入侵者;流匪者,就如刚才提到的白狼,间或以暴力到处向村民抢资源,抢掠过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待下次有需要时再来抢掠。两者向村民抢掠资源的本质一样,但前者佔着一固定的地盘作为抢掠的对象,后者却是流窜式的四处抢掠。
奥逊假设两种恶霸行事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私利,但两者的掠夺行为却有重大分别。流匪的掠夺像蝗虫一样,所到之处均被抢掠一空;被抢掠的村落或许会恢復过来,但村民由于担忧不知流匪何时再来光顾,因此村民不会作太过长远的投资,以免下次再给一把火烧掉。流匪关心的只是村落有没有东西可抢,懒理村落的发展如何。
「包容利益」行为变爱民
相反,同样自私的固匪考虑的就不一样了。面对手无寸铁的村民,固匪大可把村民的所有抢个干净,抽百分之一百的税。不过,固匪这样做没有好处:若见东西就抢,村民只会消极对抗,尽量减少生产,整条村落只会落得一穷二白,固匪也就抽无可抽,和村民一同捱穷。
固匪为了私利,不会抽百分之一百的税,而是降低税率,以鼓励生产及投资。例如,把苛捐重税由百分之九十五降至九十,村民所享用到的增加了一倍,村民会因此增加生产和交易,固匪收到的税项要比在高税率时多。此外,固匪更有动机自掏腰包,给村落进行基建投资,修一下桥、建一下路,以令村民多加努力,固匪的收入就更为可观。还有,保障村民的安全,抵抗外来的侵袭,也成了这位自私的固匪的份内事。
固匪的所作所为全由私心而起,但其私心却引导出勤政爱民的行为,奥逊称之为「包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由私心而起,希望别人好令自己也好,把别人的福祉都考虑进去,是为包容也。流匪对村民没有包容利益,行为于是不一样。
除了冯玉祥,奥逊亦以罪犯作例子,解释流匪和固匪的分别。小偷在某城市行动,打家劫舍当然是抢得就抢,不会留下余地。相反,若果小偷成了某城市的黑社会头子,就不会抢得就抢了:收取有限的保护费,保障市民免受其他恶势力侵扰,好让市民安心做生意,百业兴旺,这位黑社会头子的收入将更可观。同一个自私的恶霸,在不同的局限下其行为亦随之而截然不同。

註:奥逊有关此问题的着作甚多,比较浅白的是其死后出版的《权力与繁荣》(Power and Prosperity)(由Basic Books于2000年发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