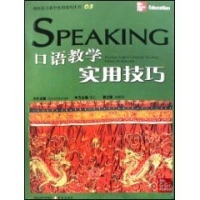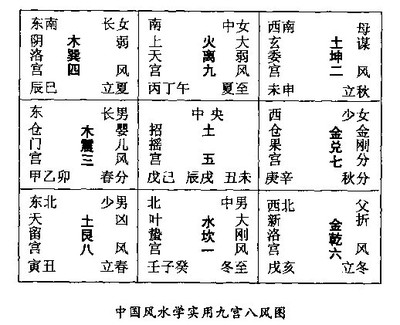Christian Northeast
“你的专业是什么?”一个美国朋友问道。我犹豫了一下,内心十分排斥这个生平最害怕被问及的问题,然后以一贯的策略笑着说:“你猜?”
在北京鼓楼附近的一个小酒吧里,布置了很多古典的家具和装饰,墙上贴着一些毛主席和红卫兵的海报,在一个镜框里放着一张文革期间的《人民日报》。一个英国朋友带我去见他的一些美国同学,那时他正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读研究生,关注的是阿富汗地区。 这些聪明的学生有着不同的专业背景,包括历史学、政治学、政府学、国际关系、东亚研究、法学,等等。于是,我们就坐在传统的中国式椅子上畅谈美国的历史和政治,在酒精的作用下不时迸发出很多思维火花。
聚会临近结束之际,我被问道了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在大多数朋友推测我学的是东亚研究之后,我非常不自信地告诉他们我的专业是英美文学。一个朋友扶了扶镜框,夸张地说:“哇哦!”所有人都用一种复杂的眼光看着我,然后我补充说是现代诗歌方向。话音刚落,另一位朋友说:“很有意思!但是这个专业的学位以后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我的父亲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那一年我大学毕业,班里的大部分同学都走上了工作岗位,我获得了保研的机会,在比较实用的国际新闻专业和英美文学之间最后选择了后者。父亲首先问我这个专业是什么,然后紧接着追问读完这个专业可以做什么。见我一时无法回答,他便安慰说读研究生也好,因为现在的就业形势不好,而且他从电视上了解到那时的应届毕业生平均工资只有三四千,便感叹说“都没有我一个农民赚得多”。
父亲的那两个问题,第一个我是可以回答的,虽然要跟他解释莎士比亚和荷马史诗会比较费力;但是第二个,我至今都无法作出回答。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害怕被问及专业是什么,因为我真正无法接招的是接踵而至的另一个问题——有什么用?我可以理解父亲的初衷,毕竟他是个做生意的人,难免用他熟悉的生意经来考量我的人生选择,但是当精英学校的学子也提出类似的问题时,我不免对当下盛行的这种用“实用主义”,或曰“功利主义”的角度去衡量大学教育的现象而感到担忧。
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孤独。哥伦比亚大学的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教授于2012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大学教育的著作——《大学的过去、现在和应有的未来》(College: What It Was, Is, and Should Be),指出在学费上涨和毕业后就业前景渺茫成反比的现实下,家长、学生和社会越来越倾向于把教育当做一件“关乎盈亏的事”。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前不久公布了关注度很高的本年度美国大学排名,虽然这些五花八门的排名很难真实反映一个学校的状况,可是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为家长和学生在择校时提供了一个参考。但这种基于名声的大学排名在几天后发布的另一个榜单面前败下阵去,由PayScale发布的“大学生工资水平排行榜”显然对承受着巨大经济负担的家长和学生来说更具现实意义。杜克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行榜中分别位列第七和第十,但两校毕业生的平均薪水水平在PayScale的榜单上只并列第44位。而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私立文理学院哈维姆德学院(Harvey Mudd College,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该校在本年度文理学院排行榜中位列第16),却以平均起薪73300美元傲居榜首。
在《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描写了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型文理学院维克森林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从开学第一天就开始让家长和学生知道他们是如何重视以就业导向的方针在教育中的位置,使得很多家长坚信他们的孩子在这所学校就读可以拥有一个稳定的未来,在他们心中这是一所“最伟大的学校”。
反观自身,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一个“伟大”的学校。当中国诸多高校的英语学院正在大力发展商务英语、同声传译、教学法、翻译专业硕士等能与就业挂钩的专业方向时,我的精神导师却在敦促我读古希腊语和英文对照的《神曲》和《伊利亚特》,他时时刻刻向我强调这些经典作品永恒的美,但从未敦促我考虑当下的就业之急。
而我曾任教的美国威廉玛丽学院(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虽然也关注学生的就业,但其无疑更为重视建校320年来一直坚守的“博雅”(liberal arts)本科教育,该校师生比例只有1:12,大学期间学生需要在文理学院的七大领域内修满足够的学分。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今年公布的榜单中,威廉玛丽学院在“重视本科教育” 一项跻身前三,仅次于达特茅斯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在公立学校中排名首位。看上去很不错?可是如果我告诉你在PayScale的榜单中其应届毕业生的平均工资水平排名97的话,作为家长的你也许在帮助孩子选择高校时也会有所犹豫。
博雅教育(在中国大陆通常译作“通识教育”)源自古希腊及古罗马时期,旨在教育“自由”的个体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参与到公民生活之中。在西方历史的长河中,大学的任务从最初与宗教相关的道德教育逐渐发展到现代基于知识层面的智性教育,同时也肩负着帮助学生培养社会责任感的使命,但到如今则偏向了明显的实用主义教育。 很多人衡量一所大学和大学教育的标杆已不再是学生在大学里学到了什么,而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可量化的问题——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薪水是多少?

博雅教育最初的名字是artes liberals(拉丁文),其词根“liber”承载着大学教育的核心任务之一——自由,帮助自由的个体获得自由的思想。德尔班科教授在他的书中一语道破:“大学存在的伟大目标之一,不是给学生准备工作,而是让他们在走上社会之前在思想上做好准备” 。“做好准备”具体来说包括具备“从看似独立的现象中找到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从另一个角度看待问题”的能力,以及“培养一种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感”。
复旦大学是中国大陆率先推行“通识教育”改革的高校之一,要求学生在文史经典、哲学批判、自然科学、生态环境和艺术审美等六大领域中从每个领域至少选修一门课程以达到12个总学分(共六门课)的要求,在这六大学科领域中共有近180门核心课程可供学生选择。这样的课程设计目的在于使学生的知识框架更趋完整,以“借鉴国际先进的本科生培养经验”。每个领域至少选修一门课的标准当然难以改变中国文理分科过早导致学生知识结构不平衡的局面,但复旦大学在这方面的努力却值得其他高校借鉴,正如该校一位参与通识教育课程设计的老师所言,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已经是中国高校关于核心课程要求的最高学分了”。杨玉良校长今年九月在开学典礼上自豪地告诉大一新生,复旦大学的教育理念是“博雅教育”,最大的特点在于人文情怀的培养和熏陶,“大学更重要的实际上就是教育你、教你具有巨大普世性的这样一种知识……拥有相当高尚的品德,能够引领社会走向美好”,以帮助学生孕育“自由意识”。
这种所谓的“国际先进本科生培养经验”即美国高校普遍采用的GERs 系统(General Education Requirements),每个学校在具体的课程设置和要求上大同小异,但正是其中的“小异”体现出了各个学校对待“博雅”本科教育的不同态度。因为高校在通识课程方面的投入越大,意味着在更具有实用主义的课程方面的投入可能会越少。
以威廉玛丽学院为例,其文理学院设置了GER1-7七个不同领域的学科,分别包括数学与量化推理、自然科学(物理、生物)、社会科学、世界文化及历史(欧洲传统、非欧洲传统、跨文化问题)、文学与艺术史、创造性艺术与表演艺术、哲学宗教和社会理论思潮。学生除了需要在自然科学和世界历史两个学科各选修两门和三门课程之外,还需在其他五个领域分别至少选修一门课,以满足所修GER课程超过54个总学分。正是其强度之大、要求之严苛成就了该校在本科博雅教育方面的良好声誉。其文理学院在官方文件中指出,这样的课程设置旨在帮助学生“培养自我审视的习惯、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想象,以及道德自觉”,同时“教会学生用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在这一点上,威廉玛丽学院的努力正好与德尔班科教授倡导的“让学生在思想上做好准备”不谋而合。
然而,这种理想化的教育模式来之不易,摆在美国众多高校面前最现实的问题就是高校的财政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学费的上涨和奖助学金惠及面的减少。近年来政府对高校的财政补贴逐年减少,这对于公立高校来说无疑是严重的打击。在这一困境之中,诸多公立高校不得不通过调整课程设置以及教职安排来应对预算的缩水。对于很多注重博雅教育的公立大学来说,维持现有的大量核心课程本已不易,在资金紧缺、教师岗位缩减的情况下学校不得不通过增加班级学生人数、聘请薪水更低的兼职教师代课等措施来应对,但这些举措都将危及到博雅教育的核心特征:小班授课、注重讨论、教授亲自教学等等。如果博雅教育的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很多学生和家长就会开始怀疑每年投资如此多学费的价值所在,转而投向更为实用且廉价的技术性学校。
社区大学以及其他技术类学校也并不是赢家。据加利福尼亚州一所独立公共政策研究所PPIC的研究表明,从2007年至2012年,加州政府对州内社区大学缩减的预算总计15亿美元,全职教师职位的减少导致了班级规模的扩大,从而导致教学质量无法保证。从2008年开始,这些社区大学的课程减少了21%,而暑期课程竟减少了60%。在美国,社区大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往往能为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提供一个继续接受教育和过渡到精英大学的机会,然而虽然加州的高中生毕业人数上升了9%,社区大学的招生率却下降了5%。在参与调查的超过100所社区大学中,77%的负责人表示州政府缩减财政补贴对学生的学术方面有着直接的负面影响。
公立大学中的精英大学也同样面临这种困境。在威廉玛丽学院公布的历年经费预算中,州政府财政补贴所占的比例从2000年的27.8%跌至2012年的12.8%,而在今年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关于“财政来源”一项的排名中,威廉玛丽学院排在114名,与其综合排名32名相差82名,这也是美国前50名的高校中教学质量排名与财政资源排名偏差最大的一所学校。“正如这些排名所体现的那样,在财政相对紧张的形势下,威廉玛丽学院在教学质量方面还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威廉玛丽学院校长泰勒·瑞福里(Taylor Reveley)说。
但并非所有的高校都能如此从容应对。在州政府财政补贴缩减的情况下,为了保持原有的教学质量,众多高校不得不通过提高学费等策略来应对这一难题。但学费仅仅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可见因素,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教育系统中,还有很多不被注意的重要方面已经或正在进行巨大的改变。
在研究型高校,领导层与教授都清楚地知道热情地投入到博雅教育并不能为学校带来实质性的利益收入,因此一方面本科教育被淡化,另一方面众多有经验的教授不愿在一线为本科生讲课。在课堂内,那些原本被一致认为可以帮助学生开放思维和塑造品性的基于西方传统的科目已经很少出现在高校的必修课之列。甚至在很多高校的英语学院,古希腊文学已鲜有人问津。而那些不再使用的“死语言”(古希腊语、拉丁语、古希伯来语),尽管仍是很重要的学术语言,事实上正在“死”去。普林斯顿大学的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教授在文章中援引德尔班科教授的观点,指出即使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这样的顶尖学府,虽然那些传统科目还是必修课程,但是这些课大多由年轻老师或者博士研究生授课,只因他们较为容易“被安排”去教这些课程。而这些年轻的教授又“十分期待从这类教学工作中得到解脱”,因为他们“既没有接受过训练也没有什么品味”。
1954年,著名小说家、批评家C.S.刘易斯(C. S. Lewis)曾说,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如果在某个世纪会一个儿子读不懂他父亲书架上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那么这个世纪最有可能就是20世纪。而到了21世纪,那个家庭的孙儿估计连维吉尔是谁都不知道。未料刘易斯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对于家长来说,把高等教育与昂贵的学费和将来孩子毕业后的薪水挂钩就等于把上大学和投资画了等号。在孩子高中毕业选择大学的时候,一般的家长都会建议选择州内的高校,原因很简单,州内高校对本州的学生有优惠政策,学费与州外和国际学生比较将近便宜一半。我的一位学生曾被康奈尔大学录取,但由于昂贵的学费最终在家长的建议下选择了为其提供四年全额奖学金的威廉玛丽学院。一位美国学生曾多次向我表示对汉语和中国研究很感兴趣,很想在暑假的时候选修汉语课,然而其父亲在得知一门课的学费需要四千美元时果断表示不支持,理由是因为他的孩子已经学了一年的日语,他认为再重头去学两年中文对毕业并无好处。在很多家长看来,学校的关键任务不是在道德、智性和责任上的培养,而是能让自己的孩子顺利入学、顺利毕业,以及毕业后找一份薪水高的作业。只要在这方面得到满足,家长会乐意掏钱支持自己的孩子去某个学校,也会自然而然地像文章之前提到的家长一样认为威克森林大学是“最伟大的学校”。
当然,家长的这种实用主义心态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其实由来已久。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在早期很多移民家庭并不具备为其子女提供大学教育的经济条件,这一现象即使今天在某些低收入家庭也依然存在。由于就业所需,进入以工作为导向的职业学校自然成了诸多移民子女的首选。而博雅教育,似乎只是中产阶级的一种特权和象征。但是在近几十年来,这种心态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缓解,反而有抬头之势。密歇根大学玛莎·贝利(Martha Bailey)教授和苏珊·迪纳斯基(Susan Dynarski)教授2011年的研究成果表明,父母收入与孩子上大学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低收入家庭的父母越来越倾向于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去影响孩子做出人生的选择。
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正是实用主义大学教育最大的受害者。据一份由斯坦福大学卡罗琳·霍斯比(Caroline M. Hoxby)教授和哈佛大学克里斯托弗·艾弗里(Christopher Avery)教授共同得出的研究报告显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大学升学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只有34%申请了全国238所具有竞争力的大学,而同等学习水平的高收入家庭的孩子这一比例却有78%。那些高分贫困生要么选择去社区大学,要么去就近的一所学费较低的高校, 他们很多甚至都从来没想过去申请精英学校。至于该校是否与其成绩和兴趣匹配,常常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
在理论上,精英学校常常标榜要保持博雅教育,要面向更“多样化”的学生群体,而从大学的招生政策来看似乎也能让更多的贫困学生被录取,但现实并非如此。通常情况下,政策都带有理想的成分,现实的情况是更多的富裕家庭的孩子被录取,而更少的贫困学生进入到顶尖的精英学校,这种趋势将会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如上文所言,博雅教育在美国的历史中反映着中产阶级的特权,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要成为中产阶级彼岸的一员,就必须先购买“博雅教育”这张船票。但由于政府补贴的减少,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更加难以获得政府原本可以提供的奖助学金来完成学业。因此,越来越多的学生只能通过借钱来进入大学。而对于那些不愿意通过借钱来买船票的家庭来说,便在很大程度上错过了进入中产阶级的机会。据报道,哈佛大学商学院中存在的阶级问题远远大于备受关注的性别问题,富裕家庭的学生往往在精英学校占据重要的位置。由此可见,当今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在促进阶级流动方面发挥应该有的作用。
这样一种充斥实用主义的高等教育一方面没有推动社会公平,而另一方面又极大地阻碍了博雅教育的良性发展,偏离了大学真正要义。在19世纪末以前,我们的大学教育还是注重“form”(塑造学生的品格和个性),并兼顾“inform”(教授知识、启发智性),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谦卑感。但是如今的大学,特别是本科教育,过分注重专业化和实用性,而缺少关注学生的思想启迪和品性培养。
前不久,一位在中国任教的美国朋友跟我分享了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故事。他去参加普林斯顿大学在北京的一个招待会,遇到了一位中国高三学生在会场做志愿者拍摄照片。这位男生表示特别想去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去年已经申请过一次但不幸被拒,他因此没有去上别的高校又花了一年时间准备今年再度申请。我的朋友问他为什么这么想去普林斯顿大学,这位男生回答说,“因为我想去那接受最好的本科博雅教育,使自己达到全面发展。”对于一个中国学生来说,要摆脱名牌大学这一标签实属不易,但他自身对博雅教育的憧憬和理解则更值得我们关注。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都抱着一颗纯粹的心去追求最优秀的大学教育以使自己做一个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个人,至少我在这位高中生身上看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
爱默生在其1834年4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一个老师的真正力量在于坚信人是可以转变的。而且事实上真的可以。他们需要觉醒。”本科期间正是学生被唤醒的最佳时期,博雅教育到目前为止仍是让学生在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最为可行且有效的方式,因为它不是通过告诉学生“你需要思考什么”去唤醒他们,而是教会学生怎么去思考、怎么用批判性思维去看待一个问题,让学生自我觉醒并激励他们不懈地追求真理。在这样一种光荣的使命面前,所有的教育管理者和教授们都应当坚定地让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淡出大学教育。
硕士一年级的时候,我曾去IBM实习,为了尝试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学习一些商业意识,可以更好地了解我父亲看问题的角度,也可以更好地了解我自己。我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专业而放弃这次在一个国际IT公司学习项目管理的机会,经过几轮面试之后我终于见到了部门经理,这是我必须要过的最后一关的面试。这位台湾裔的美国女士并没有问我诸如“你的专业是文学,为什么要来一个IT公司实习”这类问题,她亲切地招呼我坐下,用英文和我谈了很多校园生活,然后告诉我她女儿也喜欢文学,大学期间看了很多小说。她问我为什么热衷于诗歌,我回答说因为诗歌不仅可以给你创造一个想象,而且可以促使你超脱这个想象以收获一种新的关于美感的体验。她看着我,似乎在期待一个更为简单的答案。于是我补充说:“诗歌于我就如IBM于这个世界。诗歌给我带来想象和智慧;而IBM这100年来也同样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无限的想象,创造了一个更为‘智慧的地球’(IBM的核心战略理念)。”于是,我得到了这份实习工作。
找工作真的那么难吗?还是你,没有“做好思想上的准备”?还是你,没有“觉醒”?
六木曾在美国威廉玛丽学院任教,现居北京,是自由撰稿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