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医家记写医案是选择性记录,记难不记易、记变不记常。我们看不到所选医案代表的“总体”,只能看到“样本”,这些样本又不是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的,而是选择性记录和保留的,因而不可能真实反映“总体”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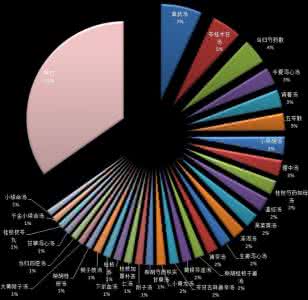
中医医案,在古代又称诊籍、脉案、方案或病案,它是古代医生临证实践的记录,客观地记录医生诊病中辨证论治和处方用药的过程,是我国历代医家临床经验的结晶。中医医案是传承历代医家学术思想和经验理论的重要载体,认真研读医案,可以探究医家辨证施治、遣方用药的治病经验,把握名家的治病思想,开启诊病的思路,也可以从医案中借鉴成功经验,汲取失败教训,提高中医学术水准。因此,当代中医大家都很重视中医病案的学习。
但是,古代医家记写医案是选择性记录,往往喜欢选择记写复杂多变的病情,常规病情则不太收录。因此,古代医案不是基本医理和常规诊疗的教科书,我们在研读古代医案时,主要也是从中学习复杂病情下古人如何辨证施治。把古代医案简单地混同于现代病历作数据研究,是一种错误的选择。
举一个实例:一位硕士研究生在作他的学位论文报告,他的论文是关于某本古代医案专著中血证(论文中指称各种出血病)的研究。研究者对书中各类出血病人的病情作了分析,并作了简单的数据统计分析。结论是:在该书中出现的血证病人,以虚寒性出血病人为多。学中医的人都知道,通常出血病人以实热性出血为多。作者的统计结果与这个常规情况显然不相一致。但作者对这个数据的意义没有作说明。作为答辩老师,我现场提问:“这个数据统计结果意义是什么?是否意味着在这本书或这批病案相对应的历史时期中,出血病人都是虚寒性出血为多?”作者对此显然毫无思考,一时语塞。
对古代医案“数据挖掘”易入歧途
事实上,近年来中医界研究古代医案者颇多。除了用简单统计方法计算出百分比外,还有对古代医案作“数据挖掘”的,有时选择一个对象范围,套用一些挖掘方法或公式,挖掘出一些关联,论文就写成了。遗憾的是,这种研究方法很容易走上歧途。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要回顾一下古代医案是如何形成的。
古代,医生属百工之一,也就是说,医生和其他各个行业的从业者一样,都只是一个社会行当而已。这些行当在履行行业职能时,只要做好日常工作就可以了。作为各种行当之一,医生在从事自己的行当时,也没有任何自我的或社会的特別要求,为自己日常的基本工作书写记录性质的医案。依照这个道理,医案在古代本来不一定会发生。
现在公认最早的医案,是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保留下来的淳于意二十五则医案。该传中,淳于意对于自己记写医案一事曾有解释,是因为随师学业“方适成”,老师就去世了。为了提高临证水平,淳于意在临证时就常作记录,以便事后能够与老师所传理论知识作比照。后来,汉文帝因故诏问淳于意的诊疗能力,淳于意在自己所记医案中摘抄了一部分写成奏章呈献汉文帝,这部分内容又被司马迁编入了《史记》。这样,才有了第一批医案的传世。可见,这批医案的形成与传世其实属于偶然事件。
因为不觉得有什么必要性,其后很多年,很少再有医家有意识地撰写医案。只是在史书或《千金要方》这类方书中偶有医疗案例的零星且不完整的记载。
直到宋代,这种情况才开始变化,医案记载逐步增多,医案专著应运而生。许叔微以案立名方式编著的《伤寒九十论》被公认为我国第一部医案专著。作者选择自己临证治疗的90例医案,结合《内经》、《伤寒论》及自己的临证经验加以讨论评述。其医案多数记载完整,辨证准确,方药规范,疗效明显,每多新见。而比《伤寒九十论》更早问世的宋代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也附有23则医案,采用以证类案的方式分析病因病机,阐述证治方药,是为最早的专科医案。在此之后,金元时期许多医书如张子和的《儒门事亲》、李东垣的《脾胃论》和《兰室秘藏》、朱丹溪的《丹溪心法》、王好古的《阴证略例》、罗天益的《卫生宝鉴》和滑寿的《十四经发挥》等书中都附有医案。到明清两代,医家撰写医案更为流行,医案格式规范也引起了注意,医案编集的品种也呈现多样化(在个人专集之外,有多人合集,医案类编等)。可以看出,宋代以后,医家书写医案的主动意识明显增强。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