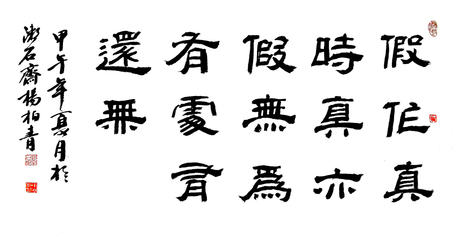张开济的建筑功能和规模各异,但都有一个特点:适宜摄影和入画。这是因为在他的图纸上,每座建筑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城市的一部分,造型不追求华丽奇特,而追求与城市的时空和谐统一。他把这种境界叫做“此处无声胜有声”。在那个崇尚敢叫日月换新天、推倒一切重来的时代,张开济的“无为”,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智慧和勇气。
为施展才华和赚钱留在新中国
1912年7月,张开济出生于上海,小时候淘气,学习不好,但非常喜欢画画,画得投入时饭都顾不上吃。中学毕业,他在书上看到,美国大学里的建筑系要学水彩画、透视画、人体写生,就下定决心学建筑。1935年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张开济在上海、南京、成都等地开办建筑事务所,业务开展顺利,但没有空间充分施展才华。“炮火连天的,谁还造房子?只有达官贵人可能造一些房子。”
1949年,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张开济有三条路可选:台湾,美国,北京。抗战胜利后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陈果夫,陈果夫很欣赏张开济,交给他不少工程,1949年赴台之前邀他一起走;张开济参加过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留美生考试,考了建筑专业第二名,也可以赴美留学。
考虑再三,张开济决定去北京。晚年接受作家祝勇访谈时,一向被老伴儿评价为“爱瞎说”的张开济,坦诚地说:“这并不是因为我多么爱国才留下来的,这个我得说实话,我是出于专业方面的考虑。我想,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建筑师大有用场,既可以施展才华,又能赚钱。”
北上途经天津时,张开济住在舅舅许丹(字季上)家里。许丹是著名佛学家,和鲁迅、梁漱溟、赵朴初等有深厚友谊。当他听说张开济想在北京开办建筑事务所,把他训了一通,说“解放了,你还想搞自己的事务所,你应该参加政府机关工作才对。”张开济这才了解新社会形势不同。他给从未谋面的梁思成写信,请他帮忙引荐。没想到梁思成马上回了信,告诉他现在北京很缺建筑师,邀他来北京一晤,这封回信张开济始终保存着。
张开济进入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当上总工程师,成为现代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建筑设计师。他在设计院安排的联谊舞会上结识未来夫人孙靖。四海漂泊只顾给别人建房子的建筑师,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家。1951年结婚时,张开济39岁,孙靖28岁。孙靖出身大户人家,辅仁大学家政系毕业,婚后独自管理所有家务并负责两个儿子的教育,张开济作了甩手掌柜,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设计上。张开济晚年总结,人一生最重要的一是事业,二是婚姻,在这两方面,我都很走运。
“四部一会”办公楼中途搁浅
1950年,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梁陈方案”,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地点选定在三里河,当年那里还是一片农田。项目规划建筑面积近九十万平方米,苏联专家选中了张开济代表北京建筑设计院提出的方案:基地分成五个区,中心区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四周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重工业部和财政部,总称“四部一会”办公楼。
在城市建设理念上,张开济与梁思成一脉相承,他是新首都大胆的设计者,更是古京城谨慎的守护者。为保护古都开阔的视野,他设计的办公楼以六至七层为主,避免过高。朴素灰砖墙,配墨绿色琉璃瓦大屋顶,既符合苏联专家推崇的“民族主义形式”,又与古城墙城楼相协调。1954年突遭变故。2月,“高饶事件”发生,国家计委领导人高岗自杀,以计委为核心的“四部一会”工程搁浅。“四部一会”办公楼刚完成西南一角,占地九万平方米,只有原计划十分之一。
这西南一角也未能按照张开济本来的设计建成。两座配楼的琉璃瓦大屋顶已建好,主楼大屋顶刚要盖时,建筑界掀起批判“大屋顶”的反浪费运动。“四部一会”办公楼成为众矢之的。据说,屋顶一只瓷鸽子压脊兽,就抵得上一辆飞鸽自行车的价钱,更不要说琉璃瓦的造价。而张开济本人又是三反五反运动中,设计部揪出的“老虎”之一,因在一次调查中,“爱好”一栏大家都写着“读毛主席著作”、“看报纸”等,他竟填了“金钱、女人、狗”,结果受到批判。可他不当回事,“打老虎”时还甩着心爱的劳力士手表玩。
李富春当时既主管“四部一会”工程,又领导反浪费运动,他只得以身作则,大义灭“顶”。已经送到顶层的琉璃瓦又搬了下来,上百只瓷鸽子也弃置一旁渐渐不知所踪,张开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检讨了自己作品中“搞复古主义的错误”。过了一段时间,“反浪费”运动高潮过去,彭真等领导看了三里河路这座大型办公楼,成了“两个道士”(带屋顶的配楼)和“一个和尚”(未盖屋顶的主楼),批评张开济没有坚持设计原则,于是张开济又检讨。
晚年提起“四部一会”工程,张开济说,“来回检讨,自相矛盾,内心痛苦,真是一言难尽!”最令他遗憾的并不是废掉一个屋顶,他相信,如果整组办公楼按计划建成,旧城内就不必再大拆大建,办公用房与古城保护问题也许可以妥善解决。
遗憾天安门广场“太大”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在全国大跃进的背景下,中央决定兴建十大建筑,为国庆十周年庆典献礼。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在9月8日的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特别说:“在设计中大家要敢想,敢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过去曾经反对过浪费,也反对过一阵大屋顶,我看这些框框可以打破,如果认为琉璃瓦大屋顶能搞出高度艺术水准也可以尝试搞大屋顶;如果有其他更好的形式,就应当去创造更好的形式。” 大屋顶又受到肯定了,说明政治气候发生变化,鼓励建筑师大胆发挥创意,尽可能把工程完成得漂亮,向那些“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人证明新中国实力。最后完成并确定为首都国庆十大建筑的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民族饭店、华侨大厦、钓鱼台国宾馆。其中革命和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由张开济主持设计。
所有工程同时破土,张开济每天奔波于天安门和玉渊潭之间。博物馆采用欧式古典立柱,与人民大会堂呼应,气势恢宏。而国宾馆则与这种风格截然相反,采用分散式的低层建筑,围绕以中国式的小桥流水、庭院游廊。张开济希望带给来宾温馨舒适的感觉。这种设计在当时并不受认可。外交部派来几名干部和张开济一同草拟设计任务书,他们经常访苏,推崇苏联建筑,要求把宾馆房间建得很大、很高,张开济据理力争,才稍稍降低了尺度。
十个规模宏大的建筑,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完成设计建造投入使用,堪称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但张开济认为,“大”既是十大建筑的成就,也是遗憾。作为天安门广场的设计者之一,他最为遗憾的,也是“大”,“大而无当”。“早期我们受苏联的建筑设计思想影响,用建筑来表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广场要大,建筑要高大,老百姓见了觉得伟大,高山仰止,望而生畏。这种设计思想是非常落后的。现代的建筑思想是以人为本,让人觉得美,有亲近感,住着也舒适,人是为主的,建筑是为人民服务的。你看看天安门广场,整个广场连个人坐的地方都没有,广场拿来干什么用,除了五年、十年一次的国庆节举行一 下活动外,平常根本没发挥作用。”他理想中的广场,应当“有坐椅、有水池、有鸽子、有植物、有无障碍设施”。
革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加上北京天文馆、北京科普展览馆,并称四大馆,是奠定张开济地位的代表作。但张开济自己常说,他最满意的不是四大馆,而是一个台——天安门观礼台。提起观礼台,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天安门有观礼台?这种表现是最令张开济得意的。设计观礼台时,建筑师们展开了方案竞赛,为了引人注目,有的把观礼台盖上琉璃瓦,和故宫配套;有的设计成金黄色,比天安门还鲜亮。“我却认为这个设计越不显眼越好。天安门城楼前本来就不应当再搞任何建筑,可是又有这种需要,怎么办呢?所以我的设计高度不超过天安门的红墙,颜色是红色,琉璃瓦绝对不用,让观礼台和天安门城楼浑然一体……这就是最大的成功。一个建筑师该当配角的就当配角,观礼台就是天安门城楼的配角。”
晚年致力于保护古城风貌
作为建筑师,张开济的人生是幸运而遗憾的,盛年之时赶上新政权建立,大兴土木,政治为他提供了一张百年不遇的巨大图纸,却又在十年后剥夺这一切。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二连三的运动使他的职业生涯过早终结。“文革”结束后,他已经将近七十岁,晚年只好致力于保护古都风貌。
张开济对老北京有特别的热爱,经常回忆自己第一次到北京的情景。1934年,他还在中央大学建筑系读书,同学们集体来北京参观学习。“火车快到东直门火车站的时候,宏伟的东南角楼进入我的眼帘。角楼上面是碧蓝的天空,下面是城墙和城楼,一队骆驼正在缓缓行进,真是好一派北国风光啊!”
在他看来,“不该拆的拆了,不该盖的盖了”,是愚蠢的悲剧。在他和老一辈同行的努力下,湖广会馆保护下来,变成戏剧中心;先农坛太岁殿变成了中国建筑博物馆;五塔寺变成了石刻博物馆。他推崇古为今用,但特别反对复古主义。九十年代北京西站建立时,张开济写信给北京市长,劝告不要在楼顶建小亭子,“千篇一律,惹人生厌”,交通建筑应该讲效率,而不是搞气派,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去世前几年,张开济呼吁:“高层建筑到处冒尖,而四合院则大片拆毁。北京乍看竟很像一个二手香港了……尽管今天北京的古都风貌已经大不如昔,我们仍应该千方百计地加以抢救,那种‘破罐破摔’的消极思想在任何时候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斯人已逝,他的作品仍然带给人美的感受,他的理念仍然给人启迪。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