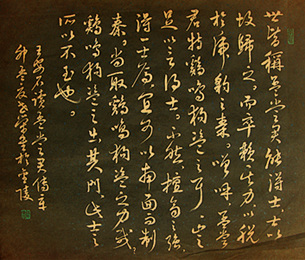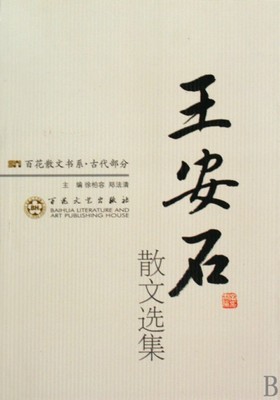内容摘要: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能够发现蕴藏在文中的真、善、美。作者传承着祖国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以极其虔诚的态度来表达其内心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性的赞美。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优美,别有特色。主要表现为雅俗并济的大白话,返朴归真、浅显直白;文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苏北水乡方言,贴近老百姓自己的生活,令人倍感亲切。同时,还有浓郁的文言色彩,清淡自然,别有情致。
关键词:小说语言 口语 方言 文言
汪曾祺就像是一阵清风在新时期的文坛上刮过,让人眼前为之一亮。许多人都喜欢汪曾祺,十分喜爱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他的小说语言如同是铺在池底的鹅卵石一般,干净清爽,十分圆润。这种语言的魅力显然和他那极富表现力的语言是分不开的。在他的文论中,谈到小说语言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他曾反复阐述:“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外部的东西,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是小说的本体,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并以这种小说语言本体论代替了五四以来的小说语言工具论。读汪曾祺的小说,不难发现他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积累,并且善于学习民间语言,同时也不乏现代意识。在他的小说语言中,最能充分体现出他的文化修养及美学追求。
诚然,作家是最讲究语言的。将汪曾祺小说中的语言称之为“诗化的语言”,不仅是因为其小说语言的优美,更重要的是其更胜人一筹的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在汪曾祺看来,美的、富有诗意的生活是丰富生活的组成部分,作家的任务就是将这个部分用自己的方式,尤其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而汪曾祺小说语言的魅力正是在于他能够用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将民间日常平凡生活中的这种美和诗意表现出来,告诉给人们生活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雅俗并济的大白话
汪曾祺从小就生活在苏北高邮水乡,这里的民风十分淳朴,在作者的眼里心底,“这一切真是一个圣境。”对于这里的一切,作者无不怀着温馨的感觉。故乡人说话的习惯、表达情感的方式、日常行为的准则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都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中,这使他的情感、气质、心灵都显示出鲜明的乡土文化特征。在他的小说中,将家乡的俚言俗语与现代白话文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又从古典文学和群众语言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错落有致、亦庄亦谐、文白杂糅的“大白话”的语言风格,这种类似于长短句的大白话,浅显直白,却又充满古典韵味,字里行间都浸透着一种淡泊超然的气韵。
汪曾祺的大白话,并非是白开水似的大白话,而是返朴归真、雅俗并济的大白话。这是与汪曾祺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深切体悟密不可分的。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语言意识,既能够建立在日常语言基础之上,又能够表现出它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性。这种大白话式的小说语言是在自发的个体语言之上的提炼与升华,他可以对众多的个性化口语、书面语言进行感知,察觉其背后的思想感情、人生经验以及对于生命的认识,并且能够把这些语言进行提炼升华,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写作风格。这种独特的语言写作是作者对日常生活的一种重现和创新,它能够比较客观地描绘日常生活世界以及个体的生存状态,但也能够创造性地融入了作者自身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小说语言世界。有人认为汪曾祺的语言为“韵白”,认为作家总是通过语言修辞来实现对世界的想象的。的确,一种语言形象的想象,也就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想象。汪曾棋小说的大白话,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凝结着现代作家认同的现代白话文形象。在这里,他的大白话,既可以看作是现代作家审美情趣的体现,也可以看成是现代作家自我想象的一种方式。
有人认为汪曾祺的这种“大白话”式的小说语言,实际上是一种“写话”式的文学语言。其实这两者是一样的。称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为“写话”,这是因为汪曾祺一直认为“照生活那样去写生活”,“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做到无意为文,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等的观点,这也是汪曾祺所坚持的美学观念。然而,他的小说语言并不仅仅是原生态的口语化语言,而是对日常语言经过必要的“发酵”之后形成的这种“写话”或“大白话”式的独特的语言风格。
《受戒》是汪曾祺的小说代表作之一,小说讲述了农家孩子明海剃度当和尚及其朦胧的爱情故事,同时也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原始淳朴的民间日常生活画面。整篇小说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繁杂的描写,也没有特别吸引人的情节,作者似乎只是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乍一看去,平淡无奇,读完之后细细品来,却又是韵味无穷。举《受戒》起头的一段为例:“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十三岁来的。这个地方的老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就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这一段看起来像是大白话,白得几乎连形容词都没有,但读起来如长短句,自有一种风情,一股韵味。开头一句提出地名叫庵赵庄。下面紧接着就有三部分来介绍这个名字的来历。但作者在句式上做了一点变化:赵,是因为……。叫做庄,可是……;庵,是因为……。句子的连接安排得十分巧妙,各部分的内容有多有少,安排得错落有致,读起来淡而有味,犹如诗词一般。
同样是在小说《受戒》中,有一段描写小英子姐妹的文字:“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这里的风俗,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这两个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通红的发根,雪白的簪子!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好一个“头是头,脚是脚”,好一个“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似俗实雅,凝练传神。在这段文字中,作者就充分运用了这种长短句的大白话,将两位乡村少女的淳朴与美丽,青春与活泼,表现的淋漓尽致,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汪曾祺把大白话写得清新独到,俗而不鄙,雅而不涩,即使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婚丧嫁娶,极其平常,也能写得韵味无穷。如在《鉴赏家》中他写道:“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白的像珊瑚,红的像玛瑙。端午前后卖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重阳近了,卖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入冬以后,卖栗子。”这段文字真是洗尽铅华,尽显朴实,文中很少用形容词来修饰描写对象,只是为了使作者所要描写的对象能够更加具体一点才采用限制性的定语如“鸡蛋大的香白杏”。这些句式都非常的短小,读起来却朗朗上口,流畅如小河流水,很难令人相信作者用如此简单的词语组成的大白话竟然能给人以一种音乐感、节奏感。
汪曾祺的大白话,仿佛是在讲故事,但讲故事从来都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更注意的是故事的“氛围”和“意境”,于是乎,这种雅俗并济的大白话,这种既有民间清新气息,又有古人所说的韵外之致的大白话,就这样诞生了。
二、地道的方言
自五四以来,尝试着把民间语言溶入写作的人当然绝不只是汪曾祺一个。老舍也热衷于此。但是倘若拿这两个人相比,我认为汪曾祺则更胜一筹。这是因为老舍的民间语言多半只能构成一定的语言特色,而小说的总体框架还是相当欧化的。汪曾祺则与此不同,他的小说往往是在大的叙述框架上,来有意顺从现代汉语中口语叙事的规则。
在汪曾祺小说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方言,使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倍感亲切。自小生活在苏北水乡的汪曾祺,不但对家乡的风土人情烂熟于心,对江苏一带的特色方言更是非常的熟悉,颇知其传神妙处。如《受戒》中,小英子送明海去烧戒疤时,在船上有一段对话:“你真的要去烧戒疤呀?” “真的。” “好好的头皮上烧十二个洞,那不疼死啦?”“咬咬牙。舅舅说这是当和尚的一大关,总要过的。”“不受戒不行吗?” “不受戒的是野和尚。” “受了戒有啥好处?”“受了戒就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褡。” “什么叫‘挂褡’?” “就是在庙里住。有斋就吃。” “不把钱?”“不把钱。有法事,还得先尽外来的师父。” “怪不得都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就凭头上这几个戒疤?” “还要有一份戒牒。”“闹半天,受戒就是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呀!”“就是!” “我划船送你去。” “好。”在这段对话中,“不把钱”“有法事,还得先尽外来的师父”这两处便是明显的苏北一带的方言,“不把钱”是不用给钱的意思,“有法事,还得先尽外来的师父”中的“尽”是第一个先请的意思,也就是说当地有法事做的时候,第一个先请外来的师父,剩下的人选再依次从寺庙里挑。另外在《受戒》中,还有一处对话,是小英子和受了戒的明海隔着一条护城河时的对话:“明子!”“小英子!” “你受了戒啦?” “受了。” “疼吗?” “疼。” “现在还疼吗?” “现在疼过去了。” “你哪天回去?” “后天。”“上午?下午?” “下午。” “我来接你!” “好!”……一句“现在疼过去了”,相信吴地的读者读完自有一股说不出的激动。正是因为汪曾祺运用了如此质朴简洁的地方方言,自然而然地就能细致入微、栩栩如生塑造了一大群耿直淳朴的下层平民百姓形象,有当和尚的,剃头的,修鞋的,打铁的,酱园店的老板,学校的教师职员,洗衣的大嫂等以及兴化帮的锡匠等。尽管人物性格迥异,但语言都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大淖记事》中挑鲜货的姑娘们喊的口号:“好大娘个歪歪子咧”,还有在《星期天》中的“操那起来”,既有地方色彩,又把人物写活了,再如《岁寒三友》中一段“早!早!吃过了?偏过了,偏过了!”极其富有情趣。运用方言实际上就是用老百姓自己的语言去贴近生活,像这样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处处皆是。因此,多年后的汪曾祺总不忘强调民间语言对自己的影响。
汪曾祺极其喜爱民间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到了迷恋的地步,特别是地道的各地方言。1950年在北京做过《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编辑,这段经历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只是民间的戏曲、歌谣让他着迷,甚至连北京一派出所墙上写的一条宣传夏令卫生的标语“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再吃!”;八面糟附近的一家接生婆的门口的“广告”:“轻车快马,吉祥姥姥”;做竹藤活的写的:“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绷”。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由衷地赞美说,“这都是很好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我想,从这些方面就不难看出汪曾祺对民间的文学是多么的偏爱了。
三、浓郁的文言文色彩

有人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又有人说,汪曾祺是能作文言文的最后一位作家。翻遍他的《全集》,并未发现他有一两篇文言作品,但为何会给人留下如此的印象呢?这就不能不从他的语言运用、文字风格中去找原因了。
其实汪曾祺除了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寻求语言素材外,还非常重视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而且对古典文学所特有的凝练、传神、含蓄,一直情有独钟,偏爱有加。汪曾祺的语言不但继承了唐宋散文的流风,也继承明清散文的传统。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说“唐人传奇本多是投之当道的‘行卷’。因为要使当道者看得有趣,故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又因为要使当道者赏识其才华,故文词美丽。是有意为文。宋人笔记无此功利的目的,多是写给朋友们看看的,聊资谈助。有的甚至是写给自己看的……是无意为文。因此写得清淡自然,但,自有情致。”他也一再提到过明代作家归有光对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尤其是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一些散文写得像聊家常话似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的衔接十分自然,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我受营养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有了这些“余韵”,汪曾祺的语言就能够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文言文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的联系。为什么那些平平凡凡、十分普通的日常口语一融入汪曾祺的笔下,就能够有一种特别的味道?秘密就在这里。
记得《陌上桑》中描写罗敷的形象有这么一段“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者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见罗敷,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把罗敷之美通过侧面描写烘托出来,十分巧妙。读到《大淖记事》中描写“巧云”的一段“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快,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份量比一般人多,东西都比别人好。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她们就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膊酸痛酸痛。泰山庙唱戏,人家都是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的座。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你就会发现两者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的!
《徙》是汪曾祺在小说中运用古典文言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写文人学子则杂以少许文言”,这里写的就是一位旧社会的国文教员,为了和人物统一,无论是叙述还是对话,都夹杂了许多文言成分。如:先生名鹏,字北溟,三十后,以字行,家业世儒。祖父、父亲都没有考取功名,靠当塾师、教蒙学,以维生计。……先生少孤。尝受业于邑中名士谈甓渔,为谈先生之高足。这种文言语式在全篇中到处可见。另外,像《故乡人》中描写王淡人每于看病之余,临河垂钓,“一庭春雨,满架秋风”;还有《故人往事》中叙述收字纸老人“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等,诗意浓郁,更是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古典素养。
在文学创作中尝试文白相杂,文白相融的作家当然也不仅仅只是汪曾祺一个,但是我认为能在写作中,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入到其中,使二者能够刚柔相济,和谐统一,让人看着只觉得原本就是一个整体,这大概也只有汪曾祺能吧。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蕴藏在文中的真、善、美,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五千年所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的发现,以极其虔诚的态度来表达作者内心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人性的赞美。他的小说读起来平和淡泊,但在你静下之后细细回想时却又能感觉到自有一番情趣,把为人处世的哲理隐藏在世俗琐碎的小事中,把人性最真最美的一面展现在患难夫妇相濡以沫的生活里,文中的每个人每件事在他的眼里都是一首诗。他的语言显得纯熟而又简洁,通俗而又文雅,是一种淡泊而饱含情感的语言,一言以蔽之,是一种化平凡为神奇的语言。老子说,上善如水。水有一望无垠的大海,有波涛澎湃的大河,也有清澈见底的小溪,汪曾褀的语言就像那绵延不断的小溪,缓缓流动,“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给读者留下持久的美的享受。
语言的美不在于用词的华丽或朴实,也不在于行文的铺排或是简洁,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深深打动每一个人的内心。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你会发现都是一些简单常见的句子,甚至都不太容易找到一两个生僻的字和词,但就是这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句子,一经他的笔下,便仿佛是注入了生命注入了灵魂,让人读起来可亲可爱可敬可感。佛门有一句话叫做:高僧只说平常话。也就是说真正得道的高僧是不会动不动就给你引经据典来讲什么大道理,也不会动不动就给你背两句高深的经文来显示自己的不凡和与众不同,他只会用最平常最通俗的语言来讲述佛理,但这平常并不代表浅薄,而是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大智慧。汪曾祺便如同那隐迹山林超脱尘世的得道高僧,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未经人道语”。当真是了不起的大智者,大智慧。
参考文献:
1.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
2.汪曾祺,《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96年第2版。
3.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
4.杨学民、李勇忠,《从工具论到本体论—-论汪曾祺对现代汉语小说语言观的贡献》,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