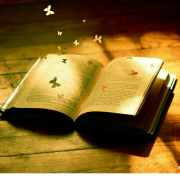雅 娜
那天,因为收拾行李,我到单位比平时晚了十几分钟。
门开着,林丽正在打电话,一边说一边笑。不知道是不是跟大民说我去则扎寨的事。
我装作没听见。
林丽十一月来的,现在才二月。我很后悔一个晚上坐在被窝里看着电视突然告诉大民办公室新来了个漂亮的同事。他正坐在床上翻报纸。为了领行情,他订了很多报纸。我其实想说林丽这个人非常懒。她自己说的,她有三十几条裤子,每天换着穿。我说,大民,你肯定不相信她的裤子一年洗一次,她还说裤子洗多了就走样了。我替她算了算,每条裤子一年穿十天。大民没说十天洗一次裤子脏不脏。
我过生日大民说请几个同事,一块儿聚聚。我开始不想叫林丽,但是临到下班,一边关窗,一边听见自己在问林丽晚上有没有空,就像我在央求她。我以为她不一定肯,因为她老是什么都瞧不上的样子。结果她一口答应了。
那真是我最不开心的一个晚上,看着大民殷勤地叫她尝这个尝那个。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全身都在放着光。
你上午还来上班?林丽打完电话,回头跟我说。
大民中午送我去机场,我说。反正傍晚我就在则扎寨了。这让我有一种飞出去的感觉。我把抽屉底下的两个日记本放到包里。
出了机场,又搭了一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停在一条新建的街口。我总不大相信自己已经在则扎寨了。
正如旅游手册上介绍的,则扎寨有不少私下招揽游客的小旅店。我在卖纪念品的铺子之间转了转,选定了吉央的妈妈。我喜欢到了某个年纪还气色红润、精干果断的女人。
谈妥住宿费和伙食费,吉央从凳子上站起来,说她带我去。
我也喜欢这个一脸喜气洋洋的年轻女子。
则扎寨的人仍沿袭传统住在石砌的碉楼里,不过不再在底层圈养牲口。现在他们都知道赚游客的钱。吉央家除了银器店还开着制作木雕的作坊。吉央领着我绕过作坊。房间在二楼,窗子对着山谷,山谷之间若隐若现的正是孔雀海。
摸着木头做的隔扇,我有些抑制不住心里的惊喜,说我就要这间了。
吉央笑着看着我,似乎在提醒我就不再看看别的了?
我这才想到是应该先看看房间的陈设的,扫了一眼铺得平平整整的床铺,放杂物的木柜,角落里盛着水的脸盆。
吉央告诉我开晚饭的时间,踩着楼梯下去了。
我锁上门,甩掉又湿又闷的鞋子躺到床上,对着窗外暮色中的孔雀海,给大民打了个电话。他正准备下班,问我路上怎么样。我说挺顺利的,就是有一阵飞机颠簸得很厉害。
吃饭了?他的声音很模糊,我说正准备去吃。
多吃点,别舍不得钱,他说。在机场他也是这么说的,别舍不得钱。然后把车开走了。
我叫他放心,挂了电话。也许他已经接到林丽了,这是迟早的。不是今天也是明天。我想象他兴奋地替林丽打开车门。他知道很多吃饭的好地方,有的是花样让林丽高兴,欲擒故纵一番,然后扑到一起。这有什么呢?很多人不都在这么干。不过明一点暗一点。我又躺了会儿,起来就着盆里的水洗了脸,感觉肚子空荡荡的,抓着扶手下了楼。
楼下响着吉央妈妈说话的声音。
我来的很是时候,吉央的姐姐结婚后第一次回娘家,来了许多客。
吉央的妈妈亲自去羊圈挑了最大的一只羊,用一根绳子勒死。我听见了羊死前的呜咽。肉在炉架上烤着,油滋滋地滴下来。我穿着吉央的旧团花藏袍,烤着火,恍如梦中。有人说我像吉央妈妈的另一个女儿。笑声中,一个人割了一块肉递到我手里。我实在不喜欢那种不加佐料的吃法,拿了一会儿,悄悄放下了。
这个人惊奇地问我怎么不吃。我想起原先边上是个驼背老人,不知他什么时候坐过来的,脸长长的很俊秀。看穿着,像是吉央家的房客,很高兴可以说点什么了,不用老看着别人的脸傻笑。
他有些羞涩地说他叫格桑,是吉央家的邻居,眼睛看着我。
真看不出来,我有点尴尬地说。现在不少藏族人汉化了。也不奇怪。
他问我叫什么,依然目不转睛望着我。
我想了想,说我叫雅娜。这是我正看的书里的人名。我是这么想的,反正过两天就走了,我叫毛小红还是叫黄小玉对他来说有什么区别呢?
看上去他相信了,问我刚才看什么,看那么久。
看什么?日暮的山谷和流水吗?谁面对这样一片风景都会入迷。可为什么他这么看着我?细长的眼睛深处竟有着无限的情意。
我们尚不相识,哪来的情意?我转头不再看他。
第二天我在则扎寨的各个海子间转了一整天,回到旅店,迎面又是那双眼睛。
他高兴地和我打招呼,问我去哪里了,说附近有个岩洞有很多漂亮的岩画,还有个寨子明天是赶集的日子,他可以给我当向导,他当了好几年向导了,我想去的地方都可以带我去。
他忽而说的这么流畅,这才是他,一个导游。我告诉他我不喜欢出去有人跟着,而且我担心付不起钱。
不贵,他举着手说一个地点只要五十块,那些地方我自己绝对找不到。
我答应去的话找他。第二天早上,想到早晨的孔雀海,没吃早饭就出了门,逛到中午才回来。
吃过饭,我拿了本书,上了吉央家屋顶的平台。摊晒的菜白森森青绿绿的,有股清香。
我翻开书。带这本书为了打发路上的无聊。几次拿出来都看不进去。这会儿在吉央家的平台上也还是看不进去。我看着四周,感觉自己超出尘世似的,干脆合上书。
一阵咯吱声,睁开眼睛,又是那张长长的俊秀的脸,看见我,羞涩地朝我举了举手,问我这么好的天怎么不出去?
我忽而发现本质上我也是个好色的人。他实在太英俊了。都说米脂的婆姨康巴的汉,他就是康巴汉吧。世界上最优质的人种。有些女人来这里,就为了跟他们同居,带一个孩子回去。
我笑着看着他,想起答应请他当向导的事。我对买东西兴趣不大,问他岩洞远不远,吃晚饭前能不能赶回来,正说着,就听见吉央的妈妈嗓门很大的在楼下吵嚷起来。
我和格桑趴到围栏边上望下看。吉央最小的弟弟噔噔地跑上来,揪了根菜茎塞到嘴里,吐了吐舌头。一溜烟跑了下去。
听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和吉央的妈妈吵起来的是两个帮工。吉央家的柴油机坏了,吉央的妈妈认为修一修还能用,两个帮工尽是找着理由拖延着,几天了,还不肯把它抬出去修。
吉央的妈妈生起气来。辫子被风吹松散了,白发乱蓬蓬地飘着,额上刀刻般的皱纹让我不相信她有什么错。
我问格桑有办法吗。
格桑犹豫了一下,下楼和吉央的妈妈叽咕着,吉央的妈妈脸还是板着,格桑仰脸朝我一笑,牙齿和眼睛发着光。我知道他们说成了。一会儿,一辆没顶盖的汽车开了进来。格桑跳下来,和两个帮工一起把柴油机装上车。揩着手,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去山巴寨。
我看着漆得花里胡哨的“敞篷车”。
去吧,他认真地劝说我,不看看就走很可惜的。
我又问了几句远不远啊之类的话,拿起书往楼下走。回到房间里,把书往枕头边一放,找出镜子和口红,慢慢地涂着。
我很后悔没带粉底液来,不到两天,这里的太阳已经把我晒黑了。我一边涂一边又有点好笑。
这是干什么呢?难道你以为他不是为了从你这儿赚走五十块钱?
我已经三十五了。结婚也有三年了。大民有个八岁的儿子,是他前妻生的,平时住在他父母那儿,他并不在乎我要不要生一个他的孩子。现在我的脸色没以前好了,乳房没以前结实了,大腿冒出来很多疙瘩,难道我跟他带过的别的游客有什么不同?
院子里,格桑发动了车子。
“敞篷车”在土路上开得跌跌撞撞。格桑说这是辆“新车”,上个月刚改装好就接了笔生意——每天早上把两个美国大学生和一堆吃的喝的送过去,天黑前接回来,接送了十一天。
你看,这个,他们送给我的。
他抛给我一个银壳的迷你播放器。我按了按钮,歌声传出来。我听了一会儿,关了按钮,问他,你会吹笛子?刚才看你拿着笛子。
你说这个,他拔下笛子给我。这笛子比我以前见过的短,颜色乌紫发亮。
我父亲说这个叫皮可洛。
皮可洛?
他腾出手吹起来。
那声音和我以前听过的不太一样,它其实不太好听,但又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我看着窗外,听着,不知道在为什么高兴,也不知道先前在为什么不高兴。我的生活一直缺乏让我高兴的事。我想到放着一盆水芋的办公桌。还有林丽和主任。他们总像一伙的,而我不管多努力,还是像他们这一伙之外的。我也想到大民殷勤地叫林丽吃菜,想到林丽浑身发亮的样子。等我回去他会开车来机场接我,他说过他爱的是我,我应该理解,请漂亮女人吃个饭,献个小殷勤,是他的本性。这会儿,如果我告诉他我跟一个叫格桑的英俊的藏族小伙子坐在一辆车里准备去山巴寨赶集他会说什么?叫我管好手机钱包,逛完早点回旅馆睡觉。他不会担心我跟这个康巴汉有什么。我也许会跟他睡觉,却没胆量怀上这个男人的孩子,即使我已经有了一点心动的感觉。在我们对视的时候,似乎已经有过点什么。
车子停在挂着干藤的石墙边。
到了,格桑开了车门。
一个伙计嘻嘻哈哈说着话走出来,和格桑一起把柴油机抬了进去。
院子里冒着热滋滋的羊粪味,修理工厂很幽暗也很简陋,伙计颇费手脚地把机器拆开,捣鼓一阵草草装起,好像医生观察一个打开的肚子又把它缝起来,说起码等五六天,把柴油机拖了进去。暗乎乎的屋子里全是坏了的机器,得等配件到货,才能动手修。
格桑把修理单子折了几下,装进衣袋,拍掉身上的灰尘,做了个走的手势。
路上,格桑又吹起“皮可洛”。这个曲子是他父亲在世时经常吹的。红马。
我望着前面,想象着一匹瘦马在晨风中跑,细瘦的马蹄踏在地上,却是坚实的。
你有过这种感觉吗?我问他,你到了一个地方,你明明没来过,却觉得熟悉,好像来过,看见过?
格桑不解地看着我,很多人都这样啊,来则扎的人大都会觉得他们来过。这里的山是圣山,这里的水是神水,这里就像天堂,我们都是从天堂里来的,所以喜欢这里。有的人来了就不走了。下一世,他们就是这里的人。
那么这感觉不是我一个人有的。
街两边的摊子一眼望不见底,格桑走在我前面,一步一步晃悠在卖虫草、鹿茸、麝香的摊子旁,时不时呼啸一声,跟熟人打个招呼。药材味儿夹杂着牛羊的膻气钻入鼻孔。这就是这里的味道。我也不走了,下一世,就是这里的人。
我买了一个放香粉的银壶,一块淡紫色的羊毛披肩。
这种紫叫格桑紫!我回头大叫,却不见格桑。
前面有个卖糖的小摊。透明的糖像一块块玻璃插在草秸上。这不是小时候吃的那种糖吗?我买了糖,吮着,一直走到底。集市开始散了,街上到处是收摊的和抢着做成最后一笔买卖的人,轰起的灰尘草屑沾着人的头发和鞋袜。
我看到格桑,拼命朝他招手,他跑了过来。
格桑,这儿也有唐溪人啊。他们在这儿卖糖。一对夫妻,很老了的一对夫妻。
唐溪是哪里?格桑整齐的牙齿在太阳里闪着金光,晚风吹过来,他好像摇晃起来。
是我出生的地方,那里产枇杷,你知道吗?枇杷很傻,冬天就开始开花,反正要到夏天果子才熟,为什么不春天开花?受一冬冻。我会把它的皮剥成一朵莲花。我一口气说着,把这两个字写在手机里拿给格桑看。
那里产丝绸吗?格桑问。
丝绸?当然也产丝绸,我说。想到很久没回去了,我有了想哭的感觉。为什么呢?我不愿回出生的地方,也不愿留在现在生活的地方。我不走了,下一世,就是这里的人了吗?找一个格桑这样的丈夫?心思里只有丈夫,孩子,马,牛,羊。
我想到马,真的过来了一匹马,是一辆马车。马头和车轴上扎的红绸喜气洋洋地飘着。两个年轻女孩坐在上面,悠闲地说着话。马漂亮的鬃毛也在风里飘着,过去了,脖子上的铃铛还在叮叮当当响着。一个念头蹿上来,我叫道,不行,我要坐那辆车!
格桑看着我,他们还要去别的寨子的。
我说我不在意多逛一个寨子。
可是,我把你带过来的,应该把你带回去的啊。格桑说。他真像个孩子,我看着他,很想抱着他的脖子,久久地吻他的头发。可是,这个时候还不行。还不行。
就这样吧。我拿了五十块钱,往他手上一放,朝马车奔过去,说,这是今天的。就这样。明天见!
格 桑
我来不及想这里面的变化,看着她笨手笨脚爬上车,坐好,冲我摆了摆手,只好也冲她摆了摆手。好吧,小心点啊!明天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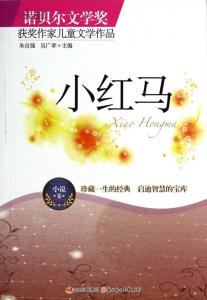
那时我还没想到她和米雅一样走了。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十九岁时我已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事。米雅。雅娜。她们挺像。米雅的下巴更尖一点儿。她们的头发都是又细又软,眼睛都很大、很亮。她们都认为自己很有想法。米雅要的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和我一样的孩子。用她的话来说,没被污染的纯洁优质的小孩。雅娜呢?
我回过头,看到一个淡紫色的小点。她干吗非要走呢?看她刚才那么高兴。她们这种单身客经常会冒出点奇怪的念头。她明天真会要我带她去看岩画吗?她们都差不多,往往前一分钟还这么想后一分钟已经改变主意了。但是她和别的游客还是不一样。究竟不一样在哪,我也不知道。不是每一双看着你的眼睛都会跟你发生点什么。
我又去了比尔酒馆。稍后,一个我认识的进来了。我们喝着酒谈着天。我告诉他今天赚了五十块钱。我还说了雅娜。她非要坐马车,我说。
这些人都这样。他舔着嘴唇上的啤酒沫说,这些人在家里门都懒得出,却不怕远地跑到这儿来。不是吗?这家伙摇着头,没舔干净的啤酒沫沾在嘴上,好像又长了一张嘴,一张白嘴。我知道他说的这些人不单是女人,还是男人。每到这时,他就快说话了。勒索,骗局,谁上了谁的当,谁骗了谁,他有一肚子这样的事。
不过我不希望他这么说雅娜。
她很像米雅。我说。
这里的人都知道我和米雅的事。游客有兴趣和本地人谈天,一定会从他们嘴里听到我的故事。我们在一起过了十八个月,她身材苗条,胸部饱满,干起活来一点不省力气。我喜欢她教我认字读书,干完一天活晚上浑身松软地摊在床上,说她生活的南方,那些过去的事,像一块丝绸,她老家产的丝绸。她总是说,格桑,你不会知道那些丝绸有多软,摸在手上有多光滑。我想不出。再软再光滑的丝绸也比不上她的背吧。有一天晚上,她告诉我她要回家了,我问她,要我跟你一起去吗?她说不要。她给我做了足够吃三天的饭,把给我新织好的毛衣平摊在床上。搭上去县城的汽车前,她抱着我的脖子,久久吻着我的头发。车开了,她隔着车窗把孩子的头托起来,让我看他圆滚滚的小脸。我等了她三年,猜她不会来了,娶了同一个寨子的梅朵。梅朵跟米雅一样,干起活来不省力气,像头牛一样,谁知道她会死在生孩子上。我没有再娶,一个人过有什么不好?
我很久不想这些事了,端起酒杯默不作声喝了一口。
巷口修车的上午被抓走了,你知道吧?果然他开始说了。我的兴致提了起来。我知道,我说,就是戴棒球帽那个吧?
嗨!他在老家做了案的……逃出来七年了,谁看得出!
我们坐到雅娜的五十块钱被消磨了大半才走。
借着酒劲,我兴兴冲冲地开着车,我喜欢这样,边开车边看月亮星星,天上所有的星星都是天神的住所。吉央家的屋子黑乎乎的。我想到她,那个女人,雅娜,她溜达够了回来了吧。睡了吧。刚才,她走之前,眼睛那么看着我,她想告诉我什么呢?我回到家,躺下去了,还在想这个,我也想米雅光滑的背,这两样东西搅得我很久没有睡着。
雅娜夜里没回来的事,我中午回到寨子里才知道。吉央的妈妈叫住我,问我昨天把雅娜带哪去了,到现在也没回来。
她还能去哪里?会不会早上出门溜达去了?我问吉央的妈妈,把昨天的经过一遍两遍讲了七八遍。每一遍最后,我都说,是她自己要坐马车回来的。
吉央说我们太大惊小怪了。没准,她就是在哪儿被迷住了。玩够了就回来了。但是等她交的房钱过了期限,我们并没有看到她。很多天过去了,谁也不相信她还会回来了。她去了别的寨子,我们找到那个马车夫,他这么说的,半道上,她说要下去,叫他不用等,他就自已走了,她觉得那儿更好,干吗非要回来呢?则扎寨又不是她的家。
她留在吉央家的除了枕头边的那本书,还有一块干透的毛巾,一条绣着粉红蔷薇花的裙子。
吉央的妈妈把这几样东西装进布袋,收了起来。她要是还想要就找我来拿,我不能老让这屋子这么空着。这个倔强的老婆子干脆利落地说。
吉央家不久就有了新房客。那对四十来岁的双胞胎总是一同进一同出。她们什么地方都要去,一到就拿出照相机,你给我拍我给你拍。我也带她们去了岩洞,但是她们好像对那些岩画毫无兴趣,站在岩画前嘻嘻哈哈笑着,不知拍了多少张照,而后一阵风似的走了。
我知道那儿有个山洞,几年前也有游客迷路掉进去,反正掉进去的人活着也跟死了一样。没有人有本事把人从那儿捞上来。我不相信雅娜有那么倒霉。米雅以前喜欢说,这世界是很公道的,需要好人也需要坏人,必须得有人充当坏人,他们有时会得到很多东西,但是往往死得很惨,比如,被汽车轧死是一种,掉到这个洞里慢慢饿死也是一种。我不相信雅娜是这种人。我小心地朝洞里张望,喊着有人吗?有人吗?洞底回答我的不是我自己的回声,就是水从岩石上滚落的滴答声。看来她不在那儿。
一早起来,挣游客的钱。但是回到家里,却总是坐立不安。直到我又去了那个山洞,在那个山洞附近找来找去。有时候,我的袍子被野蒺藜的刺刮下来一大块儿,我的脸也撞得青紫了,落魄地走下山来,吉央的妈妈,这倔老婆子讽刺我,你有什么不能心安理得的?好好挣你的钱吧。
有一天,这倔老婆子站在院子里问我柴油机修好了没有,我猛然想起她家的柴油机还在修理铺里搁着。我说我这就去,到了修理铺才发现单子不见了。回到家里翻得底朝天也没找到。我记得把它放在那天穿过的袍子里。一次次把手伸进袍子的口袋,里面总是空着。我只能回到修理铺,说了好多好话,他们就是不让我拿回来,说,凭单子拿机器是铺里的规矩,否则,下次有个人拿着单子找我要,我拿什么给他?
那以后,那老婆子一看见我,就催促我快点把她的柴油机给弄回来。
我告诉吉央我的苦恼,好啦好啦,吉央嘴里吐出来的话跟那老婆子一模一样,你有什么不能心安理得的?是你带她去的。那又怎么啦?好好挣你的钱吧。别这么呆头呆脑了,她拍拍我的头,你干吗老想着她?
我看着吉央。我干吗老想着她呢?就因为她像米雅?不是,不是。我想起她的眼睛。不是所有的眼睛都会告诉你什么。她想告诉我什么?她好像想吻我的头发,像米雅做过的那样,抱着我的脖子,久久吻着我的头发。
吉央开导我说,你要想,就像那些一阵风赶过来又一阵风走掉的游客一样,她也像一阵风似的回她自己的家了。
是的,是的,就这么想吧:她回家了。冬天不久就来了,这种时候谁也不做活了,天刚擦黑,家家便闭了门,围着火塘烤火,把身子吃得热烘烘的躺进被窝里。我只怕闻到松柏香堆燃着后的气味儿,知道那股青烟正袅袅在山野间飘浮,飘入云霄。那是有人死了。雅娜是死了,还是活着呢?
又是一个冷清的晚上,我烤着火,看着自己的手。我的这个家,从前的热闹是再也不见了,先是我父亲,接着是我哥哥,一个死在马上,一个死在医院。现在,家里只剩下我和阿妈了。白天,阿妈只在屋子里诵经,夜黑尽了,才捧着一只点着火的铜钵出来。塘边放着的旧经书,是她无意中落在火塘边的吧。我拿起来翻开,突然一张纸掉了下来,轻飘飘地落到地上。
我捡起来,弹掉灰尘,愣住了。这不是那张修理柴油机的单子吗?
那晚我把单子放在膝上,在火塘边迷迷糊糊睡着了,迷迷糊糊做起梦来,梦见自己坐在汽车里,车不停地往前开,往前开,一直在往前开,窗上结着雾气,我只能知道我们走在一条宽阔的大街上,街两旁房子一幢接着一幢,天蓝的桔黄的屋顶积着雪,像蛋糕上的奶油,涌到啤酒杯外面来的泡沫。车子停下来,我看见了雅娜。我问她,你去哪里了?她身后的光越来越亮,我还以为是那火光自己在飘动呢,却看到朝我走过来的阿妈。
我很高兴阿妈赞同我去唐溪,她说,你心里放不下,就去一去吧。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要去那么远的地方,看一下地图就知道有多远。吉央说这太天方夜谭了,靠着这么一个梦就能找到?
是太天方夜谭了。可不靠这个梦靠什么?反正我已经知道有唐溪这么一个地方,产枇杷,丝绸,为什么不去一去呢?这个念头像根针似的,时不时用它尖利的那头钉我一下。
比尔酒馆,我认识的那个什么都懂的人开导我,去,不去,就那么简单,没有去和不去。就这么简单?我把“敞篷车”押给酒馆老板娘,叫她好好替我管着,等我把钱还上就把它开回去。
飞机天亮时到的。在飞机上和我一样一个人的有很多,只有我空着一双手没事干。没有谁看我,他们谁也不看。看来我不古怪,这让我好受了很多。
出了机场,搭上一辆大巴,车不停地往前开,往前开,一直往前开。窗上结着雾气。和则扎寨一样,这儿也刚下过一场雪,细碎的雪花被风吹落下来,一小片、一小片地飞舞着。我用力抹开窗上的雾气,贴着窗子看着外面慢慢划过一幢幢房子,和梦里一样,也是天蓝的桔黄的屋顶,屋顶积着雪。
车停在一条新建的街口。我下了车,走得很快。沿街的窗户关着,一条狗跑过来,嗅着我的脚,一个女人把它叫走了。我往前走着,两个手里提着菜的人,嘀咕着从我身边走过。一个戴皮帽的老头迎面走来,留下几声虫子似的哼哼。一个在街沿上摆了几棵青菜的老太婆胆怯地问我要不要青菜。墙上贴着布告。这就是雅娜落生的地方。米雅呢,米雅会在哪里呢?带着我的儿子?
只剩最后几个天蓝的桔黄的屋顶了,已经到了这条路的尽头,我有点胆怯,却管不住我的脚,它一大步一大步,磕磕绊绊朝前跨着,直到眼前忽然一亮,我走到一个游乐场里来了。真想不到这里有这么大一个游乐场,有这么多不怕冷的孩子,穿着五颜六色的棉衣,赤着的手,手心冻得通红,争着在滑梯上爬上去滑下来。我就像掉进一个麻雀窝,耳朵里全是孩子叽哩呱拉的叫声。
太阳慢慢地大起来。哪里都是通红的,金黄的。雪薄的地方开始化了,滴滴答答地滴着水滴。我觉得热。好像冬天挤掉春天,夏天突然来了。我脱掉最外面的衣服,还是热。绕过一个跷跷板,我又脱掉一件,把它们扎在腰间。
不能再往前了,我的心突突地跳着,闭了闭眼睛,又睁开了。紧靠着墙的尽头,在梦中雅娜出现的地方只有一匹木马,一个小姑娘坐在木马上面。
是个很小的小姑娘,漆黑的头发,漆黑的眼睛,看着我笑着。
就像看到了雅娜,也看到了米雅。虽然,我知道我再也看不到她们了。我的喉咙就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抖动得厉害。所以我就那样垂着手,看着她。过了很久,我往前走了一步,轻轻地说了声“你早!”
作者简介:吴文君,浙江海宁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学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中青年作家班学员。近年陆续在《北京文学》、《大家》、《收获》、《上海文学》、《中国作家》、《钟山》、《山花》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
百度搜索“爱华网”,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爱华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