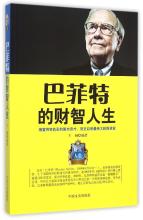没了母亲的第一个母亲节,一个人在公寓里把个空空的皮囊放倒在床上……,多少年没人打扰的生活,也常有这样空荡荡的感觉。象这房间一样,只要自己不动,便是一片安静,安静的象这空气,划一根火柴便能燃烧。我有些透不过气来,想出去找一位在春天的阳光里散步的老人,或朋友的妈妈,听她随便唠叨些什么……。
母亲住在东宁城边安静的绥芬河南岸,大大的院子西北两面,长着高高的杨树,院门外是一条近两百米的、一眼望不到一个人影的胡同,但这是一条我永远走不出母亲视线的胡同。
每一次从绥芬河市回东宁看母亲,母亲总会说:“这么老远回来干啥,花着钱,跟前儿的不过年节、不过生日都不回来”。她象是烦我回来,其实是心疼我花钱。是的,我是她唯一一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风雨飘摇的无家的儿子。每一次说完这番话,无论母亲在院子里,还是在屋里炕上,总要缓慢无声地斜斜身子往我的身后看看。这看似漫不经心的细小举动,总会弄得我一阵酸楚。在八十多岁的母亲面前,我一个人来来去去的身影是揪着母亲的心,我知道这是一种最大的不孝。每次的这一刻,我非常想抱一抱我的母亲,可每一次都只是抓起妈妈那粗糙变形的手,尽可能笑出一种没饿着、没冷着、没什么病的憨儿子的样子来,嗓子却紧紧地咽着多出来的唾液。离开的时候不管你怎么说不让她出来送。可我知道,不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母亲那弱小弯曲的身影一定会缓慢地挪出来。在那个安静的胡同,我走出一百米左右时,母亲保证在院门那儿露出半个身子,半张脸,看儿子孤单的背身,母亲能想些什么?期盼或担心在这条冷清的胡同里不再可能看见两个孩子一同来去的身影……。差不多在看见那半身半面的每一次,我都无从控制眼泪流出,幸好母亲是看不见我哭成了女人。但母亲会扶着门久久地追望我已没了踪影方向。母亲已走不了多远了,不然……。
母亲八十岁那年,我给她买了个俄罗斯拐杖,母亲却不常用。八十四岁那年她先后把手腕和脊椎摔成了S形。医生说:看CT这老太太的小脑已经萎缩的太严重了,她早该不能走路了。但我的母亲就是这么神奇,我记忆中就没听过母亲有病要去医院。有病抗着是母亲的倔强习惯。手摔坏了,她也坚决不许别人给她洗内衣内裤,一只手自己洗,不能拧,放到筛子里控水。母亲爱干净,却常有像小女孩子一样的腼腆。她把脊椎摔弯的那次,母亲倒在菜园子里起不来了,她不知自己努力着拱了多久才疼得大汗淋漓地喊我父亲……。正巧我那日回东宁,带母亲去了医院。上楼时,我右手抓住母亲的右手一转身,蹲在母亲前边说:
“妈,我背你上楼”。
母亲竟然非常不好意思地打我的头,之后又用手支住我的背说:
“我不用,不用”,
“你听话,快来妈!”我执意的,
“我不!那样更疼”。
我不知这疼是真是假,但母亲真的扶着楼梯一步一步上到二楼。我搀扶着母亲胳膊,看见汗水在母亲脸上滑落。我再也忍不住怪怨的眼泪了,心疼又骄傲的近乎语无伦次地和看见的人说:“她不让背,把腰摔了,都八十多岁了,不让我背”!
母亲的刚强是无声的,看看她的手和这弯曲的手腕,看看这疼出的汗足已说明。
她有七个儿女。大哥大嫂是六四年插队知青,领两孩子挣不来工分,口粮都没着落。母亲能在山上刨老多的地,能缝缝补补,精打细算地让所有的孩子念完了高中。一家十二口人,不知在那个年代母亲是怎么抗过来的。要知道家里活父亲都不会干。直到八十年代,母亲一直都给他做小灶。那个油、肉定量的年代中,母亲能闻着奶香、菜香,却半口不动地端给父亲吃,自己却吃一些我们吃后的粗粮剩饭。
六七年文革时期,父亲被抓。罪名是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父亲的工资停发了,被关进小黑屋,不许吃细粮。这可难坏了母亲,因为母亲从来没给他吃过粗粮,说父亲肝不好。
我那时刚上学,常在放学后和母亲去绥芬河发电厂送饭。母亲常在送完饭后站在那个高高的大煤堆上看破衣烂衫、满脸黑灰的父亲推煤推灰。(那种小轨道式的铁翻斗车)
,如父亲正好走到母亲下边,看守没注意,母亲会象变戏法一样从怀里拿出一个包好的牛皮纸包扔下去,父亲会像小偷一样把纸包塞进破棉袄里。有一次被看守发现了,父亲乖乖地交出来之后左躲右躲,还是被踢到两脚。那个走到哪把光明和动力带到哪儿的工程师,竟然落到被人踢来踢去像狗一样的地步。看守查看着纸包,把糖三角举得很高摔在地上,踩了一脚,大声喊骂母亲。母亲躲一会儿之后,会快速跑下煤堆把那两个糖三角捡回来,边用嘴吹吹,边把脏地方剥掉说:“煤沫不埋汰,你吃一个吧”。我看着母亲手里的另一个,飞快地吞吃着,糖三角太香了,吃到一半时,我抬头看着母亲的时候,才发现妈妈是那样无助无声地流着泪。我停下嘴,手拿着半个踩扁的糖三角,默默地走着。母亲用那个有些脏的手擦着我的脸说:“男孩子不许哭,吃吧,一会该冻了”。我那时还不懂母亲的眼泪里有多少内容多少艰难。只是不久就又看到一次次那无助的哭泣。一次我在学校被当作狗崽子把头给打坏了,我非常昂扬的哭着跑回家告妈妈,可是母亲只是把我那个头发都贴到一起的血脑袋搂在怀里哭出了声。妈妈没去找老师,也没去找那些学生家长,妈妈什么也不说……。
现在想想母亲那时真的太难了,仅父亲从厂长……工程师、掉进这种被踢来打去的耍猴斗狗一样的处境,就足以让母亲倒下。没了父亲的工资,母亲领着一群孩子,吃穿、上学、受气、种地、还要常常目睹父亲戴着高帽在街上游斗。可是我的母亲不知用什么力量支撑着没有倒下。母亲像一把大伞,多大的苦难,她都一个人支撑着……。
如今,母亲的头发是银白色的了。苦难如烟的岁月中,那把大伞下面的孩子们,都已经各自走进了自己的风雨中。然而,那把斑驳荒凉的大伞,却像是在给人类文明的生命中,这种亲情的淘汰过程刻写着一种无奈与苍凉。
03年4月的一个周五,我从绥芬河市回到东宁准备领取父亲去省城哈尔滨看病(父亲怀疑自己已得了癌症)。离母亲家还有一段距离,我就要求下了的士。
春天多好啊!空气中都有一种松软暖绿的气息,尤其这美丽的绥芬河畔流淌着多少芬芳妩媚的传说或潺潺哀婉的故事。我非常想在那河岸上呆一会,但还是有一种什么力量在召唤着我拐进胡同,正看见落日西山的落照中,巷道空无人行,却见母亲依门半面在晚辉里银丝寒舞……妈妈,你茫然中在等谁呢?你常常这样遥无知晓地等盼着什么吗?你知道那个孩子在这个黄昏中到来吗?我不得不停步转身料理一下我的脆弱。还好,我比眼泪坚强一点点,快步走完这乍暖还寒的两百米,抓起母亲的手说:
“妈,挺冷的你在这傻瞅啥?你看手冰冷,脸冰凉的”。
我很想把妈妈的脸抱在胸前,可是母亲的话让我吃惊:
“我在等你来”我扶母亲边走边问:
“就像你知道我今天这个时候来似的”
“我知道能来”,我不解地歪头看看母亲的脸,
“站半天了吧”?我问,
“没有”

“还没有,你脸和手都冰凉的,不知道冷啊老是摔倒,出来也不拄拐杖白给你买了,再摔倒,就一只手吃劲,不又得骨折了”!
扶母亲慢慢地进了屋,心里却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吃完晚饭,母亲的手依然冰凉。
她拄着拐杖要出去,我说就在屋便吧,我去倒,母亲说:“臭,不用”。
父亲把脚放在脚盆里,放着很大声音看电视。我依着暖墙坐着,握着母亲的手和母亲唠着:
“现在还没暖过来呢,还不得感冒呀”!
“到寿了,不中用了”
“妈,你过一百岁没问题,你看你眼不花,耳不聋的,你看我爸耳朵”。
“没那命了,到寿了,不死让人烦,他们都不回来看看,也不知真忙假忙”。
“妈,你进被窝里吧,被窝暖和”,我心里有些怕。觉得母亲今天不正常。
快九点时,母亲唠唠便睡着了,那么安详的。我也去了西屋睡下,九点半,爸爸来叫我说:“你看看你妈怎么了”?我没顾穿衣服,三步两步跑过去,母亲已经不是那个安详的样子了,我看舌头好像堵在嗓子里,便轻轻地把母亲抱了起来。然而千呼万唤也没有叫醒母亲,我让父亲挂120,我抱着母亲不敢动,贴贴母亲的脸依然那么凉,妈妈!你真的要走吗?难道你真的事先有什么感知吗?
医院CT显示,母亲的脑干大面积出血。医生说:“准备后事吧,不会过今晚”。
在母亲柜里面拿出她早已给自己做的装老包裹里发现了两个瓶子,父亲说是我母亲早买的毒药一人一瓶,说怕万一得病不死好吃,别让孩子们麻烦。母亲在医院里昏迷了六天,医生说神奇的老太太。母亲像在等什么,第二天晚上哈尔滨的女友来电话……,“你好像在一个走廊里,出什么事儿了吗?”我告诉了她,她说马上过来,我心中一阵难过……。要是早点领来让母亲见一面该多好。母亲是等她吗?
母亲的鼻子里插着氧管,用嘴呼吸,嘴就干干的,我去熟人家里要了些香油给母亲擦舌头和嘴。我想,若是女友能来,母亲也许能感知到的。三天没有合眼,哥哥嫂嫂子们轮流睡,我睡不着。总有一种在空旷的水面上漂流的感觉,没什么时候比现在更渴望有个女人在身边。
妈妈,我对不起你,你应该再晚些走,你本来应该看见我已有一个女朋友了。你为什么不等等我呢,妈妈。一直想抱抱你我的妈妈,可没想到,那晚的抱,你已永远不能感知了。这一抱竟然把你抱进走向天堂的胡同里……。
我的泪不知道多少次这样重重叠叠流着,我似乎明白了走进胡同的那一幕黄昏,母亲在春寒中等什么……。
邻床的阿姨过来说,别人都打打盹。你怎么一点觉不睡?别老哭,这样你母亲是走不了的,你这不是让她多遭罪吗?
我给女友打了电话,她关机。她还在路上吗?她没有来,是怕该还借我的钱吗?天!这世界……!
母亲走了,带着牵挂走了。留下父亲和那空大的院落,留给我这长长的胡同,让我独行,却永远不再有母亲那牵挂的注视了……。
完稿于二〇〇四年母亲节后的几个雨天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