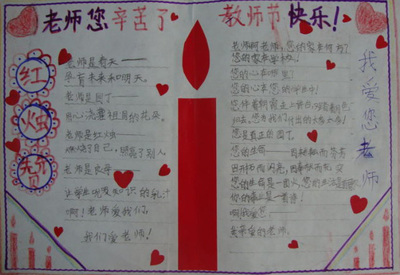主食:滋味的依赖
中国最古老的主食之一的“黍”,在编导胡迎迎的寻找中得之偶然。她是扬州人,并不属于“吃货”,扬州精致的饮食习惯对于她造成了相反的作用。“也许是物极必反,每年过年,我奶奶和几个姑姑都在厨房忙个不停,我家过年的规矩是摆上几大桌最精致的菜肴,每道菜都能让你精致到不忍下筷子。”
因为逆反心理,所以她在接受拍片任务的时候,听到题材是“主食”,反倒很高兴,她实在厌烦了精致化的食物。去陕西寻找主食,无论是陕西岐山臊子面,还是肉夹馍,尽管都不错,可还是缺了点什么。“我觉得陕北这片土地上应该能找到更扎实、更基本的主食,朋友建议我去绥德那边看看,结果找到了靖边县。快过年的时间段,县里干部直把我往外边赶,告诉我他们这里没什么我想要的。我被他赶得心里发毛,冲他喊道:‘我也不要你们干什么,我自己找找选题而已。’”
最后的县委食堂的大师傅救场。他告诉胡迎迎,除了供应给县委领导白馒头、烙饼等主食外,他们这里还有一种黄馍馍,不过爱吃的人少,尤其是年轻人基本已经不吃了,是用糜子面做的,也就是中国最早的谷物“黍”制成的主食。县城下面的集市上有个老头,专在赶集的日子去卖黄馍馍。胡迎迎就找到了集市,那天卖馍的老头正好没去,大雪天她又一路找到了康家沟,结果山坡上,赶着毛驴驱动碾子的老黄让胡迎迎终生难忘——“太美了。”景色基本上符合所有的要求,而和媳妇并肩坐着的老黄完全符合她对中国这种最古老的主食制作人的想象,眼睛特别干净,态度也不卑不亢,一谈到黄馍馍,精神来了。“他觉得自己做的就是天下第一。”大碾盘上放着蒸出来的十几个黄馍馍,胡迎迎说自己南方人的胃不觉得这种食品多美味,但是,拙实,粮食本身的微甜,没有巧劲,由此,这就成为“主食的故事”这集里的第一个故事。
《舌尖上的中国》执行总导演任长箴
中国花样繁多的主食,目前大多还是出自乡土。在山西丁村,她们找到了咸丰年间的大厨房,拉着风箱的大灶,炕上坐满了来说家常的亲戚。“不过磨磨的牛是从地里现找来的,当地已经普遍改用电磨了。”坐在炕上切面给老伴祝生日的老太太手上的大刀,也是从丁村文物队队长手中借来的,队长可兴奋了,因为他自己的收藏派了用场。
这是一个正在改变的乡土。胡迎迎告诉我:当地很多人现在过生日都已经改吃挂面,因为他们拍摄的关系,大家才把当地的各种面食手艺都施展出来,花馍、馒头、包子和长寿面,他们待在那儿的几天里,顿顿主食都不重复,“有一种北方的笼统的好吃”。
朴实的东西有一种归属感。胡迎迎说,她做主食这一集,慢慢明白了这个道理。在广州找到竹笙面的路边店,也是看重了这种感觉。开始在一家著名的酒店里拍,镜头里有一种特别的俗气。胡迎迎说,广州的主食,怎么都让她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拿竹笙面来说,特别脆;黄鳝饭血淋淋;干炒牛河用的沙河粉,开始被向导说得很神,说是白云山的水做的,可是并非如此,她开始都不太喜欢。拍摄了一段时间下来,猛然明白,这种她不喜欢的主食体系里,有一种南方的主食精神:对口感的不懈追求。“竹笙面的汤底用大地鱼和骨头细细熬出来,沙河粉磨成米浆,和西安热米皮的制造过程看着相似,可是最后出来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胡迎迎说,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主食依赖。比如兰州拉面,开始不太想拍,因为通俗,可是后来觉得兰州拉面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太神奇了。每天听着城里清真寺的召集声,看着面馆里老师傅拉面如入化境,觉得拉面真是种干净、有仪式感的食品,充满了对面的尊重。
更多的中国主食,多的是对食物本身的喜爱,有一种日常的满足感。在贵州拍米粉,一对做了30年米粉的夫妻,每天早上起床压粉,早上的小房间里蒸汽腾腾,充满了米香,女儿在外地上大学,老夫妻说,自己这辈子很值得,因为后代有出息。在温州拍摄锁面的计划后来被阴雨天打败了,当地的锁面很长,在南山上生产,挂起来感觉很像大片大片的渔网,很壮观。一对小夫妻主持着小作坊,男主人改进了生产机器,是当地最聪明的小老板之一。“可是一去就下雨,结果就不能晾晒,只能放弃了。”
虽然是“南米北面”这样大的主食区域划分,可是,中国的主食体系可没这么简单。主食体系并不单独存在,一定是配备菜和佐料食用的。同样是米粉磨成浆,热加工蒸制成米皮,南方是配虾仁、牛肉或青菜,成就了广东海南等省份的肠粉。可是在西安,这种热米皮是用醋和辣子搅拌后食用的,滋味改变了主食的体系。
《舌尖上的中国》拍摄现场
就拿胡迎迎觉得难以完成叙述而放弃的馒头和包子来说:虽然中国各地都有肉包子,但是南方和北方的猪肉包子完全依赖不同的味觉体系,北方常用的大葱和韭菜,到了南方完全变成了小青菜,而在云南则摇身一变,加上了大量的香菇和苏子。
主食的一大趋势是工业化。在嘉兴的五芳斋拍摄包粽子的画面,胡迎迎印象深刻的是,尽管还是靠手工,可是工人们已经机械得如同机器。最能干的工人,一天能包数千个粽子,劳动力本身的低廉价格,使得这种手艺也并不太受尊重。她说自己心里很不舒服,有人一天包3000个粽子,旺季包5000个。“一辈子包这么多的粽子,意义何在?”包括流水线上的饺子也让她害怕——“就是画面好看我也没拍,因为这种主食后面没有了人的存在。”
她更忽略了一件事情:流水线上粽子和饺子的最大问题,其实不在于是不是机械制作,而是滋味的重复化,工业化生产的主食体系必须寻求共同而稳定的滋味,几个批次、几个月、几年,都要达到味道和外观的同质化——这哪里还是中国小家小户生产出来的主食的滋味?
就在这两天,因为黄馍馍而成名的靖边县的老黄被西贝莜面村的老板叫到了北京,准备弘扬光大西北美食。听到消息后,胡迎迎非常生气,她说她打电话把那个老板骂了许久。她就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商业化的现实,在她心目中,老黄就应该在山崖上充满自信地做他自己唯一的黄馍馍。
菜肴:自然的馈赠
以中国地域之广阔,主食只是解决了基本问题,主食之上的是菜肴。负责这集的导演任长箴告诉我,当初她们筹划的时候,有一种打算是将之拍摄成“厨房里的秘密”那种类型,可是她自己并不喜欢。“我不是美食家,也不打算拍摄成一个厨房接一个厨房。”一本意大利作者卡罗·佩特里尼的书《慢食运动》改变了她,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为什么食品要讲究优良、清洁和公平。第一个例子就是发生在欧洲的令人担忧的景象,意大利皮埃蒙特区域的传统方胡椒被荷兰进口的、价格便宜颜色鲜艳的胡椒取代了,这导致厨师的手艺还是很好,地方风味却消失了。
任长箴告诉我,她因此而开始研究自然和人的关系,食品如何破除了原来的生产状态,把多样性破坏掉,那么地方风味何在?看了这本书,她确定了几集的结构,第一集食材,其实是讲自然的馈赠;而最后一集进一步讲人类如何利用自然去获得食材,其中还有两集讲食物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时间的味道和食物的转化。
其实中国在饮食上的古理就是吃当时当令菜,品尝“时鲜”。她们就跟随着时间走,追随当时当令的食材。最早拍摄的,是北京的屋顶菜园——最后放在人类对自然的索取那集里。主人公叫她们快点来,西红柿、豆角和黄瓜都快熟透了,不来摘就快“掉”了,都是北方当季的家常菜,却有种鲜活的质感。
7月份去香格里拉拍松茸。“那么多摘松茸的人,一眼就看中了卓玛。”不是因为她是采摘能手,“当地100个人里面能找出99个采摘能手”,而是因为她的干净和紧张。在海拔4000米的山地上,小姑娘如履平地,拍摄的人倒是无法跟上。一般的菌子,卓玛看不上,她的眼睛里只有松茸。采摘下来的松茸,品相不好的在帐篷里用酥油煎烧烤着吃掉,用最普通的当地陶锅。任长箴回到北京还在回味那种鲜美的味道——“无法想象当时怎么觉得那么鲜美,那酥油味浓得让人不能接受,可是在帐篷里,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她又发展出自己的第二个观念:一定要在当地环境里吃当地的东西,一方水土一方人,是最天然的。在帐篷里,大家用奶渣蘸白糖,大把吃,从来不吃甜食的任长箴也被这种食品迷住了——回北京想想,也觉得奇怪。
《舌尖上的中国》拍摄现场
回北京去“云南印象”拍摄昂贵的餐厅制作的松茸,1600块钱,小小的几片,她在高原上对这种食物的感情陡然就消失了,所以用了几句简单的解说词就打发掉了。但是在高原上的采摘镜头,她却毫不吝啬地配了很多词语。包括采摘松茸后掩埋菌丝坑,当地人的平常习惯,她都予以了高度赞美。
松茸结束了,是笋。浙江遂昌山里巨大的笋,这种冬笋价格昂贵,可在当地人看来,却就是一道家常的菜,根本没那么多讲究。“那种刚摘下来的笋,随便一碰就酥了。和别的食材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笋摘下来后还会不断变老,所以能吃到最鲜美的笋,实在是人的福气。”任长箴说,吃东西要吃30公里内的,这个距离是她随口说出来的,可也非常有道理:“离开了土地节气,确实就吃不到好东西了。”
8月份,去广西田林的八渡乡去拍笋,因为干旱,成立了10年的八渡笋合作社濒临倒闭,但她们也没有放弃拍摄。“还是想看看人在面对自然索取不得时候的状态。”人们漫山遍野地寻找,向更深更潮湿的山林进发的场面,让人印象深刻。索取的有时候是放弃,拍摄查干湖的破冰捕鱼,找到的石把头有点老了,并不是新一代的当家人。可是他的网很有特点,因为网眼很大,多少年他都不肯变,就是想把小鱼留在湖泊里,他知道自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不过任长箴告诉我,最让她吃惊的还是藕。北方人对藕并不熟悉,最早选择的是微山湖去拍挖藕。总导演陈晓卿建议她们去湖北,说相比起湖北的藕,北方的藕就不算什么了。去了湖北嘉鱼,已经是10月份,那种艰苦的采藕环境还是让她吃惊,谁都想不到这种高产的食物,采集却是这么艰难,几乎所有挖藕的人都得了关节炎。特意选择了不甚强壮的圣武和茂荣兄弟俩,就因为他们和环境的艰苦有反差——如果选一个强壮汉子,大家印象反而就不那么深刻了。环境恶劣,报酬就高,长相文弱的圣武会不断地说,老婆叫他注意身体。可是,这句话在严酷的劳动中,更像是一句空话,工头给他们提供的食物也很简单,按照任长箴的观察,热量不高,清汤寡水,可是却要应付高强度的劳动和严寒的天气。
《舌尖上的中国》拍摄现场
也许就因为有了这种观察,镜头下出现的藕夹显得异常美丽。本来上一个镜头还是说藕的孔中不能有泥浆,下一个镜头,就是肉沫夹进了藕孔中,成就了湖北特殊的美食藕夹。
新鲜的藕,有大把的藕丝,当地人吃的时候,一边吃一边用手把缠绕不清的丝给抓掉,这种场景让任长箴越发相信:离开产地,享受食物的乐趣就会大大减少,由享受食物,退化成了消费食物。
11月份,云南的井盐。新鲜出产的盐用来腌制当地的山猪肉,成就了诺邓火腿。井盐的熬制颇为费劲,可是用这种辅料,才能成就诺邓火腿那种扑鼻的香,遍布的脂肪层经过盐腌,油花才完美,做火腿的人并不觉得盐是便宜的配料,掉在地上的也会捡起来,然后再使用。他们一直觉得,诺邓的井盐是自然的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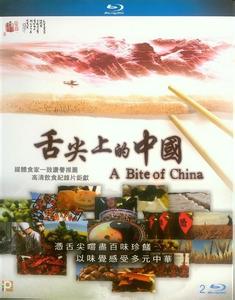
菜肴的物理和化学变化
因为是执行总导演,任长箴还得陪同自己队伍的新手一起去拍摄,比如第三集讲食物的化学转化,一开始的云南石屏豆腐,就是她和分集导演一起去的。那是一对淳朴的夫妻,本来的拍摄计划,也就是拍豆制品的转化,怎么发酵,怎么变得美味——中国是豆制品的发明大国,总有千奇百怪的场景值得拍摄。
可是,在拍摄中,任长箴的问题却是,做豆腐的每天那么早起来磨磨,一辈子都如此,那对夫妻中看起来明显精明的妻子,甘心吗?她把问题抛出来,本来不愿意说话的女主人一下子脸红了,话也多了,她内心的骄傲被激发了,尤其是丈夫说她全身都是优点的时候。后来在她们吃烤豆腐的时候,女主人甚至给她们唱了一首歌。不过,本集的导演是学生物出身,她对食物的把握有另外的感觉,比如在介绍黄山毛豆腐的时候,她的解说词是,这些毛豆腐上的毛看上去很像活的一样,事实上,它们就是活着的菌类,每时每刻都在生长变化。中国的豆制品种类丰富,从南到北都有自己的特点,如何让人不厌烦?显然就是靠各种豆制品的微妙差别,安徽的八公山豆腐靠的是质地的紧密;广东广西直接将黄豆做成豆豉,靠发酵产生的鲜味,再去提高主材料的鲜味——而北方的奶豆腐和云南的乳扇,则完全是另一种蛋白质的转化。中国食品之丰富,全在各地的制作者掌握的细节里。
比起化学变化,第四集“时间的味道”讲食物的物理变化更有趣:风干,烤干,腌,醉,渍,遍及全国,各地区用自己的方式保存食品,经过一冬的储藏,最后成就了各种口感和味道都变得与新鲜食物大不相同的新食物。
张铭欢是这集的导演,也是整个后期制作的总导演。他同样不是个对食物讲究的人,可是做完这一集,他对整个风干腌渍的食物有了感情:现在的人从健康考虑,越来越少地食用这些食品,是不是有一天这种食物会消失呢?
在他们拍摄之前,调查团队已经去了许多地方考察,并且告诉他什么地方的东西值得拍摄。不过走进湘西的大山里,他还是陡然明白了,为什么这里的腊鱼和腊肉特别美味。女主人公告诉他,这里的山路,怎么走也走不完,路太难走了,还给他回忆小时候母亲别一块腊肉在她身上,送她去上学的事情。“这些腊味就是当地环境的产物,因此也特别好吃,你说腌制过程有多复杂也未必,要说多讲究也不一定,可是,因为和山区的环境紧密联系,所以,哪怕是用萝卜干和辣椒简单地一炒,也能让我们吃几大碗饭。”
东北绥化的辣白菜也是如此。朝鲜族女主人公在北京生活,可是特别想念家乡的辣白菜,按道理,东北各地都有腌辣白菜的,可是他们最终选择了绥化,除了地形很美外,女主人公的家庭更让他们觉得舒服,一个最简单的腌泡菜过程,可是极有章法,纹丝不乱,做好的辣白菜卷在豆腐皮里食用,有种新鲜的好吃。
“每个人的性格,甚至都能反映到他做的腌制食物中。”在安徽黄山找到了制作臭鳜鱼的师傅,是个特别想把徽菜发扬光大的人,对自己有天然的自信。徽州的山多地少,徽州人想走出去的性格,在他身上特别有体现,他特别的投入,“他就是那种一心想把徽州菜带到外面的世界的人”。结果他做的臭鳜鱼,完全颠覆了编导们对臭的食品的印象。
不过,最大的发现,还是大城市里隐藏的美味。上海的醉蟹和香港的腊肠,是他们搜索的在现代化大都市里诞生的美味——腌腊食品并没有因为乡土变化而消失。在上海拍摄三阳南货店的时候,他们觉得有趣的是,在这么一个现代化都市里,人们却始终如一坚持购买最传统方式制造的火腿,而南货店的师傅也像个手艺人,一挑一捡,就能拿出最精华的火腿。更大的秘密是沈宏非帮他们找到的汪姐,这是一位家厨师傅,平时喜欢烧菜,朋友聚会也都是她做菜,慢慢地名声在外,开始小规模接待客人。可是去了她家,还是让张铭欢他们意外,到了蟹季,汪阿姨会买上几百只螃蟹回家做醉蟹。“更让我吃惊的,是她把螃蟹放在浴缸里涮,特别有一种成熟的厨娘的范儿。”
在香港中环找到的腊肠店也是这样。一片高楼大厦的丛林中,年轻的主人公阿千没有去做什么现代职业,而是老老实实做着腊味。他告诉他们,一个人做好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用心。所以他一直在极其骄傲地做着自己的腊肠,除了各道手艺的严谨外,用钉耙小心地在腊肠上扎孔,也让编导们印象非常深刻。
福建的紫菜,台湾的乌鱼子,包括大澳的老太太和丈夫做了一辈子的虾膏,这些食品之所以让人们牵挂,张铭欢觉得,主要还是因为都是“家乡的味道”。每份腌腊食品吃进嘴,最让人们唤醒的,还是童年的记忆和家乡的感觉——毫无疑问,这是中国人共同的集体记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