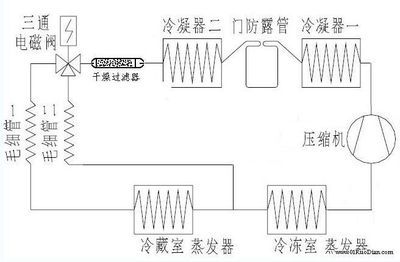据言中国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主流是“乡土文学”。即便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学”仍然没有发展起来,或是“城市文学”创作的成就仍抵不上“乡土文学”,抑或对“城市文学”的评价没有“乡土文学”高。凡此种种,至少在我们的批评史视野中,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关于“城市文学”的批评标准,或者是缺少充足的批评资源与批评经验去面对当下所谓的“城市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实不乏有关“城与人”的作品,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批评。例如赵园就曾在《北京:城与人》中,深入分析了“城”与文、与人的关系。也正如赵园所说的那样是要“借助于文学材料探究这座城、这座城的文化性格,以及这种性格在其民居中的具体体现”①。从老舍到邓友梅的创作,虽然都是围绕北京这座“城”来讲述,但这座“城”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城”,“城”中的人还远没有过上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生活。总体而言,在老舍、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等作家的笔下,北京这座城市所展现的还是老北京的“皇城根”文化。

这些讲述“城与人”的文本,并不是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城”与“人”,而是一种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市井文学”。这类“市井文学”侧重讲述的是市井中的人情冷暖、世间百态,往往带有“风情画”“风俗画”的意味。尽管这类“市井文学”讲述的时空均是“城市”,但这里的“城市”仅仅是一个在地理学意义上,与“乡土”相对的一个空间概念。在此,“城市”不具有一种“现代”意义或“文学”意义。虽然有论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关于“城市文学”的定义,“凡是写城市人、城市生活为主,传出城市风味、城市意识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为城市文学。”②但我们去回顾那些写城市、写城市生活的作品,它们所呈现的“总体性”特征,基本没有超出“乡土文学”所能触及的范围。从“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的转变,难的不是空间的变化,难的是文化意识的转变。在我看来,得以实现这一转变的基本前提便是传统生活样态的瓦解,城市生活样态的确立,也正如孟繁华所言的“新文明的崛起”。如果没有这一“新文明的崛起”,城市没有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文化形态,那么所谓的“城市文化”或者“城市文学”,其实质无非也还是“乡村的延伸,是乡村集镇的扩大。城市即使与乡村生活结构(并由此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不同,也同属于乡土中国,有文化同一”③。
二、“进城”:从城市题材,到城市文学?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大体有三次有关“进城”以及“进城”之后的文学叙事:第一次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经历了一次从“乡村”到“城市”的转移;第二次就是“文革”末期与“新时期”之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加强,乡土中国的人口开始向城市流动;再有就是20世纪末以及新世纪以来农民工进城。三次重要的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基本上都是单向性的,即由乡土中国向城市的流动。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前两次的“进城”基本上是“空间”意义上的转移,并没有在转移后的空间中构建起与“城市”有关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尤其是第二次基本上就是从乡土中国到城市的一次试探,结果还是退回到了乡土;第三次“进城”,是一次彻底的“融入”,是一种既不同于“乡土”,也不同于“城市”的体验。所谓“打工文学”讲述的既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农民”,也不是纯粹的“市民”,他是一种新的身份,一种新的体验。而这种新的身份与新的体验是由农民从乡土中国到城市后,与“城市”一起派生出来的。虽然这样一个新生事物,并不完全属于我们所理解的典型意义上的“城市”,但他已经融入现有的“城市生活”中去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自然革命取得成功后,要从�r村进入城市。这种日常生活空间的转移,必然也会影响到文学创作。在“十七年”时期,我们的文学史上就有一些关于“城市”的小说,准确地说应该是关于“城市题材”的小说。尽管一些学者去努力开掘其中所蕴含的“现代性”,“‘十七年’中国的城市现代性设计包含了三个方面:首先,必须排除口岸城市原有历史线索的多元性,寻找到城市历史起源与发展中的‘左翼’主导意义――也即社会主义的线索;其次,在城市现代性中,只有其符合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面才被许可存在;第三,城市的资本主义私人性、消费性的日常生活,必须被‘公共性’加以改造甚至铲除,以保障高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④持此论者,所描述的“十七年”间我们对于“城市”进行改造的进程所言不虚。但其中的核心概念“公共性”,它所指向的主要价值是国家的“工业化”,“工业题材小说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城市文学写作,因为首先,它反映的工业生产是一种现代化的工业大生产,是一种典型的城市现代性产物。虽然说工业题材小说中很少涉及城市的工业生产的功能,但它却明白无误地彰显出现代城市的工业生产的功能。”⑤我们知道,通常所谈及的“城市文学”,是与工业化的浪潮或进程有关,但“工业化”并不是其终极目标与终极价值。而“十七年”期间的“工业化”进程,所关注的重心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有时甚至为了这一目标反而要对“都市生活”或如一些论者所言的“资本主义”日常生活进行改造。如《我们夫妇之间》《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等小说讲述的就是这一类题材。在此,我们需要辨析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关系。“文学现代性”往往不是与“社会现代性”构成一种同步或正向关系的。“文学现代性”以“‘人’的自由,以人道去和社会现代性发生关系,是沿着人的价值这一线路和社会现代性相应,而不是跟在社会现代性的后面亦步亦趋做历史的工具”。⑥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十七年”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对既有的城市生活的改造,从民族/国家抑或“社会现代性”的层面而言,这是带有“历史进步性”的;但就文学更确切地说“城市文学”而言,这样的改造就不具有“文学现代性”,或者说这样一种“反城市的现代性”改造对于“城市文学”的发展来说显然是构成了一种破坏。
百度搜索“爱华网”,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爱华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