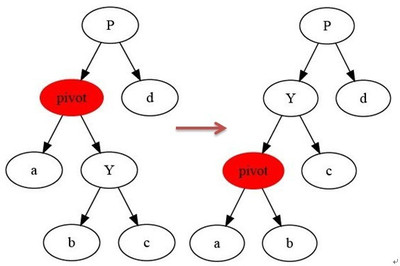▏谁去谁留
——给Maria
黄昏,那小男孩躲在一株植物里
偷听昆虫的内脏。他实际听到的
是昆虫以外的世界:比如,机器的内脏。
落日在男孩脚下滚动有如卡车轮子,
男孩的父亲是卡车司机,
卡车卸空了
停在旷野上。
父亲走到车外,被落日的一声不吭的美惊呆了。
他挂掉响不停的行动电话,
对男孩说:天边滚动的样样事物都有嘴唇,
但它们只对物自身说话,
只在这些话上建立耳朵和词。
男孩为否定那耳朵而偷听了别的耳朵。
他实际上不在听,
却意外听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听法——
那男孩发明了自己身上的聋,
他成了飞翔的、幻想的聋子。
会不会在凡人的落日后面
另有一个众声喧哗的神迹世界?

会不会另有一个人在听,另有一个落日在沉没?
哦,踉跄的天空
世界因没人接听的电话而异常安静。
机器和昆虫彼此没听见心跳,
植物也已连根拔起。
那小男孩的聋变成了风景,秩序,乡愁。
卡车开不动了,
父亲在埋头修理。
而母亲怀抱落日睡了一会,只是一会,
不知天之将黑,不知老之将至
作者 / 欧阳江河
一个小男孩在昆虫体内听到“机器的内脏”;他看到的落日也只是卡车黝黑的轮子。这样的世界其实无须偷听和窥探,它有自己的理直气壮。男孩倒像在玩游戏,就不知道到底是哪个世界在跟他捉迷藏。父亲带着卡车般被卸空的心(那些糙硬、沉重、笨拙、迟滞的“货物”暂时被挪移,但它们永远在路上流转),讶异于落日“一声不吭的美”。
在我们浪漫主义的想象中,大人和孩子为之着迷的这两个世界通常要调换一下。但或许父亲那被捆绑的现在正是孩子等待的将来——孩子有的是时间去怀抱去失落、去沉溺去逃离……所以父亲一本正经的训诫对孩子来说反而是另一重阻隔——“天边滚动的样样事物都有嘴唇,但它们只对物自身说话,只在这些话上建立耳朵和词。”宛如一串被移植的嘴唇、一行被挪用的词语,这种操之过急的诗意与哲理不仅无效,反而生硬地切断了起初那颇为流畅的电影镜头。
男孩仍照着自己昆虫般的本能,“意外”而自然地发现(而非“发明”,正如童年在文艺复兴时期也是被发现而非发明)“自己身上的聋”。即便万物都以各样方式敞开、诉说,我仍执意认命于自己内有的“聋”;即便“另有一个人在听,另有一个落日在沉没”,我们也彼此无份,就像在异次元空间,近得没有距离就是最远的距离,因为通道已关闭或从未开启(比如在《黑暗元素》里,在牛津同一座花园的同一张长凳上,两个主人公却永难相逢)。但那又怎样?或许小孩因无知而坦然,大人却被这异样的静寂和无形的嘴唇所搅扰——他不知道,鼎沸的人声同样是温存而长久的。
但这意外得来的世界不会持久。父亲必须埋头修理卡车以再次启程。男孩任性的聋则似乎哗哗哗前行了数年,变成了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风景,秩序,乡愁”。只有突兀的母亲毫不在意地“怀抱落日睡了一会,不知天之将黑,不知老之将至”,以为摆脱了时间永恒的捆绑。他们三个人是否也像散落在大地上的草籽,各自发芽,各自开花,“彼此没听见心跳”?
我所不解的是,为什么非得把世界这样决然地一分为二?为什么男孩非得“为否定那耳朵而偷听了别的耳朵”?为什么机器和昆虫非得“彼此没听见心跳”?为什么植物在此刻非得“连根拔起”?我们或行或止,看到的不是同一轮喧哗或沉静的落日?我们自己的心脏不是可以随时携带随处安放?我以为,真正的自由就在于——不必踌躇,你选择哪样都是正当、优美的,管它谁去谁留。
最后,为什么要在“踉跄的天空”之下,又让孩子做一回器皿,预先承载太多的“诗”与“哲学”?这首诗企图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寓言,但经验的鳞片覆盖了天真的毛孔,很美,但是不自在、不痛快。不如让寓意抽身而退,让世界成为它自己。
p.s.
小勺:为什么他们都把诗写得叫人看不懂?
调羹:看得懂就要被嘲笑,就像郭小川那样。看不懂就算被嘲笑,也嘲笑得无所适从!
小勺:我从不嘲笑诗歌,可仍然无所适从。
荐诗 / 匙河
2015/07/16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