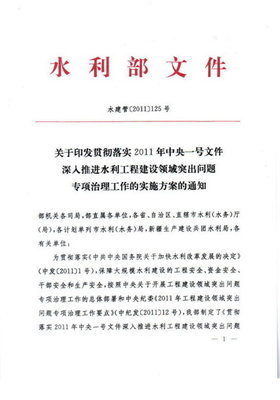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们这里的农田水利建设就拉开了序幕,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
我们公社七十年代最后两个大型的水利工程,就是至今为止依然雄踞全镇第一第二的两个大坝。我那时刚上高中,所谓的四人帮也是刚刚以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名被抓,举国上下还处在山呼海啸般高呼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深入揭批四人帮,全面抓纲之国的浓烈氛围中。
位于街区东北面四五里远的东大坝最先开工,开工仪式就在将建大坝的那个村子里举行。村子处在平地上,村子北面是类似黄土高原一样的大片黄土沟,公社决定在黄土沟一处缺口窄小处筑建拦水坝基,形成一个面积约二三百亩大的人工湖。
开幕式上,公社书记亲自主持并讲话,参加开工仪式的有高中全体师生、社直单位干部职工和全公社的三级干部。会场简朴而庄重,主席台设置在一个高高的土台子上,会场四周布满了那个时代激奋人心的标语,插满了猎猎飘扬的红旗。
会议开始后,各单位代表依次登台,大家慷慨激昂地宣读本单位的决心书。接着,大队与大队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相互宣读了挑战书和应战书。最后是公社书记讲话。
公社书记姓周,私下里全公社的人都叫他老周。其实他当书记的时候也就三十几岁,而老周这一称呼也伴随他十多年,大家一直这么叫他,感到很自然很随和很亲切,没有任何隔阂和何距离感。老周是军人出身,曾经是省委某副书记的警卫员,出身苦,受过难,打过仗,身上始终洋溢着一股使不完的劲儿。他文化水平不高,讲话时没有文绉绉的雅词丽句,全是群众耳熟能详又倍感亲切的大白话和方言土语,因此很受群众欢迎。
老周讲起话来声如洪钟,常常把高音喇叭震得吱吱响,惹得与会人员不时抬起手来揉耳朵。老周的讲话不长,但句句都说在实处,感染力很强,效果也很好。公社为建大坝,早就组织技术人员经过长时间的勘察论证,前期各项工作早就准备就绪,因此开工仪式的第二天,全公社就行动起来。
东大坝工程持续了将近一年就全部完工。我们在校的高中师生也参加劳动一个星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各突击队推拉车运土,有时候也负责往拉车上装土。实话说,人欢马叫的劳动工地上热闹异常。四周的沟坡上刷有硕大醒目的白色标语,高低错落五颜六色的彩旗迎风招展。人们推拉车时发出的声声快意呼叫,负责碾压土层的链轨拖拉机发出的不绝于耳的突突声,镢头铁锨挖土铲土时候碰撞在一起的铿锵声,交织在一起,宛如一首振奋人心的交响乐。从早到晚,除了吃饭和中间短暂的休息,这音响一直在演奏,一直在喧嚣,把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激奋得热血沸腾,干劲冲天。
工地上的劳动紧张而快活,群情振奋的劳动场面几乎把每一个人的潜能都无遮拦无保留地挖掘出来。虽然每一天收工之后,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都倍感劳累,可休息一晚后,第二天大家依然乐滋滋地奔向工地,继续着前一天的紧张与快乐。
东大坝工程告竣后,由于上游水源不是很足,以至于好几年了近看很大的水面,站在远处看上去仍然像一汪小坑塘。高二的时候,我们曾利用星期天相约到东大坝上玩,希望就近看看自己曾付出汗水的工程到底怎么样。那天,我们走下高坡,趋近水前,顿时感到东大坝实在了不起。那看似只在坝底的水面一眼望去,完全抵得上平日里见过的最大池塘的数十百倍。我们一边转悠一边感叹,要是这水能够蓄到三分之二多,那简直就是一个小西湖。
东大坝后来对下游大队的农业灌溉起到了不小作用,也成了我们这里最大的鱼类繁殖区和鹅鸭养殖场,直到今天依然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公社西边大坝筑建的时候,高考已经恢复,我们的全部时间都花费在了学习上,再也没有机会参与其中。至今想起来,心中不免仍略有遗憾。其实人生与事业的成功与否,真不在死死钻在温室里搞所谓的超强度修炼,适当地接触下社会人生,参与下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对所有知识分子和机关人员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只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一心希望建立的新型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之间无间关系的美好愿望,后来却成了一向自以好逸恶劳自视清高的精英知识分子们诟骂他的理由与借口。什么迫害知识分子啦,什么牛棚杂记啦,什么不尊重知识啦,至今想来,完全是一派胡言。那纯粹是旧知识分子们自视高邈的封建贵族等级思想在隐隐甚至泛滥作怪。实话说,在中国历史上,无论论学识渊博与哲学内涵,无论论文学素养和复合素质,有几个被虚抬为所谓的民国大师与精英,能与毛泽东比肩?无论论才华贡献,无论论个人所取得的科技成就,无论论对国家对人民所作的贡献,有哪个古今知识分子,能与钱学森、屠呦呦相提并论?
只有那些半瓶子的也不知道能否称得上三四流的所谓精英们,只有那些骨子里顽固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亮的奴才走狗们,才不加选择不加分析地仇视本民族伟人与文化,脚踮着附会西方文化并心甘情愿做它的附庸,才喜欢以所谓的什么大师欺世盗名,才把自己看得真的就可以俯仰天地,天下无敌了。

在筑建东西大坝之前,我们公社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就已经进展将近十年了。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留在记忆里最深的印象,就是大人们冬春时节大多时间全都奔忙在全公社各大队的水利工地上。公社书记老周那时候每逢开会,就要满怀信心地给大家描绘未来的宏伟蓝图:电杆成林线成网,条条渠道地上躺。电灯明亮马达响,自家门口洗衣裳。
我上小学三年级那一年,队里的壮劳力都去公社最西边一个大队的工地干活了,村子都只有妇幼老人在家。一段时间里,到处盛传着最近小偷多,专在夜里撬人家的门,胁迫在家的老人与孩子拿出自家最贵重的物品。消息传到工地上,又通过大队支书传到公社书记那里,公社马上组织人员调查各大队遭盗窃情况。调查的结果是,全公社几乎没有此类事情发生。工地上专门派人回各村给家里人传话,让大家放心,说那全是阶级敌人为了干扰抓革命促生产所造的谣。话虽这么说,可人们到底不放心,还是心有余悸。每天晚上,大家不似以往那样,吃过晚饭后走东家串西家地彻夜闲呱嗒。而是天刚黑,就匆匆吃了晚饭,一家家紧锁门户,悄然熄灯睡觉。
为了安抚留守在家的人们,使工地上的人能安心劳动,公社要求各村成立巡逻队打更值夜。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也编入其中,每天晚上带着手电筒,拿着火叉棍棒,跟在大人们身后满村子转悠。那段时间,各家睡觉前,也都用杠子牢牢顶住门,绝不允许有任何疏忽,给小偷以可乘之机。
可是巡逻队的人在寒冷的冬天和初春季节转悠了几个月,硬是没见到过甚至没听到过有小偷出现的事情。负责巡逻的人虽然紧张,但也难免有点失落,大家既不希望小偷出现,可忙碌这长时间连一个小偷的影子都没见到,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儿。可话说回来,能保证全村人安稳宽心,不遭受惊吓,咋着说也还是心存自豪的。
人们的紧张害怕也就是那短短的几个月,再后来,大家看到到处依然清平朗朗的,也就慢慢恢复了平静。巡逻队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各自卸甲归家,此后再无成立过。
七七年开春不久,远在二十几里外工地上的父亲,脖子上出了一串毒颗子。从工地上回来拉柴火粮食的人给母亲说了,母亲很挂心,却又脱不开身去工地上。一个星期天,西院江大从工地上回来后要去工地,母亲嘱咐我跟他一起看看父亲。第二天吃完早饭,我就跟着江大一起去工地了。
工地在我们村西北面那个最偏远的大队,那里地势高低不平,土方量很大,工程任务很艰巨。大队本来要让父亲回来休息几天,好好治病,等病好了再去工地。父亲执意不肯,说眼看就要完工了,任务紧,各生产队都在黑明连夜加班,这时候回去恐怕影响我们队里的过程进度。大队干部听了,便让队医每天按时给父亲换贴服的药,以便他能尽快恢复健康,不至于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
快晌午的时候,我和江大直接来到工地上,看到父亲后脖上围着一条厚毛巾,隐约可见贴敷的膏药露了出来。父亲的精神很好,见到我就说:多大点个毛病,根本用不着你们操心。大夫说这两天膏药一揭,就不用再贴了。
他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拿着铁锨往拉车上装土。那样子,一点都不像患病的人。我在工地上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要回去上学。临走,父亲对我说:回去就说我脖子上的颗子已经好了,不让你妈他们操心,过不了几天,这里的工程就全部完了,到时候就回去了。
那时候,生活条件已经有明显好转,各生产队年年都有充裕的粮食和资金供外出干活的人消费。工地上的生活远好于家里的生活,几乎天天都能吃到一顿肉面。在家里不常吃的好面馍,在工地上也是隔天都能吃到。
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到大队所在的水利工地上参加劳动。哪个生产队的学生就在哪个生产队住宿就餐。带队老师们由学校与大队协商,分散到各个生产队食宿。
那次的工地离家较近,约有七八里远,在我们村子的西南边,靠近一条公路。接连几天,我们跟着大人们一起干活,主要的任务就是为拉土车搭边捎。尽管我们年级小,气力弱,可大人一点也不嫌弃,都很热情地在车子把左右两边系上一个绳子,我们便和他们一起干起活来。大人们一边拉车,一边向我们询问学校里的事。爱吸烟的男劳力,都要在歇歇儿的时候,问我们,有用过的废纸没有。那时候,烟袋已经不为年轻一点的村人所使用,大家都喜欢拧一头大一头小的纸烟吸。拧纸烟最缺的就是纸,爱吸烟的人们也就常常从我们那里讨取用过的纸张。当然我们也不会让他们失望,不管多少都要想法给他们弄到一点。每当我们把废纸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显得很激动,接二连三地要说些感谢的话。那时候爱听瞎话的我还常用废纸和爱讲故事的西院三爷作交换,他答应只要每天给他十张烟纸,他每天晚上就给我讲两个瞎话。
工地上男女劳力都有,我的三个姐姐两个在工地上干活,一个在工地食堂做饭。每次收工后,走到吃饭处,做饭的三姐和小花姑都要偷偷在我的饭碗里多加一点肉,还悄声嘱咐我别让大家知道了,搞得我很不好意思。接连几天,她们几乎每顿饭都是如此。大姐和二姐还总是端着饭碗对我说:给你夹几块肉吧?我红着脸说:不要,我碗里有。她们哪知道我每次都在吃偏心饭。
那时候去工地干活,是不用强制谁的,大家都是争先恐后地去工地劳动。工地上不仅生活好,工分还高,环境又热闹,谁愿意呆在家里受那份清闲?
那次从工地劳动后回到学校,同学们都有说不出的依恋。过了很多天,还有人念叨:不知学校还让咱们再上工地干活不去?
我们后来又几次参加水里工地的劳动,其中有两次是学校单独安排的。有一次是在冬季,我们村子一里远的西北边上有一个二级提灌站,附近人们都叫二级站。二级站南有一条次主干渠,渠面直径大约有三百多米,渠深两三丈不等。由于渠道的护坡都是砸瓷了的土坡,我们这里的土质又是膨胀土,隔不了多久,坡上的土就会松散滚落到渠底。每一年,人们都要到渠上清淤,我们初中以上的学生也常参与其中。
那天我们带着铁锨和荆条筐来到渠边,看到渠底的水面上还结着一层薄冰,天依然很冷。站在渠坡上对着渠底用铁锨铲淤积的青泥,仅靠我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是不行的。那时候的人时刻都在受革命英雄主义的熏陶与教育,在任何时候都能即刻表现出一股英雄的豪气与行动。由于老师当时有事还没赶到,我们几个同学稍稍一议论,立即决定拖鞋下水,只有这样才能把沉积的淤泥全部挖出来。
说干就干,大家一不做二不休地坐到渠坡上,三下五去二就脱掉了鞋袜,相互搀扶着慢慢试探着往水里走。刺骨的寒冷顿时把每一个人都刺激得牙齿哆嗦,嘴也直打咧咧。说实话,在刚走进渠底的那一瞬间,每个人都有一种冰寒剜心的感觉。一时间大家愣愣站在淤泥里,一时还不能恢复过来精气神来。过了一两分钟,脚和腿部开始由冰棱刺疼变得慢慢火热起来,再一会儿,冰寒已经荡然无存,大家便开始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
没有踏进水里的同学,负责把挖出的青泥抬到岸上。处在水里的同学一边不停地挖青泥,一边无拘无束地说笑。等到老师忙完赶来的时候,我们班分的清淤任务已基本完成。老师很感动,狠狠地表扬了我们一回。回到学校,老师把我们的情况汇报到学校,学校特意在广播中予以表扬。所有参加清淤任务的同学都心里乐滋滋的,很像部队战役总结会上受到表彰奖励的战士一样,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与荣耀。
村子西北边的提灌站给附近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夏天,机房下面那口全是石头砌底砌壁砌沿的方形水坑,不仅是小孩们洗澡玩耍的乐园,更是妇女们洗衣的最佳去处。提灌站的机房在渠底部略高点的地方,三间清一色的纯青砖瓦房,两边山墙对开门,门全是当时流行于政府机关里的装心门。侧墙上全是窗户,窗户都是能开能关的玻璃窗,且全都装着钢筋立撑,同街上各机关里的房子模式一样。机房里依次摆满了抽水机器,门侧挂着不许闲人进入的警示牌,我们那时候都是绕房隔着窗玻璃向里面观望。
机房下面的那口方形大水坑是专门储蓄水的。天旱的时候,随着机房里一片轰鸣,水坑里的水便顺着渠坡东面的几根管道,被抽到机房上面约两三丈高的悬空渡槽里,渡槽全是由大石块切成。机房距离地面约一两丈高,地面距离渡槽约一丈多高。抽出的水流进渡槽后,缓缓地向北注入不远处的分岔渠道里,然后分别向北向东奔向周边各个村庄。
渡槽所用石块都是从南山里拉来的。那时我正上初中,上面安排每个初中学生有两车石块任务。我的石块是三姐跟我一起从南山拉回的。我家距离二级站最近,比其他同学要方便得多。
就在我们在拉石块的时候,曾发生过很惊险的一幕,至今想起来仍有点后怕。所有的石块都要到南山上的石料厂上拉,石料厂距二级站七八里远,公社派有专职民工在那里帮学生装石块,还负责把学生们拉石块的车子从山上放到山底下,学生们再顺着虽弯弯曲曲却基本平坦的土路往二级站拉。就在我们拉第二车的时候,车子一装好,负责给我们放车的是一位年龄二十多岁的黑皮肤大哥。他个不高,人长得很结实,也很和善。装车的时候,他一直跟我们有说有笑。谁知我们拉车后面用来护拦石块的兜绳,在车子行进到坡中间的时候突然崩断,车后面的那块大石头瞬间便滑落下去。车子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前把猛然着地,放车的大哥被巨大的惯性冲倒在地。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已经在劫难逃了,惊呼叫声立即响遍了石料厂。侥幸的是,车子双把落地后被下滑的惯性吃进了土里,拉车因此受到阻拦,便不再向下滑动,车上的石块也没有滚落。那位大哥人还算机灵,他一轱辘爬了起来,在人们的惊诧之中飞快跑到路边。所有的人都长长吁了一口气,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位大哥,只见他一脸侥幸逃脱后的窘笑,用手拍了拍身上的泥土,看着大家,连连感叹:我这是死里逃生啊,我这是死里逃生啊!要是车上的石块滚下来,要是车子继续往下飞跑,我有几个脑袋不会被砸死的?
我和三姐那一刻也是惊呆了,一直到那位大哥脱离了危险,我们还一直愣愣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稍停了一会儿,大哥缓过气来,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又把我们的拉车扶起来,慢慢把车子送到山底下。随后,他们又帮我们就近装上几块小一点的石头,我们才余惊未散地拉起车子,往二级站走去。
从那以后,我每次到二级站玩耍或者长大以后路过二级站,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位大哥,想起那令人惊悚不已的一幕。所谓的刻骨铭心记忆,在我这几十年中,那一次的经历就是一次。
在全公社完成最后两个东西大坝之后,水利基本建设就一直没有再行动。农闲的时候,人们只是做一些护理性的工作。全公社纵横交错的大小渠道,当时确实是我们公社一道最亮丽的风景。每逢旱天,各个提灌站就开始抽水,遍及全公社的大小沟渠里很快便流水潺潺。人们既利用这水灌溉有点枯萎的庄稼,也用这水灌满所有堰坑池塘。蓄满水的堰坑池塘可以确保人与牲畜的日常用水,干旱的庄稼在浇灌后立刻青葱枝楞,确保丰收无虞。完善配套的水利设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确保了农民旱涝保丰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据业内人士统计,仅我们一个公社,那时的人口不足四万,在文革中间建成的农田水利设施,按今天的市场价值估值,没有几十亿元是决然拿不下来的。可是那时候,就是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依靠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出的义务工和手中的简陋落后工具,硬是做出了在今天连想都不敢想的伟大壮举。
可惜的是,利国利民的文革水利工程,而今早已面目全非。交错有致的渠道被随意拦腰截断,被随意填平开发。开发者们以微小的投资饱受到执政者们的频频点赞与热捧。地方上引来的带有严重污染的所谓投资,远远抵不上他们毁坏的文革水利工程的深远价值。可是,造福于民的完善文革水利工程,至今依然被人骂作浩劫产物。而那些真正浩劫人民与子孙后代的高污染大排放企业的老板们,却在不断毁坏蚕食人民的财富之中,一个个腰缠亿万贯,满天飞奔。他,他们及其家人龟缩在一个个清明亮丽之地,消费着带血的钞票,安享清福。招引他们来发不义之财的地方官员们,也一个个家产日丰,加官晋爵,朱紱耀眼,成了受人追捧的改革精英。
永远难忘文革期间建设的水利工程,万分悲催它今日沦落的惨白面容。
2016.4.11
伏牛石 | 记忆:稻场往事
伏牛石 | 记忆:军属二伯
伏牛石 | 记忆:灯与火
伏牛石 | 记忆:村里的坑塘
伏牛石 | 记忆:石碾·石磨
伏牛石 | 记忆:广播·收音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