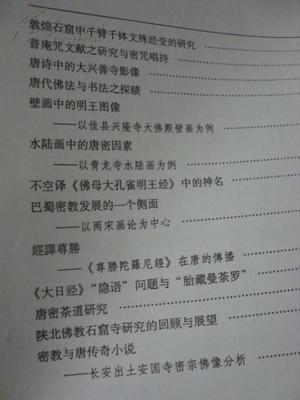周山详解老庄思想的现代意义:开拓进取与顺应自然
(著名学者周山在“楼观问道”论坛上发言)
凤凰网文化讯 2012年3月2日至7日,第一届“西安楼观中国老子文化节”暨西安楼观中国道文化展示区落成仪式在“天下第一福地”西安市楼观古镇盛大举行。3月2日上午9点,“楼观问道”文化论坛包括《道文化的现代诠释》主论坛在各界道教、两岸三地著名国学专家学者与政府官员共同参与下展开。上海社科院终身研究院周山发言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就在于重新发现传统精神的价值,今天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与阐发,首先是对老庄思想的挖掘与阐发。与前人看法不同,周山认为,老庄思想的现代意义除了“顺应自然”之外,更有“开拓进取”。以下为周山发言全文:
讲到中国传统文化,人们想到的似乎就是儒家文化;讲到弘扬传统文化,似乎就是儒学复兴。最近,有一位著名学者在上海的交通大学作题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意义》讲演时说: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文化价值体系;小传统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民间社会,体现在“三纲五常”等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就在于重新发现传统精神的价值,重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和谐。甚至还告诫人们不要轻言国学,“以中国传统为人立国之理观之,则只有《六经》可为'国学'”。其实,这样的认识有片面之嫌。细究起来,中国传统文化大致可以分为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两大系统,这两大文化系统各有源头、特征,相互之间又有很多交流和融合,形成了华夏文化的普遍属性。对这两大文化系统产生的源头,各自形成的标识特征、价值取向及其思想代表进行梳理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全面、深入的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不仅能为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逻辑合理性及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对于老庄思想作为长江文化的理论代表,在文化重心当代转移背景下的现代意义,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一、“择水而居”与中国文化两大系统的形成
人类文明的创造、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总是与水有着深厚的渊源。世界早已公认的古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两河文明”,就发生在西南亚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在中国,文明的肇始,文化的发生也同样与江河缠绕在一起,在江河的哺育中得以诞生和绵延并走向灿烂。究其原因,人类生活离不开水。“择水而居”,是江河成为古文化生长摇篮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人喜欢把大江大河称之为“母亲河”的缘故。
我不知道西南亚地区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文化有什么差异;但是我知道,中国的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是有差异的。我们能够知道这两个文化系统的差异,是因为这两种文化从诞生之时起,从未停止或间断过他们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共同创造了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我们把不间断的原因归功于华夏民族的文字,归功于我们的先人选择了从象形文字到会意文字的这一条文化发展路径。
二、黄河文化的源头、标识、轴心及其代表人物
黄河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期时代。根据二十世纪初以来九十多年时间里田野考古发现,黄河文化的形成主要与以下四个古文化系统有关,这四个古文化系统分别是: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其中,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地区,仰韶文化分布在黄河的上、中游地区,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田野考古工作者之所以把发生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作出四种类型的划分,是因为这些新石器文化存在着差异。无论是生人居住房屋或者死人墓葬的格式布局,还是日常生活所使用的陶铸瓦器的形制、纹饰等等,既富有黄河文化的色彩,又各有一定的特点。于是,二十世纪的田野考古学家便将每一类型的最早发现地,作为这类古文化的冠名。仰韶文化,就是 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发掘研究了河南仰韶村的新石器遗址之后,以该地村名命名的一类新石器文化。事实上,在此后自东向西的不断考古发掘中,从西安、宝鸡、兰州、西宁等地,也发现了与仰韶村发掘所见同一类型的新石器古文化遗址。
青铜器文化是新石器文化的延伸与发展。脱胎于仰韶等四大古文化的商、周青铜器文化标志着黄河文化已经趋于成熟。与青铜文化俱来的,不仅是祭祀或日用的青铜器具,还有铭刻在这些青铜器之上的精美文字,标志着黄河文化理念的青铜器形状特点、饰品图像等等,以及使用这些青铜器的礼制规范,等等。值得注意的还有:作为黄河文化的图腾形象标志的“龙”,以青铜器物上主要部件或图饰的形式,随着青铜器的日益发展,被进一步彰显,终于成为君王的形象代表。与青铜器的产生与发展的同时,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发生了三次重大转变。《易经》是夏、商、周三代的治国大纲。夏代的《易经》又称《连山》,以代表“山”的艮卦作为六十四卦之首,表达了这一时期先人对山的崇拜。商代的《易经》,又称为《归藏》,以代表土地的“坤”卦作为六十四卦之首,表达这一时期的先人对土地的崇拜。周代的《易经》,又称《周易》,以代表天的“乾”卦作为六十四卦之首,表达了这一时期的先人已经从对土地的崇拜转向对天的崇拜。在这一卦的爻辞中,作者以“龙”为喻,阐述了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从此,历朝历代的君王以“龙”自居。以“龙”自居的君王又称为“天子”。《周易》崇拜天,也就是崇拜龙。黄河文化发展到了周代,龙便成了图腾崇拜物。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不过,清代的龙崇拜,已经从“黄龙”变成了“青龙”。文化人对龙的崇拜,春秋末期的孔子可以算上一个。孔子在见到老子之后,向学生描述内心感受时这样说道:“我今天终于见到了龙。龙,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散开来成为一片文采,乘着云气翱翔于阴阳之间。”他无法表达对老聃的崇拜,只好用能够腾云驾雾、见首不见尾的神龙来形容他。
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从河南濮阳地区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墓穴中发现了用贝壳、卵石摆成的龙,距今大约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这一考古证明,青铜器时期成形的龙,周文化中居于至尊地位的龙,其实早在新石器文化中就已经清晰可观。
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四大古文化系统,到了青铜器时代即商、周时期,便形成了商文化与周文化。夏文化由于文字载体的无存,迄今人们还以为尚未运用文字。对于夏文化,人们的了解还很不够。在我看来,夏文化时期应该是一个运用文字的时代,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连山》的存在,很难理解治水成功之后称帝天下的大禹如何能治理偌大一个天下,很难理解到了商代一下子产生了刻画在龟板上、烧铸在青铜器上这许多令现代书法家也叹为观止的精美文字。
在充满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之沛然底气的土壤里,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承前启后,一路走来,最后止足于黄河下游的齐鲁之地,构筑完成了黄河文化的轴心。一个称名儒家的知识群体,在这片轴心之地上应运而生;这个知识群体的领军人物孔子与孟子,卓然成为黄河文化的代表。
生逢乱世的孔子,终其一生,都在极力主张“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一心要用“仁义”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要求人们以“亲亲之爱”为起点,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一座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仁爱”桥梁,并且还向人们描绘了一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残废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理想蓝图。后来的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人心本善”,不管你的心灵蒙受了多少灰尘污染,只要经常擦抹,自然能明心见性,恢复善的光亮,人人皆可成仁成圣。
由孔、孟共同构建的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成为华夏文化的一大标帜。这个被称之为“五行”学说的文化系统,在汉代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可,从此成为华夏人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规范、制约的作用。
三、长江文化的源头、标帜、轴心及其代表人物
在黄河流域产生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等的同时,曾经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其实也在产生着一个又一个文化圈。据已经发掘出来的古文化遗址告诉我们,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四大古文化系统,自西向东分别是: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和良渚文化。其中,大溪文化分布在长江上游偏下地区,屈家岭文化分布在长江中游,青莲岗文化与良渚文化分布于长江三角洲。与良渚文化相邻的还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最近二十年长江流域青铜器的不断发掘面世,彻底改变了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古文化底气不足的观点。尤其是在四川广汉地区“三星堆”遗址中发掘出来的上千件青铜器,不仅证实了长江文化的悠久历史,也向我们展示了长江文化的标帜特征。
据考古专家分析,“三星堆”已经发掘的二个坑,一号坑相当于殷商早期,二号坑相当于殷商晚期。这就从时间上表明,在黄河文化发展到了青铜器高度文明的同时,长江文化也已经有了青铜器文明的高度发展。从文化特征上看,这一时期的黄河文化是以龙作为主体的图腾文化,而长江文化则是以鸟为主体的图腾文化。“三星堆”的上千件青铜器给我们营造了一片鸟的文化氛围。有一株最引人注目的青铜器神树,高达十几米,每一层的分叉枝头都站立着一只青铜神鸟;在众鸟的下方的树根部,攀援着一条尾朝上头朝下的神龙。长江文化中的鸟与龙的地位,在这里得到了体现。除了树上站着的鸟,坑之中还有许多神态、形态各异的鸟,以及人首鸟身,人身鸟爪等青铜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中的青铜人面像的眼睛,均为细长而上翘,而与黄河文化中的人像眼睛呈圆状的情形不同。有人认为,“三星堆”的眼睛形状,与波斯人相似,并由此推测“三星堆”文化是一个受到西方波斯文化影响的产物。其实不然。“三星堆”青铜人物眼睛的形状,就是长江文化中常说的“凤目”。凤凰为百鸟之王,青铜人眼的造型取材于“凤目”,正是长江文化以鸟为主要崇拜物的必然选择。今天,当我们走进“三星堆”博物馆,便会感觉到进入了一个鸟的王国,一股浓浓的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就是长江文化的特有标帜 。
前些年,在成都的杜甫草堂附近,又发现了一个被称之为“金沙滩遗址”的商代时期古文化遗址,许多青铜器都以鸟形为其装饰特征,尤以金质的“太阳神鸟”为其核心代表。
如果把“三星堆”、“金沙滩遗址”作为长江文化的一个区域性代表即巴蜀文化的典型代表,那么,除此之外的长江文化还有两大重镇,这就是荆楚文化与吴越文化。就地理位置而言,荆楚文化以屈家岭文化为其历史背景,吴越文化则以青莲岗、良渚、河姆渡、马家浜等古文化为其历史背景。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是长江文化发展到青铜时代形成的三大代表,而以荆楚文化为轴心。
文化是人创造的。荆楚文化能成为长江文化的轴心,与荆楚人的开拓进取精神分不开。我们翻开战国时期的历史地图可以看到,楚国的地域面积,几乎与中原地区的齐、鲁、韩、魏、赵、宋等诸侯国加在一起的面积相等。中原地区这些国家,都是周天子分封赏与的土地,楚国则是楚人自己开拓出来的疆土。荆楚人的开拓进取精神,为长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吴越文化作为长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开拓创新精神,随着时代的前进越来越突出。吴越文化开拓创新精神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于青莲岗、河姆渡、良渚等古文化底蕴,另一方面来自于移民群体的自身素质。吴越东临大海,长江三角洲大片土地为冲积沙地。从荆楚一带沿着长江一路迁徙过来开垦沙地的民众,天生具有吃苦耐劳的开拓精神。吴国的开创者“吴泰伯”,本是周文王的伯父,自愿放弃父辈祖业,率领自己的部属长途跋涉来到长江三角洲,与大批来自荆楚之地的民众一起,筚路蓝缕,开创基业。所以,吴国是唯一一个属于周王室成员却不是周天子封赏的诸侯国。作为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吴国,一度称雄诸侯也就不足为奇了。根据地下发掘出的古文化遗址来看,一向被视为南蛮的“吴越”其古文化底蕴似乎最为充沛,然而后来的文化发展信息,却又突然中断。我们从河姆渡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鸟图腾崇拜的器物,仅鸟形牙雕就有6件,如鸟纹碟形器、鸟形匕首、双鸟纹骨匕。在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大量的鸟形玉饰。进入青铜时代,鸟文化的特征日益明显。丹徒母子墩西周青铜墓出土双飞鸟盖双耳壶,绍兴306号战国墓中出土的一件铜屋模型、屋顶上铸一只大尾鸠。
不仅如此,吴越还有一种特殊的“鸟书”文字,在每一个篆字旁边都有鸟形文饰,例如,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就有“越王鸠浅(勾践)自作用鐱(剑)”八个鸟篆铭文。吴越人与巴蜀人一样崇拜鸟,是因为鸟具有大自然里自由飞翔的特点。吴越人、巴蜀人把对自由与发展的向往,寄托在了鸟身上。
到了战国中期,这种“鸟文化”理念,终于在《庄子》一书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庄子讲了这样一个关于鸟的故事,有一只鸟,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直上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向南方飞去)。明代学者认为,鹏即凤。一只硕大无比的凤,一怒冲天,在云层之上,毫无阻挡地由北往南自由飞翔。其寓意,正是巴蜀人、吴越人一直未能明白表达出来的希望有一个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开拓进取的生存环境。大鹏鸟由北向南飞行,最后“徙于南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按战国中期的五色方位观念,北方为水,其色为黑;南方为火,其色为赤。由北往南,亦即由黑暗向光明。为什么北方的生存状态很黑暗?因为北方的黄河文化主张以“仁义”来唤醒人的良知,用“礼仪”来规范人的行为。为什么南方生存前景很光明?因为长江文化主张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提倡顺应自然的生活。
庄子的逍遥即顺应自然的思想,源自于他的前辈,另一位长江文化代表人物老聃。老聃是一位具有大智慧的学者,他把自己的智慧投向了宇宙生成的思考上面,认为天地之先还有一个“道”存在。“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道不明,只是恍兮惚兮而已,却正是由于它的作用,才有了天、地;有了天地才有了人与万物。由于这样一种因缘关系,所以他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更高于道的最高法则。老聃认为,一切行为做事,都要遵循自然法则。以治国为例,“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要像烹饪小鱼一样,小心翼翼,不能搅动它。在他看来,造成春秋末期礼崩乐坏战乱不止的根本原因是国君喜欢玩弄权术,干扰民众正常生活;一旦有了军事实力,大国强国就产生争雄图霸之心。所以,他认为合乎自然的治天下之法应该是“小国寡民”;国家小、人口少,就不会产生图霸之念。“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百姓就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反之,国家大、人口多,不仅国与国之间关系要复杂化,一国之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复杂化。一旦礼崩乐坏,再用“仁义”去教化,就好比敲着大鼓去追捕已经迷失做人方向的罪犯一样,不可能达到目的了。
老聃与庄子,将其顺应自然,开拓进取的理念,注入长江文化的内涵,使长江文化在理论层面上有别于黄河文化,而成为华夏文化中的又一个个性鲜明的文化系统。
四、中国文化重心的当代转移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虽然是属于两种各有特点的文化系统,但是这两种文化从其源头开始,便有着相互交流与渗透。早在新石器时期,属于黄河文化主流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向南伸延,与长江文化系统的屈家岭文化向北伸延,相互交错,在淮河上游地区形成了三种古文化并存的局面。龙山文化不仅东延至黄河下游,而且南伸至长江下游地区,与青莲岗文化交错共存。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也南伸至江苏北部,与青莲岗文化在淮河下游汇聚。到了青铜器时期,南、北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流与渗透更加广泛与深入,尤其是吴越地区,不仅笑纳楚文化的影响,而且大胆接纳、引进黄河文化系统的贤能之士。来自黄河上游的泰伯,自然也带来了黄河文化,在吴地不但受到了欢迎,而且成为吴国的领袖。齐国的著名军事家孙武,受到了吴王的重用;他改革图强的思想,尤其是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建议,也受到了吴王的重视。吴、越相继成就春秋霸业,与思想观念开放,善于吸收不同地区包括黄河文化中的先进思想有很大关系。
尽管如此,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间的差异仍然很明显。《庄子》一书中,有两处讲述了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尽显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差异。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不以为然,给孔子讲了一个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泉水干涸,一群鱼被困于陆地,便用湿气互相嘘吸,用口沫互相湿润。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里,甚至当灭顶之灾来临之际,能够将一丝生的希望留给他人。“相濡以沫”形象地体现了黄河文化的代表孔子、孟子所倡导的“仁义”关怀。长江文化的代表则认为,还有比“仁义”关怀更好的存在方式,就是“相忘于江湖”。在江湖中生存的鱼,不会想到用“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方式关怀其它个体。在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生存状态良好的社会里,人们同样会忘掉“仁义”,因为任何人都 生活得很好,无需别人的关心帮助。老聃、庄周所憧憬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不是主张“仁义”关怀的社会,而是一个完全按照自然规律构建、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而无需“仁义”关怀的社会。在他们看来,凡是特别需要“仁义”教化和关怀的社会一定是一个生存环境很糟糕的社会,而“仁义”教化被淡忘,甚至无需仁义关怀的社会,一定是生存环境良好的健康社会。因此,老聃认为孔子的“仁义”教化,“若负建鼓而求亡子”,敲锣打鼓追寻迷途逆子,注定不会如愿以偿。
“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的争论,成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核心话题。这场关乎两种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争论,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汉武帝一锤定音,选择了“相濡以沫”的儒术,成为治理天下的主流文化。此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黄河文化一直成为华夏文化的重心所在,孔孟思想作为官方话语,规范、制约着华夏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封建统治者选择黄河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心,与其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一致。甚至自西汉、东汉及其以后的唐、宋、元、明、清等各个王朝的都城,均选择在黄河两岸,也与选择黄河文化作为中国文化重心高度一致。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物质与精神如此步调一致,显然包含者历史的必然性。
在黄河文化居于重心和主导地位的两千年时间里,长江文化依然存在,依然发生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个广泛流传于吴越地区的爱情悲剧,正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矛盾冲突的典型例子。梁、祝爱情,是一种发乎内心的真情,顺应自然的表达。然而在黄河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这种顺应自然的表达方式必然要遭受压抑。梁、祝悲剧的必然性,就在这里。所以吴越人编演的梁祝悲剧,可以看作是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一次谴责与抗争。
历史车轮驶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局面终于来临。新文化运动的涌现,“五四”运动的发生,“打孔家店”旗帜的高扬,标志着中国文化的重心,开始由黄河文化向长江文化转移。
把“五四”运动仅仅作为年轻人接受新思潮洗礼之后的一次冲动,把“五四”作为青年人的节日,我觉得还远远不够。“五四”新文化运动承载的是整个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华夏民族文化观念的一次重大历史性转变,是将整个民族文化从“相濡以沫”的观念转向“相忘于江湖”的观念。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将直接规范、制约中华民族以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历程。

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5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火烧圆明园、1894年甲午战争,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向中国政府索赔近10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一次又一次提醒着华夏子孙,“相濡以沫”的观念已经过时。生物学家达尔文揭示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斗争法则,在人类社会同样存在。严复译介的达尔文进化论,引起了轰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惊醒了在“相濡以沫”梦中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华夏子孙。只有“法自然”,在开拓中创新,才能真正改善华夏民族的生存环境,提高华夏民族的生存能力,实现“相忘于江湖”的理想生活。
新文化运动开始了,推动这次文化重心转移的先驱人物,绝大多数是长江文化圈内的知识精英,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继新文化运动之后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前仆后继的政治家,也大多来自于长江文化圈中。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观念的转变已经落实到了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的转变。华夏民族终于在文化重心的转移中开始复兴。
五、老庄思想的现代意义
在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今天,作为长江文化代表的老庄思想的现代意义,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挖掘与阐发:
1、开拓进取。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刻意挤兑道家,以致长江文化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的思想一度遭到曲解,甚至其身份也受到怀疑,老子成了末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老子》一书为秦汉年间的杂凑作品,庄子也成了不思进取的隐士文化代表,等等。今天,当我们摈弃偏见,重新挖掘其思想价值时,看到的恰恰是陈见的对立面,开拓进取是老、庄思想的主旋律。老子理想中的“圣人”,应该具有方正、廉洁、正直、透明的品性,而又能把握“不割”、“不刿”、“不肆”、“不耀”的分寸。他主张“无为”,是为了实现“无不为”。庄子给世人讲的第一个故事,是由鲲化生的大鹏鸟,“扶摇直上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徙于南溟”。胸无大志的燕雀在树丛中跳跃,讥笑大鹏的高瞻远瞩、开拓进取;如同后世的第一位农民领袖陈胜,在遭遇世人讥笑之后的一声长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庄子开拓进取的鸿鹄之志,居然被满腹经纶的儒士们曲解了二千多年,反而是农民领袖陈胜成为其知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开拓进取的思想,正是我们首先需要挖掘和阐发的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之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2、顺应自然。自然,是长江文化的最高范畴。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之道,都要遵循自然,何况人类的行为举事?“治大国若烹小鲜”,说的正是顺应自然之理 :小鱼肉嫩易碎,油烹时必须小心翼翼,切忌频繁翻动;大国人众,尾大难调,政策稳定为第一要务。一大一小,顺应自然的原则却一样。《庄子·养生主》是从养生角度讲顺应自然的好处。首先讲了一个厨师解剖牛的故事:庖丁解牛,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彼节气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正因为遵顺自然之理解剖牛,所以他手中那把牛刀,历时十九年、解牛数千头,“刀刃若新发于硎”。而不遵循自然之理解牛的厨子,短则一月长则一年,都要换新刀。庖丁解牛的本意,顺应自然为养生的最高境界。顺应自然作为长江文化的一个核心价值理念,庖丁解牛的现代意义不仅在养生之道,也在为人之道、为政之道。例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相互间的矛盾、摩擦难免发生。如果能从矛盾中找到化解矛盾的空间,全神贯注,以“无厚入有间”的方式予以解决,既维持了社会环境的和谐,又避免了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所引起的心理伤害。就工作、事业而言,顺应自然,游刃有余,是人人都祈盼的理想状态。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鞠躬尽瘁”却被作为典范提倡,自诸葛亮始,几乎成为身居高位者的座右铭。而在历史上,鞠躬尽瘁的结果往往是悲剧;诸葛亮鞠躬尽瘁的结果是三足鼎立中的蜀国第一个出局。我们并不否认鞠躬尽瘁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但是与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工作效率相比较,后者更可取。因此,当我们在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的时候,理应优先选取“庖丁解牛”这一类“顺应自然”的文化元素,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改变观念;既要尊重“鞠躬尽瘁”的传统美德,更要注重选拔那些具有“顺应自然”的理念、能够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地开展工作的人才,走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是新时代的呼唤,也是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
3、和谐社会。和谐的本义是指不同音阶之间的协调。引伸到人类社会,指人与人之间、阶层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在有着多元文化悠久历史的中国,和谐社会的目标一致,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与方法则有不同。
老子主张通过“柔”与“后”的途径和方法实现社会的和谐。他的为人处世原则:方正而要自然,廉洁而不伤人,正直但不能无所顾忌,光明但要内敛。人的刚性有了柔性配合,人际关系才能和谐。用柔的目的,不仅在协调关系,更在成就事业,“柔弱胜刚强”,是一个普遍现象,例如,“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柔性的善用,又往往表现为“后”或“下”,用另一个词表达叫作“不争”。他用至柔之水作譬:“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与世无争不是消极退避,而是追求和谐,也是“厚德载物”的一种表达。在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中,他主张通过“下”即谦下的途径实现和谐:大国对小国谦下,便可取得小国的信赖;小国对大国谦下,便可取得大国的信任。在大、小国关系中,主动权在大国,所以,“大者宜为下”。老子这种协调国际关系、营造和谐世界的理念和方法,在国际关系普遍紧张、少数大国强国任意干涉别国内政颠复小国政权的今天,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结语:
三十年改革开放,是中国文化重心完成现代转移之后的必然结果;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社会构建,是长江文化的现代表达。
所以,今天的“国学”,首先是老庄道学;今天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与阐发,首先是对老庄思想的挖掘与阐发。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 周山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