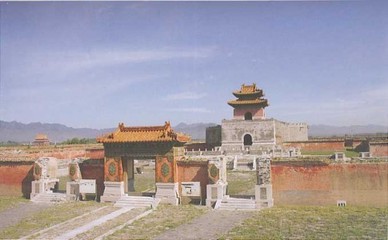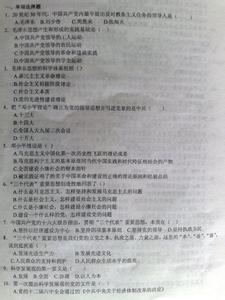近读中央文献版《真实的毛泽东》,有些感慨。因为这本书的几位作者和编者都有些特殊,一其中就有毛泽东的满女儿李讷,还有另外两位都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子女高风与叶丽亚,因此,一清对于书中所记,是以“信笔”相认的。内中有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也是毛泽东晚年白内障摘除者唐由之的一段回忆。不妨摘之于此:
(为毛泽东做手术的唐由之等一批医生与毛泽东主席合影。)
正如“一清二白讲历史”在《运去英雄不自由,毛泽东暮年的六大铭心之痛》里所写,毛泽东晚年内心是十分苦楚的。栏杆拍遍无人会断鸿声里看吴钩,这是毛泽东常有的一种心态。“运去”英雄不自由,“时来”只成昨日梦,也是毛泽东时时必须面对的现实。所以,当他面对着南宋词人《登多景楼》所呈现的情景时,不免百箭穿胸,心肠痛彻。陈亮的词里写了些什么?毛泽东又因此想了些什么?我们先看看陈词——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陈亮是南宋爱国词人,一生所写诗文几乎都与抗金有关。词的上阕,写登上高楼四处眺望观察战时形势所生的感慨。在作者看来,这一面临江、三面环山的地形,正好是进取中原、北上争雄的有利条件,而南朝历代的统治阶级为何却不思进取,醉心于江左偏安?他们无非都是为了各自的私利罢了。词的下阕更是点题指斥,气闷于心。词中“因笑王谢诸人”的王谢,是泛指当时那些有声望地位的士大夫们。他嘲笑这些人,虽然也学得像英雄那样感叹山河变异,但只知道泛论空谈,却无能去收复那充满了腥膻之气的敌占区。
毛泽东读到这首词时为什么痛切心扉,大哭不已?一则是人入暮年,感情难以控制,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再“常情”,也要有引起其痛哭的原因。我们细细品味这一首词,是不难找到些许的因由的。
(主席确实是老了,但作为主席,他得时时握住来自各地友谊的双手。)
毛泽东的这一次哭,具体时间是1975年的7月28日,5天前,刚好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也就是说,这是毛泽东做完手术后的第一次自己用眼的“阅读”。光明世界突然回到毛泽东的眼前,并且亲眼看到了这些已经隔离经年的古词人的文字,毛泽东心里难免不有隔世之叹。据中央文献版《毛泽东传》记载,1975年5月起,陆续有一大批的冤假错案呈现在他的面前,需要他一件件的批处。看到有些材料所记录的悲惨景况,毛泽东内心很难平静。当时毛泽东的白内障还没有摘除,他是戴着眼镜艰难地想看又看不下去,只得由他人代读,以听其详。特别是贺龙之女写来的关于其父所受迫害的报告,他强忍着听完了,内心十分难过。“毛泽东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里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毛泽东传》第1741页)
毛泽东哭了。哭在手术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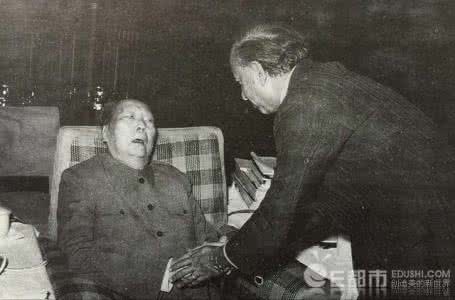
手术之后,毛泽东除了上文唐由之所记的“哭”,还有过另外几次,一次是在看完《雷锋》和《自有后来人》后,毛泽东泪流不止,哭声凄切。另一次是听说某个曾经在他身边服务过的工作人员被打成了反革命,在东北艰苦地撑着生活,病了也无钱治病。毛泽东听后,泪流不止,要求有关方面能多少给些照顾。
1975年,毛泽东的情绪多次失控,还与一些天灾等因素有着。那一年的夏天,河南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全省有三十多个县市受严重灾害,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一天,工作人员在给毛泽东读内部报告,读到有多少群众丧生时,工作人员忽然听到了饮泣之声。“这才发现,毛泽东的眼中早已浸满了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同上,1747页)毛泽东与常人一样,“伤心”的结果就是哭,痛哭!
让我们再回到陈亮的词上来,应该会对毛泽东之“哭”有所理解了。
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什么是毛泽东的“伤心处”呢?想想纷至沓来要求处理的冤情陈案,想想纷争不断的现实政治,毛泽东内心里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是痛苦十人的。毛泽东不得不在手术前的7月14日找江青谈话,要她对文艺界的人士放一马,不要“动不动就把他们关起来”;毛泽东又不得不在手术后的第2天即7月25日,在手术纱布还没有摘除的情况下对《创业》作出指示,并抖抖索索地写了6页的批语。毛泽东这时已经是个风烛残年的老者,想想自己回天乏力的处境、困境,难免不有“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的酸心感叹啊!
(从此之后,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宾,他的体能已经超支太多了。)
熟悉中国当代史的一些读者应该知道,毛泽东在进入晚年后,内心的变化是很复杂的,由于结束不了的运动,由于人事的变迁,也由于世界格局的深度博弈,毛泽东的精力已经不敷其用了,太多的付出,是一种自折其寿的消耗。毛泽东准备好好地读些书,以增加精神的充实与元气的修补。从1972年10月起,为毛泽东服务的知识分子队伍里,组建了一个“大字本读物注释小组”,就是把毛泽东想重温的一些古文古词,重新注释起来。由于这时的毛泽东眼睛白内障病痛很严重,一般的小字认读不出来,只好将印刷本字体放大,这就是所谓的“大字本”。大字本出来后,毛泽东读过很多与当时心境有关的文章诗赋,如《枯树赋》、《别赋》,又如晋书《谢安传》、《桓伊传》等。如下面陆游的四首词,就是“大字本”中的:
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 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处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
——《渔家傲.寄仲高》
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 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萍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
——《鹊桥仙》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诉衷情》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示儿》
(寄托着毛泽东期望的大儿子,而今牺牲在朝鲜战场,是父亲,都会心肠痛裂。)
不要说心境凄苦的毛泽东,便是我们今天读这样的词,又何尝不悲凉顿起,生出“鬓丝茶烟”之叹?这些词境里,大多是“愁无寐”“流清泪”“作渔父”、“寻兄弟”,“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毛泽东难免不与陆游一般,叹自己“心在天山”而“身老沧洲”。86岁的陆游临终有“示儿”诗自述“悲”痛:“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毛泽东焉能不有同“悲”之痛?读庾信的《枯树赋》毛泽东以“树犹如此”而感念“人何以堪”,悲从心来,况乎陆诗的“示儿”悲愤?毛泽东也是“死去”之时日近,而“九洲”殊异,国土分裂未归。谁成“王师”,何日家祭?想想几百年前的陆游临终还有“儿”可“示”,而毛泽东呢?毛泽东去世后,在清理中南海他的住所时,发现了一套整齐地摆放在一个任何人都不可轻易触碰的地方的一身衣服,那是毛泽东的大儿子在去朝鲜作战临走时脱在家中的一身旧衣。毛岸英不久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毛泽东内心里掩饰着巨大的悲痛,一直,他将带有儿子体味气息的衣服珍藏了下来,这才是毛泽东的内心之殇之痛啊。毛泽东自知在日无多,他当然希望在他“走”后国家好,人民好,“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痛啊!(转载自一清老师公众号)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