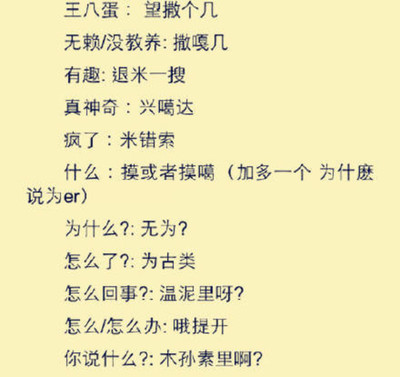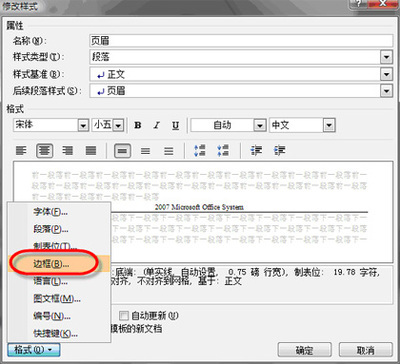日剧《半泽直树》去年创下超高收视率,堺雅人跃身成为“收视率男”。其实雅人叔已经演了21年戏,但一直默默无闻,并与家人断绝来往。最困难时,“为了养活自己,我到甜甜圈店打工、当快递员,那时候什么都要省,还在路边摘蒲公英沾黑醋吃。”
雅人叔也是个爱书之人,书籍几乎陪伴了他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爱读更爱写,04年到09年期间,他陆陆续续创作了随笔五十多篇,便有了《文·堺雅人》。
这本书算是他某种形式上的自传,据说他至今创作不用电脑坚持手写。有时是在演员休息室,但大多数文字在咖啡馆写就。书籍零零散散地写着他的观察、感悟、回忆,回忆学生时代时,他写道“在班上,自己从来都是坐在角落一言不发的那类人,经过三年大概还有很多老师根本不记得这样一个学生,不管再怎样被批评为[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却还是无力改变现状。”
也有写到中国:“因为电视剧的拍摄我来到了上海。在中国的工作的话,是三年前西安以来的工作。西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饭菜实在是太好吃了】,这次的情形也没有改变。即便有点难以说出口,我对上海印象最深刻的是,【饭菜实在是太好吃了】。在停留的五天内我发胖了四公斤。”
摘录了《文·堺雅人》一书中的三篇文章:
《始》
「1988年」对我就读的宫崎县立高中而言,是值得纪念的一年。
那年,母校的棒球队首度在夏天的甲子园大赛登场。
那是我入学前一年的盛事。
闯进甲子园大赛对于地方一般公立高中可说是不得了的大事呢。
具纪念性的「1988年」,其他社团或当时的考生都拼劲十足。
那年似乎是全校相当活跃的一年。
话虽如此,当时未入学的我们当然无从得知这些事。
身为新生,偶尔会从学长姐或老师口中得知「1988年」的往日回忆。
每当听到这些事,我总会将东京奥运和日后的高度经济成长联想在一起。
我入学的那一年(即1989年),一开始便抱持着这样的心境,
校园中更荡漾着一股莫名的期待感。
今年毫无任何预想,亦没发生令人心跳加速的事,
纯粹是期待感在作祟罢了。
宛若等待着大量的残火再度熊熊燃烧般不可思议的气氛。
(可惜的是,新火种未燃起希望,绚灿过后,又趋于平静。)
彷佛祭典过后,余兴犹存的一年。
1989年对我的母校而言就是这种涵义。
辗转过了近20年,直到现在,一想起「1989年」的春天,
就像漫天飞扬之物在坠地前一刻那种轻飘飘的无重力感,飘邈不定。
亦可说是,春天或多或少让人产生此种情怀也说不定。
但也许原因来得更单纯,吵杂的来源就是工程吧。
几年前学校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校舍改建,那时工程正好快大功告成。
由于工程每天持续进行,空气中总是尘土飞扬,噪音不绝于耳。
工程车辆时常在校园中进出,看到工作人员的机率远比教职员来得高呢。
校内处处可见禁止进入的标志,感觉上学校只是个暂居之地。
旧校舍围上了黄色的封条,建筑一一被拆除破坏。
看不习惯的建筑物飘着一股新粉刷过的油漆味。
才刚熟悉的风景时时在变,拜此所赐,
无论过了多久,我仍抓不住学校的全貌。
问了高中同年级的友人,根本没有人把「1989年」的春天记得一清二楚。
就像处于再造阶段的街坊,当时的风貌如何,任凭一个路人也没印象的道理一样。
路过的人们图一时方便,经过让时间“一时静止”的工程现场。
反正,不消多久就会出现新的风貌,
没有人有闲情特别停下脚步,一赌其风景。
在新建筑物完工,街坊的时间又再度跃动起来之前,
对眼前的景色完全“视而不见”。
工程期间所发生的两三事,或许会在几个人的心中留下短暂而片段的回忆,
但记忆终究像拍掉的木屑般荡然无存。
毕业之后,我再也没造访过母校,想当然那年的春天痕迹亦不复存在。
如同被吹散的木屑一样。
1989年春天,探访着小小的文化社团的我参观了话剧社。
话虽如此,我并非要参加话剧社。
倒不如说只要是温馨的文化社团,来者不拘。
对毕业于小小中学的我而言,
在这变化无穷的大学校之中备感威胁。
我想我很渴望有个可以喘口气,只有自己人的归属地。
原本盘算好要参观几个社团,却偏偏找不到重要的话剧社,
在寻找的过程中耗费了不少心力。
由于校舍改建,小而温馨的话剧社几度迁移,
大部分的学生根本不晓得学校有话剧社呢。
问了几位学长姐,总算得知话剧社的活动室位于校园东边的一角。
放学后,首度造访话剧社当天,直到现在,我仍记忆犹新呢。
在整体印象模糊那年的春日回忆中,这是唯一清晰的情景也说不定。
我来到了一栋老旧残破的建筑物前。
那是静静矗立于校园建地东边的某个角落,木造的一楼建筑。
里头有服装、烹饪等教室,被称之为「家政大楼」。
对我这样的男学生而言,家政大楼是绝缘之地。
若非逢此佳机,直到毕业的三年间,说不定我根本不会踏进那里一步呢。
那里的教室似乎不再授课使用了,周遭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校舍周围贴满禁止进入的封条,我知道那栋建筑物再过不久就要走进历史了。
目的地话剧社在家政大楼最深处的服装教室。
跨过禁止进入的封条,打开轧轧作响的门扉,有一微暗的建筑。
彷佛沉入水底,交织着一股尘埃和霉菌的味道。
傍晚,独自走在无人的走廊上,有种奇妙的感觉。
就像擅自蹑手蹑脚进入独居老妪的住处般,莫名地感到罪恶。
教室的门因结构不佳,打不开。
我只好踩在堆积如山的杂物上面,堂堂从破窗中进入。
教室里空无一物。
桌椅几乎被搬光了,布告栏上连一张纸也没有。
唯有作为量尺寸,身上的布已褪色的假模特儿自然地立在一旁,任凭落日西晒。
地板的磁砖东一块西一块隆起龟裂,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尘。
教室里边铺了四、五张破旧不堪的塌塌米。
那里好像是话剧社的小天地。
总觉得工程噪音和学生的喧哗声,听起来异常遥远、模糊不清。
我坐在陈旧破损的塌塌米上,久候话剧社成员的到来。
但是等了半天,连个人影也没有,我愈发怀疑我是否还在校内。
彷佛身在被村人遗忘,死气沉沉的神社中。
我兢兢业业地踏入此处,却徒劳无功。
那里恰似一座位于深山,静谧古老的圣地。
结果,那天根本没人出现。
当时只剩一位话剧社的学姐在学校,
不过,她身兼桌球社经理,那时候好像一直待在体育馆。
天黑之前,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
直到放学的钟声响起,只好打退堂鼓回家。
过了几天,我正式加入话剧社,
但入社的关键究竟为何,直到现在,我仍想不起来。
几个月后,社团教室所在的家政大楼动工拆解。
(现在应该已变成宽敞的脚踏车停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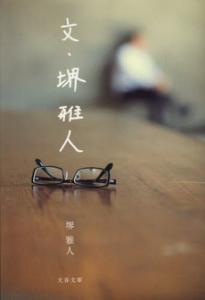
流离失所、命运多舛的话剧社再度迁徙。
这次搬到校园西边的一角,在小小的组合屋中设立社团教室。
不久,随着成员人数增加,我觉得社团活动变得有趣多了。
新校舍也大抵完工,噪音远离校园。
似乎有什么缓缓律动着。
总之,我就这样展开了演戏之路。
我不晓得这对于我目前的职业观产生怎样的影响,
但至今我时而会想起那间空旷的服装教室。
把那教室当成原点,或许很不赖。
《春》
年轻时,我认为拥有好演技是被神附身。
不完整的我带着不完整的思想
(作品的主题是什么、该如何诠释情感),随日子一天天流逝。
有一天,脑中突然灵光一闪,任凭那股冲动在身上流窜,
不知不觉化身为剧中人物。
我虽自认不是天才,但我想:「人在某种刺激下,有可能瞬间变成天才呢。」
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现年33岁的我如是想。
灵感通常来得「又快又细腻」。
好演技却不常临幸。
纵使不乏瞬间成为天才的机会,光如此,并无法应付所有场面。
就好比用绞肉做成的汉堡肉一样。
每天拿到的绞肉量都不一,
但只要在制作过程及调味方面下功夫,至少能做出象样的汉堡。
内田健次执导的电影『非命中注定之人』中,
有这么一句台词:「过了30岁,根本不会有命运般的相遇。」
消极看待认识异性的上班族对当侦探的好友谆谆告诫。
听好了,我狠话说在前头。
人过了30岁,什么命运般的邂逅、自然而然的相遇、
从友情升华为爱情……全是空话。
因为不再有换班级或文化祭了。
到某个年纪,遭遇了众所期待、让自己彻头彻尾改变的大事,
这根本是自说自话。
我震慑于山中聪先生强调此话的逼真演技。
这个论点已然在我的心中生根:「过了30岁,根本不会有命运般的相遇。」
这句格言之于恋爱,或许套在工作上也适用。
意即「过了30岁,根本不会有命中注定的作品。
扭转自己的价值观,找到有别以往、崭新的自我,绝对没有这种工作。」
有时,年轻演员的演技会深深地感动我们。
就某种意义而言,作品中的他们真的受创了,心境上有所转变。
而转变伴随着痛苦。
「命运般的相遇」硬生生夺走了曾经深信不已的事物。
以某种程度来说,形同死亡。
被导演斥责而垂头丧气的年轻演员都听过前辈的勉励:
「无论你演得多糟,也不会被杀头。」
然而,年轻演员眼中的〝死〞,却很真实。
深知「绝不会被杀头」的演员,难遭遇命运般的相遇。
这种危险的玩意儿叫思春期、青春,惟有年轻人玩得起也说不定。
不太了解自己是何许人也,认为现在的立足点不稳固,
却坚信友情、永远之类看不见的东西。
只有思春期的人才吃这一套。
话虽如此,演出新作品时,33岁如我不免这么想:
「或许这是我命中注定的作品。」
哪怕是误会一场,我也无怨尤。
目前我参与演出内田导演的新作品『AfterSchool』。
故事描述3个国中同班同学被卷入一场意外风波。
说不定这次会得到加持,演戏如有神。
若有人吐槽:「你年过30了耶。」
……想当然,我无话可说。
《食》
因为拍摄电视剧,我来到上海。三年前我也曾因工作到过中国西安。在西安最大的感触是“饭菜实在太好吃了”,说来不好意思,在上海最大的感触,也是“饭菜实在太好吃了”。我仅在上海逗留五天,体重却胖了四公斤。以下,仅是我的自我辩解。
本次导致我吃得过饱的罪魁祸首是我入住的宾馆的自助餐。即便是从早晨六点开始的“自助早餐”,种类数量已是相当惊人。
日式,西式,中式,甜点。每一种的摆放空间都无比宽敞,尤其是中餐区其丰富程度令人咂舌。单单主食就有粥、炒饭、饺子、包子、各式面类,任您挑选。面类与饺子当场现做。粥的单品种类已然令人眼花缭乱,组合起来简直近乎无限多。在我感觉来,菜品多到就像是将三、四家中华料理店鳞次栉比排在一起同时上餐一般。我再重复一遍,这是早晨六点的早餐。从十一点开始的“自助午餐”,在上述种类之上还会加上北京烤鸭、牛排等炙烤类食物。感觉又加上两三家中华料理店一起上餐,整个人从气势上已被彻底压倒。
这次拍摄过程中,我多是午后出发去片场。因此,势必是要享受“自助早餐”和“自助午餐”。夜里也是闲不住,比如经常有人带我们去吃美味的上海大闸蟹之类的。这种情况下,不胖是不可能的。
为了整个摄影组的名誉,我必须声明,在这次拍摄过程中,胖得如此明显的只有我一个人而已。但我感觉摄影组的整体食量都比在日本时要多。
上海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他在日本留学时,曾经对日本套餐的定量之少深感惊讶,“不会吧?这点儿就是一人份?”据说他春节回家时,家里人都觉得他的食量变小,很是担心。
自己的经历再加上身边工作人员的故事,让我擅自对中国抱定“能让人吃得饱饱的地方”的印象。或许,三年前在西安的记忆对我的影响也很深吧。
三年前在西安拍摄的是NHK纪录片《新丝绸之路》,内容是由我扮作一千三百年前的遣唐使,比较唐代的长安与当今的西安之异同。
纪录片的摄影组在人数上比电视剧剧组要少得多,所以每餐都是全体人员集体到某家店一起吃。令我惊讶的是,西安当地的工作人员对饮食异常执着。
早晨一碰面,马上开始讨论“中午到哪里吃”的议题。讨论通常一直持续到进入饭店之前,而吃饱之后,对话主题又变为“好吃极了”、“味道变差了啊”之类的感想。不知不觉中又到了茶点时间,在劝我们喝茶、吃点心和水果时,“晚饭吃什么”的话题又开始了。嗯,差不多每天都是如此。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