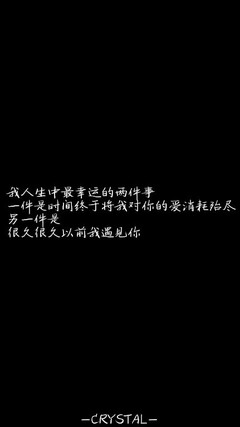爱 的 牵 挂(51) 编辑制作:林夕梦
每天收集阅读歌颂父爱母爱的文章,一遍又一遍地读,读着读着,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把这些佳作推荐给大家。请认真地读一读,好好地品一品吧——
父亲的胸怀 作者:范文静 亲爱的爸爸:
您还好吗?女儿时刻都惦念着您。
爸爸,从寄来的照片看,您比去年更老了,我知道您的老是缘于繁重的农活儿,更缘于与您相濡以沫28年的母亲的逝去。就在去年的初冬,母亲刚刚50岁的生命被可恶的疾病夺走了。母亲的病来得那么突然,她的生命消失得那么迅速,甚至来不及留下只言片语。母亲的逝去,对我和弟弟来说是失去了生养我们的慈母,我们的伤痛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对您来说,不仅是失去了一位亲人,更是失去了相互搀扶的伴侣,您的痛苦是旁人无法体会的。母亲刚刚过世的那些天里,原本沉默的您更加无言,其实我多想让您随我一起赴新疆,让我照顾您,可是面对刚刚生了孩子的弟媳和还有一脸稚嫩的弟弟,我实在无法开口。
其实,我并不是您的骨肉,可是您却给了我一个父亲最深的爱。28年前,当我的生命还是个胚胎的时候,母亲便因受不了封建家庭的奴役与挑剔,挣脱苦海逃回了娘家。受了封建思想熏陶的外公,怎么也不愿让身怀有孕、肚皮一天比一天大的女儿住在娘家,便四处托人为母亲说亲。于是您——因女方嫌弃木讷而离异的人与母亲走到了一起。不久,母亲便生下了我,奶奶因我是女孩儿,又不是您的骨肉,想送人,可您笨拙地抱着我,说:“谁说她不是我的孩子!只要她生在我屋里,吃了我的饭,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我就这样留下来。
在我3岁的时候,妈妈生了弟弟,村子里的人都说您好福气,您笑笑,骑在您脖子上的依然是我。记得您在生产队喂牲畜的时候,一个冬天的晚上,我闹着要跟您到饲养室去睡,妈妈怕我闹,不让去,可您不愿意看见我哭,我就骑着“大马”到饲养室去睡。半夜我醒来发现没有妈妈,又哭着要回家找妈妈。您从热乎乎的被窝里钻出来,又把我扛回了家。在我长大后的今天,村里仍然有长辈说我是在您肩膀上长大的。
上学后我每年都会有漂亮的新衣服,那时候我从来都不去思考这些衣物给你们带来的经济负担。上初中后,因为住校要带一周的干粮,于是,您和母亲总是轮换着骑自行车在40里的土路上颠簸,我因此成为住校期间父母探望次数最多的学生。
一个夏天,我们正在上课,我突然看到了母亲。我走出教室,母亲拉住我的手对我说:“他要来看你,是你的生父……”顺着母亲的目光,我看见不远处站着一位与您年纪相当的陌生男子,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我朝后退了几步,说:“不,我不认识他。”返身跑进了教室。我的心乱极了,也恨极了那个人,甚至有些恨母亲,是他们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13岁的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身世。当暑假来临的时候,您像往常一样来接我,并且在集市上为我买了套衣服。我在心中悄悄地比较着此前的您和现在的您,但是您一如既往。就在我几乎忘了这件事的时候,有一天妈妈不在,您悄悄对我说:“那个人要认你要领你,别跟他去好吗?”我没有作声,因为年幼的我,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件事,好在以后他再也没找过我,否则,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因血缘而冷落了亲情,辜负了您对我的爱。
初中毕业时,我报考了学费较低的职业高中中西医班。开学时,您亲自背着行李,把我送到学校,报完名后您便急着回家。望着您渐远的背影,我差点儿掉下眼泪。我的学费是您东拼西凑借的,往后的六个学期里,您还要担负一个职高生的花销。您其实可以不用这样操心的,几年前您有机会卸掉这个负担,可是您没有。学校的饭票是用钱买或者用粮食换,我们只能选择后者。家和学校中间要倒一次车,但您不辞辛劳,每学期都跑几趟,总是来去匆匆,毫无怨言。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您的一次露宿。那次给我送粮食时,您把身上的钱全掏给了我。上车时我突然想起您没有吃饭,便给您买了一个肉夹馍。问您有没有钱,您说有,但到了西峰,您因无钱买票被售票员推下了车。异地他乡,举目无亲,您在初冬的冷风中在街上转到深夜,最后在一个橱窗下面蹲到天亮。清晨,您饿着肚子磨破嘴皮子,才有一位好心的司机将您拉到家。后来,我从母亲口里知道这件事,泪水夺眶而出,我的心在疼痛……
毕业后,我千里迢迢来到这座城市,虽然路途遥远,但是从别人代写的信里,我看到了您与母亲对我的牵挂。1999年底,我携新婚的丈夫回到家中,不善言辞的您在饭桌上不断地往我们碗中夹菜,脸上露着由衷的笑容,我知道您对女儿的婚姻十分满意。我以为等到条件成熟就可以把你们接来颐养天年了,可是噩耗传来,母亲患上了急性白血病。当我日夜兼程赶回家中时,看到了我时刻担心的母亲和消瘦的您。4个小时后,母亲停止了呼吸。那一刻,我的心被伤痛击得粉碎,我扑在您怀里,放声大哭。您搂着我喃喃地说:“孩子,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我抬起头,看见您脸上纵横的泪水,于是我止住了悲声,我不能让自己的哭泣加重您的痛苦。28年的相濡以沫、形影相伴突然缺失了,真正需要安慰的人是您而不是我。我很后悔在母亲的葬礼后因逃避没了妈妈的家而整日在亲戚家奔走,我知道您很孤单,需要陪伴。在三姑家的一天下午,下着雪,我突然很想妈妈,很想您。当我不顾三姑阻拦带着一身雪花站在您面前时,我看到了形影相吊的您正从花生壳里一粒粒取出花生米,烧得通红的铁炉旁边只有您一个人,原本该有纳着鞋垫儿的母亲在炕上陪您说话。站在您面前,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吓得您满手灰尘地站起来:“我娃不哭,我娃不哭,爸好着哩……”临走时,我拿着行李和您并肩走着,我不敢看您的脸和眼,那张脸全是皱纹,那双眼满是牵挂和不舍。上了车我回过头,汽车已远远撇下您,您那么孤独,那么苍老!转过脸,我的抽噎充满了车厢,引得四邻侧目,而我却泪雨滂沱。
现在,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不知道您可否习惯了没有母亲照料的日子?曾经当面对我许诺会来照顾您帮您缝补浆洗的小姑可曾食言?这一切,本来是做女儿的本分,可是,异乡与家乡山高水远,任我的针线纫得再长也无法缝制您那往年由母亲料理的衣裳。爸爸,您可因此而责怪过您的女儿?可曾后悔当初让女儿展翅远飞?爸爸,母亲的一生都是在黄土高原那块贫瘠的土地上度过的,她没能看看外面的土地,也没能站在摩天大楼顶端鸟瞰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城市,这成为我心中一块不能触及的伤疤。所以爸爸,我希望您走出来,替妈妈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为妈妈过一过那没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让我负疚的心也得到一丝宽慰。
亲爱的爸爸,照顾好自己,让女儿有个完成心愿的机会,好吗?
祝您安康!
不孝女叩上
2002年12月26日
(选自《当代青年》2003年第6期)
父爱如禅 作者:倪新宁
我感到一只手轻轻地却又深深地一下一下地推着我。睁开眼,朦朦胧胧中,父亲如冬晨河岸的枯树桩般正站在我的床边。我懵懂着爬起来,周围的鼾声起伏如小河的波浪,别的新生还在甜美地睡着,远大而美好的前程为他们的梦乡舒展开怎样一幅幅海阔天空的画卷哪!本来我也同他们一样,不,我以比他们更优异的成绩考入这所名牌大学,比他们更有权利梦想美丽的将来,但我却由于先天性心脏病而不得不等待严酷的“判决”——鉴于我的病情,校方坚持必须经过医院专家组再次严格体检认可后方能正式接收。前途未卜,世路茫茫,一种世界末日之感包围着我,心中自是一片荒凉与凄苦。
呆了许久,我颤抖着对父亲说,你不能等我体检后再回去吗?话音里分明已带着哭腔。父亲掏出一支烟,却怎么也点不着。我说:“你拿倒了。”父亲苦笑,点着烟深深地吸了两口。我突然发现地上一堆烟头,哦,半夜似醒非醒时闪现的那明明暗暗的星火不是梦境,父亲定是——夜没合眼吧。
父子相对无语。
“我有事的,真的有事。”父亲局促地说,拿烟的手抖动着,一脸的愧疚。“我,真的必须赶快回去,不能在这儿呆三天等体检结果的。4点子,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烟烧到了尽头,父亲的手烫得哆嗦了一下。“你走吧!”我突然恶声恶气地说,“不就是个大学吗?上不上的无所谓。”父亲的头缓缓抬起,凝视着我,有什么东西在父子之间无声地流淌着。似乎过去了一个世纪,父亲才低声说:“不敢再耽搁了,我走了。你快睡下吧。”
父亲仓皇地逃离了。我还是禁不住追送父亲。下楼梯时,明亮的灯光下父亲如蒲公英般的白发赫然刺痛了我的双眼。一夜之间,父亲苍老了许多。
父亲回头发现了我,低声却严厉地说了一句:“回去!没事的,我没事,你也会没事!”然后扭过头疾步而去。我的头脑中一片茫然,还是身不由己地追赶父亲。偌大的校园一片阒寂,只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虫在角落里哀怨着不尽的凄凉。我努力地捕捉着昏黄路灯下父亲的背影,多么希望父亲再回一下头,更希望他改变主意留下来——父亲再没回头,尽管他的脚步有些踉跄,尽管有一刹那甚至要停下来,然而父亲还是一阵风样消失了……
转身回返的瞬间,我委屈、怨怼的泪水夺眶而出——父亲,孩儿多么希望你能陪着度过这漫长难挨的三天哪!在决定儿子命运的关键时刻,你却惶惶地逃避了。什么大不了的事要你一个普通工人急赶着回去处理,而把你的爱子独自抛弃在这非常时刻呀?
苍天有眼,我总算勉强通过了体检这一关,连夜把电话打回家,母亲高兴得语无伦次。我让妈把电话给父亲,母亲说:“你爸听到了,他欢喜得流了泪呢!”我坚持让父亲接电话,我要让父亲亲:耳听到独自闯过了体检关已成为名牌大学学生的儿子的声音。我不仅要让父亲高兴,还要让他为他的逃避而愧疚。
母亲的声音有些呜咽了:“你爸他,他不能接电话,他,他……”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我爸怎么啦广电话中传来父亲倔强的声音:“别瞎唠叨,我没事,没事……”接着是一阵呼啦啦的响动,父亲终于气喘吁吁地接了电话。我急切地问道:“爸,你,你怎么啦?”“你放心,我没事,真的没事,你只管安心读你的书。我说了,你会没事的,往后也会没事的……”
我还是知道了,父亲不但扭伤了腰,而且为了我他险些把老命都搭上了。我们市发电厂高达一百多米的大烟囱需要人从上面爬进去清理,尽管标出3000元的高价,还是没人愿冒生命危险去揽这差事。就在送我到学校的前两天,父亲得知了这消息,便背着家人去揽下了这赌命的差事,毫不犹豫地与电厂签下了死伤与厂方无关的“生死文书”。
父亲,儿子明白了,你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赶回去了。那时离你为儿去电厂卖命只有25个小时了(电厂在25小时后停机13小时,父亲必须在这13小时内清理好烟囱),而火车运行就需23小时20分钟。赶到火车站和下了火车再赶到电厂只有1小时40分的时间。你在儿子床边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几乎是忍着生离死别之情离开了我。而你是舍不得搭出租车的,你的两条腿必须如钟表的指针精确地度量时间。
原来父亲早已打听好了,即使我现在能坚持大学学习,一年后也必须进行心脏手术,手术的费用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父亲是在用自己的命换儿子的命啊!
我的心被父亲的心撞得发烫、发痛,热泪奔涌如波决堤。木讷的父亲不会对我讲这些的,我亦无言以对。人世间越是深越是厚的情感,往往越是难以言说的——父爱如禅,只能悟。
(选自《人间方圆》2003年第3期)

阳光下的守望 顾振威
我见过一个母亲,一个阳光下守望的母亲。母亲就站在七月炙热的阳光下,翘首望着百米外的考场,神色凝重。母亲脸上早已狼藉着豆大的汗珠,汗水早将她的衣衫浸染得水洗一样,她的花白的头发凌乱地贴在前额上。母亲就这样半张着嘴,一动不动地盯着考场,站成一尊雕像。
树阴下说笑的家长停止了说笑,他们惊讶地望着阳光下的母亲。有人劝母亲挪到树阴下,母亲神情肃然的脸上挤出个比仲春的冰还薄的笑,小声嗫嚅道:“站在这里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考场,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孩子。”
没人笑她痴,没人笑她傻,也没人再劝她。
烈日下守望的母亲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目光扫了扫不远处的茶摊,就又目不转睛地盯着考场了。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半个小时,也许一个小时,母亲像摊软泥一样瘫在了地上。众人一声惊呼后都围了上去,看千呼万唤后仍是昏迷不醒,便将她抬到学校大门口的医务室里。听了心跳,量了血压,挂了吊针,母亲仍然紧闭着双眼。经验丰富的医生微笑着告诉众人:“看我怎样弄醒她。”
医生附在母亲耳边,轻轻地说了句:“学生下考场了。”
母亲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拔掉针头,下了病床:“我得赶快问问儿子考得怎么样。”
常常将这个真实的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学生说,这故事抵得上一千句枯燥无味的说教。
(选自《周口日报》)
一天,收拾屋子,找出两本布满尘土的小学课本。女友说还扔不扔了?我抚摩着书半晌没说话。
书是我上高中时妈妈为我买的。妈妈是一字不识的苗家妇女。家乡有种风俗,一个女人在去世时,口里必须含银(或金)才能入土为安。所以在贫困人家,攒钱置办一件小小银饰便成了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那一年,妈妈起早摸黑喂了两只猪,终于置了一对银手镯。
在临近高考的那段日子,妈妈时常进城给我送些吃的。她知道我复习忙,每次都是匆匆来匆匆去。有一天,妈妈去了不久却又回来,拉我到僻静处:“孩子,我替你买了两本考大学的书。”
“什么?”我心里咯噔一下。常听人说学校外面有人用假书、假资料来骗那些来自山区一字不识的家长。
“人家说,只要用这书,考大学包中。”
“哪来的钱?”
“镯子换的。”
我抢过书,撕去包装,一阵巨大的绝望顿时袭上心头:两本小学课本竟然就骗走了妈妈的镯子!
“孩子,行吧?”
望着满怀期望的母亲,我强压下泪水和屈辱:“行,妈,行的!”
后来我考上大学,妈妈高兴极了,说是两只镯子花得值。她甚至想找卖给她书的人道谢!
“你妈后来知道真相了吗?”女友问。
“没有。我永远都不会让她知道。”
(选自《精短小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