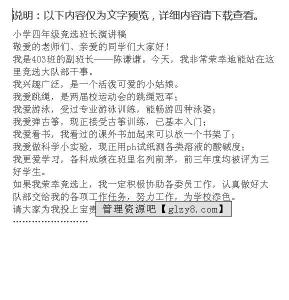文学是两难的,也是超越俗常的善恶是非的
已经有了结论的地方,是不需要作家的;那些没有结论、具有无穷可能的精神领域,才需要作家去探求。中国由于是儒家思想一度做主导的国度,现世层面的关怀,一直是文学的主流,尤其小说,是很少对一些深远的问题作出思索的。包括鲁迅的作品,很多也是面对现世问题发言的。这种关怀现实的传统,使得中国作家身上有着很深的责任感,这是好事,同时,你又不得不承认,过度受制于实感层面的现实,经常会阻碍作家往灵魂的深处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看重鲁迅的小说《祝福》。这篇小说,直接写到一个被生活舔干了生气的人,却追问起灵魂的有无来,这是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小说里写到,“我”回到鲁镇见到祥林嫂,她问了“我”一个问题: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这个问题令我悚然。鲁迅是这样写的: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一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虹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者,“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勿勿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
祥林嫂问的问题,是说不清的,也是“我”所不知道的,但只要是人,就会思考这个问题。这样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由祥林嫂问出来,她的精神空间一下就变得开阔了,她就不仅是一个平面的被压迫、被损害者了。她问了,但“我”回答不了。如果“我”说,这个世界没有灵魂,大家都吃吃喝喝吧,死了就灰飞烟灭了,这样回答,人的精神探索就停止了。文学要追问的是:人的灵魂是否存在?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人的灵魂永恒吗?其实祥林嫂会有这么一问,根源在柳妈那里:
“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诡秘的说。“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我想,这真是……”
她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这是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她被柳妈吓怀了,她才会来问“我”。她的问题,丰富了她灵魂里那复杂的侧面。鲁迅在这部小说中,对祥林嫂的命运,以及究竟有没有灵魂问题,也是存着复杂的感受的。他不简单地作出抉择。因此,鲁迅的小说,有着丰富的阐释空间。从这个问题再往下走一步,就是自我审视了。自我审视的时候,两难的、超越善恶的事物,就会更加迫切地来拷问一个人的内心。鲁迅的《野草》,就写到了这些更深的疑问。
文学就是处理这种两难的、无法抉择的精神经验的,同时也是超越俗常的善恶是非的。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面临许多抉择,有时却又难以抉择,这是人生的实质。而更多的时候,甚至连善恶都很难简单地区分。一个人杀了人,这应该是一个恶人了吧,可是他在法庭上说出的理由,实在又值得同情;一个人为了孩子读好书,天天严格教育他,这是善良的愿望吧?可他过于严格,孩子受不了,自杀了,这又成了恶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复杂。但是,再难区分的善和恶,背后还是有是非标准的,假如都是善的,都是好人,可是造成了悲剧,你怎么看待这个悲剧?没有坏人,没有恶势力,可是悲剧还是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就是文学的悲剧,也是深刻的悲剧。
《红楼梦》就是这样的悲剧。造成这个伟大悲剧的原因是什么?是封建礼教吗?太简单了;造成林黛玉伤心至死的凶手是谁?没有凶手。所有的人都是好人,都爱林黛玉。《红楼梦》里没有极恶之人,没有蛇蝎之人,谁都不想林黛玉死,他们都希望她幸福,宝玉这样希望,贾母更是这样希望。一旦这个悲剧演成,才发现这是一个没有凶手、但每个人都有责任的悲剧。这个悲剧的内涵,比过往的中国小说、中国戏剧都要来得深邃,原因就在于曹雪芹看到了一种时代性的错误,是人力无法解决的错误——在这个错误的时代里,哪怕是最平常的人情、最平常的道德,都会造成一个情感悲剧的演成。王国维看到了这一点,为此写了一篇很有名的《红楼梦》评论,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研究《红楼梦》精神空间的发端之作。曹雪芹的伟大,不单在于他看到一种无错之错,还在于他没有把自己置身事外,他认为自己也是有罪的,他也是有责任的。贾宝玉算是作者的投射,在宝玉身上,这种自我悔悟的精神非常明显,最后,他甚至要离开家,离开那个伤心地。他这样想,表明他没有推卸自己的罪责,这也是曹雪芹在小说一开头就点名出来的,他说“我之罪固不免”,他的写作是在赎罪,是在还情感和精神的债。
说到还债,巴金的《随想录》也是还债,他对“文革”有反思,觉得自己欠了历史的,欠了别人的,也欠了自己的。这种自我反省,无论他的反省得是否够深,但很宝贵。那个荒唐岁月,有那么多人都经历过了,可真正站出来反思的人,有几个呢?中国作家在写人类的恶和绝望的时候,往往是把自己摘除出来的,好像这个恶和绝望,和自己没有关系。巴金的意义在于,他承认自己也在恶和黑暗里有份,承认自己也曾经是蒙昧的、甚至作恶的势力中的一员。这令人想起鲁迅。鲁迅的深刻在于,他不仅写黑暗,写绝望,他还带着这种黑暗和绝望生活,因为在他看来,他身上也有黑暗,也有精神的阴影。鲁迅对世界存着大悲悯,他虽以冷眼看世界,却从来不是一个旁观者。当他说“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时,不忘强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也就是说,鲁迅的思想并没有停留于对“吃人”文化的批判上,他承认自己也是这“吃人”文化的“帮手”,是共谋。他的文化批判,没有把自己摘除出去,相反,他看到自己也是这“吃人”传统中的一部分,认定自己对一切“吃人”悲剧的发生也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充当的不仅是灵魂的审判官,他更是将自己也当作了被审判的犯人——他的双重身份,使他的批判更具力度,在他身上,自审往往和审判同时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具有这种自审意识的人极为稀少,鲁迅是其中最为坚决的一个。如他自己所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写在〈坟〉后面》)这样的自我解剖,迫使鲁迅不再从世俗的善恶、是非之中寻求人性的答案,而是转向内心,挖掘灵魂的黑暗和光亮。没有这一点,鲁迅也不可能这么深刻地理解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说: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鲁迅也是能写出“灵魂的深“的作家。他同样兼具“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这双重身份,不仅超越了善恶,而且因为深入到了“甚深的灵魂中”,达到“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的境界——这远比一般的社会批判要广阔、深邃得多。然而,在如今的鲁迅研究中,总是过分强调他作为社会批判家的身份,恰恰遗忘了鲁迅身上那自审、悔悟、超越善恶的更深一层的灵魂景象。这或许正是鲁迅精神失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未完待续)
注:二○○五年五月在广东省作家协会“小说讲习班”上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而成,并经作者审订。

(选自《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人文讲演录)一书,该书由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