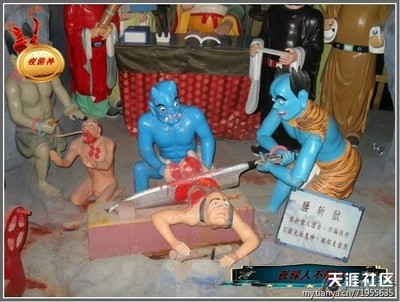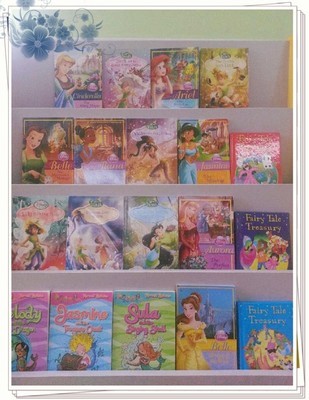“只有疯子才会试图去描绘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高迪
孤僻沉默、衣衫褴褛、成天工作、无浪漫史 ——这就是西班牙19世纪最著名的建筑师,整个巴塞罗那建筑艺术的缔造者:安东尼·高迪·克尔内特。今天,让我们跟随蚂蜂窝旅行家肉松夫妇一起来到西班牙,走入高迪之城,看看那些出自高迪之手的艺术建筑。
-
安东尼·高迪·克尔内特(Antonio Gaudi Cornet,1852-1926),西班牙建筑师,塑性建筑流派的代表人物,属于新艺术建筑风格。高迪曾就学于巴塞罗那省立建筑学校,毕业后初期作品近似华丽的维多利亚式,后采用历史风格,属哥特复兴的主流。高迪最早接受的主要委托项目是完成巴塞罗那的神圣家族教堂(也称圣家族教堂,1883—目前仍在建设中),这是一座极有个性和感染力的建筑物(高迪去世时仅完成一个耳堂和四个塔楼之一),米拉公寓,巴特罗公寓(又称巴特罗之家),吉埃尔礼拜堂和古埃尔公园。
文图/肉松
设计/骨干
在巴塞罗那的每一天,我们都会从城内不同的角度看到圣家族大教堂那直冲天际的尖顶,今天才终于来到它的面前。这座教堂的外观总体上还是哥特式的,也许是因为尖塔上那些凹凸不平的孔洞,从远处看起来,教堂就像是用松软的红土给捏成的,走近了,才看到是天然的红色石头砌成的。
圣家族大教堂从1882年开始修建,高迪从1883年开始主持该工程,直到现在还未完工,已经修建了整整132年,可想而知这一工程还将继续几十年,也许上百年。好处是,如果你每隔几年去一次巴塞罗那的话,你看到的圣家族大教堂都会有细微的变化,绝不会重复。
▲圣家族大教堂远看像是用松软的红土给捏成的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一个愚人节笑话,说一支来自中国的建筑队将在几年内让圣家族大教堂彻底竣工,的确也有不少游客难以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一方面,这个教堂设计非常复杂,施工难度确实很高,另一方面,这个教堂的全部建设资金都来源于私人捐赠,漫长的筹资也拖慢了工程的进展。
其实换个角度看,历史上很多著名的大教堂修建时间都跨越了几个世纪,米兰大教堂前后建了一百年,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教堂花了两百多年,科隆大教堂的建造时间更是超过了六百年,跟它们比起来,圣家族教堂的修建时间并不出奇,只是它开始建造的时间晚一点。从三十一岁盛年到七十四岁高龄,高迪主持修建这座教堂四十三年之久,在生前的最后十二年,他谢绝了其他所有工作,专心致志于这一教堂。可惜在高迪死后,保存着高迪设计图纸的工作室毁于战火,工程在1936年停了下来,由于高迪的学生和追随者的努力,借助于从大火中抢救出来的图纸,1952年重新开工。
▲圣家族大教堂模型
高迪最初的设想是严格按照宗教思想教义,建造一个象征着基督教的世界。为此,教堂地面采用古罗马教堂巴西利卡式的十字形格局,五个正厅有交叉甬道连接,象征天与地、人与神之间的交汇,教堂的三个立面将分别表现基督的诞生、受难和复活,每一面上都有四座高塔,一共十二座分别献给十二位圣徒,四座钟楼则献给四位《福音书》作者,最高的那两座圆形尖塔,献给基督和圣母。
我们首先来到基督诞生的那一立面,头顶上悬着的密密麻麻的雕塑几乎要把我们压垮。在大门口正中间树立着的是耶稣家谱柱,圣母小心翼翼地抱着刚刚出生的婴儿耶稣,圣父何塞则在身后呵护着圣母和耶稣,两旁围绕着牛和骡子等各种牲畜。虽然极尽精美,但在看过了那么多高迪的作品之后,总觉得如此写实的雕塑风格显得不那么“高迪”,据说高迪为了追求雕塑的真实效果,在表现犹太国王希律下令屠杀婴儿的那个故事时,他还特地去找了不少死婴,制成石膏模型悬挂在工作间里,连工人见到都觉得毛骨悚然。
▲圣家族教堂基督诞生的那一立面,雕塑密密麻麻
等走进大教堂,来到正厅,我们才感觉到,这座教堂的内部实在是高迪,太高迪了。教堂的内部空间极其高阔,阳光透过天顶的天窗洒在地板上形成光斑,侧面的彩色玻璃则让室内充溢着五彩的光线,几十根粗大的柱子就像热带丛林里的参天大树一样生出分叉,共同支撑着巨大的拱顶,在柱子的分叉节点,生长着一种像苍蝇复眼的圆形凸起,部分已经被装饰上了充满童心的五彩图案,就像一颗晶莹的纽扣一样装点在柱子上。一切都显得辉煌,灿烂,毫无心机,正大光明。
▲圣家族教堂拱顶
我们在欧洲走过了那么多宏伟壮观的教堂,它们大都令人震慑,油然对上帝生出敬畏之心,但是只有来到圣家族大教堂里,我们才第一次觉得满心欢喜,觉得上帝可以可亲可近,就连被悬挂在空中的耶稣受难像,也因为天顶正上方洒下的阳光,和那个看起来像是旋转木马的黄金罗盘伞盖,让人更多感觉耶稣之死是一种解脱,是充满希望的涅槃重生。

▲被悬挂在空中的耶稣受难像
从另一个立面的大门走出来,复活立面的雕塑已经充满了现代特征,它们来自雕塑家苏比拉克,线条有棱有角,简洁写意,为了表达对高迪的敬意,他还把米拉之家上那些烟囱士兵也搬了过来。还有日本雕塑家外尾悦郎设计的塔尖,就像盛满了五颜六色的冰淇淋球,它看起来来自于古埃尔公园的马赛克拼贴。
对于这种做法是否符合高迪的原意,喜爱高迪的人们也在争辩不休,毕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座圣家族大教堂,虽然尽量遵循高迪的原始设计理念,也不得不融合了不少后来艺术家自己的理解和创意,所以它不会像高迪一人设计的巴特罗之家和米拉之家那么纯粹,但是无论如何,这仍然是一座令人无法忘怀的建筑。可惜高迪不能亲自完成这座建筑,否则我们将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高迪。
▲圣家族教堂西侧的“受难立面”
吃完饭,我们乘公车来到了古埃尔公园(Park Guell)附近。古埃尔公园位于巴塞罗那北部的坡地地区,沿着那些陡峭的街道向高处一路走过去,蔚蓝的大海在身后若隐若现。
古埃尔公园肯定是高迪设计过的最大的地方了,它占地20公顷,原本是高迪最重要的赞助者,富商古埃尔计划建造的一片高端商业住宅区,后来销售不成功,项目最终只完成了门房、中央公园、高架走廊等几个公共设施部分,被市政府收购后开辟为社区公园。值得一提的是,高迪故居也坐落在古埃尔公园里面,高迪在这里住了二十年。
看起来,古埃尔公园是高迪童心大发的产物。公园入口处那两座包裹着靓丽釉彩的彩色屋子,看起来就像是童话里的糖果屋,这里现在被当成了小卖部,游客纷纷跑到二楼的窗户留影,我们也不能免俗,在一间糖果屋拍下了一张比迪斯尼乐园更有童话感的照片,说实话,高迪编织起童话世界来,质感比迪斯尼乐园可要强多了。
▲古埃尔公园
古埃尔公园最著名的标志性景观,当属那只由彩色马赛克拼成的巨型蜥蜴立体喷泉,这只蜥蜴源自加泰罗尼亚徽章,无数游客在这里争相与它合影,拥抱、亲吻和调戏那只可怜的蜥蜴,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拍照时比出剪刀手是一种跨越国界和种族的普世行为。
正在发愣时,一位漂亮的俄罗斯女孩把她的相机交给我,用灵巧的手势和生硬的英语示意我帮忙,一起完成一张她用舌尖舔蜥蜴的照片,当然不是真的舔上去,但看起来就要像是跟蜥蜴的舌头接触在一起,我辗转腾挪找了将近一分钟角度后,终于获得了成功,俄罗斯女孩开心地问我要不要也来这么一张,我犹豫了一下,充满东方气韵地表示了谢绝。
▲古埃尔公园的建筑
古埃尔公园并不算是我们最喜爱的高迪作品,但来到这里的人们显然最快乐,一方面,我想这跟它是唯一免费的高迪作品有关,另一方面,这里的确也有种其他高迪建筑所缺乏的没心没肺的欢乐感,高迪用一堆瓷砖碎片、玻璃碎渣和粗糙的石块,拼贴出了华丽而又稚趣的图案,不事经营,却照样气象万千。
傍晚时分,我们终于坐在了山坡顶上那只号称“全世界最长椅子”的蜿蜒曲折的陶瓷长椅上,远远眺望夕阳下的巴塞罗那城。虽然巴塞罗那是个极其美妙的城市,但如果没有高迪的建筑,它也只是一座普通的城市,但因为有了高迪,巴塞罗那就成为了一座特别的城市。虽然这座城市还有米罗,毕加索,达利……放在其他任何城市,我们恐怕都不错过这几位艺术家的博物馆,但是为了高迪,我们将在巴塞罗那的参观时间几乎全部都给了他的建筑,对于我们来说,巴塞罗那就是一座属于高迪的城市。
▲沉浸在夜幕下的古埃尔公园
之前提到过,高迪故居也在古埃尔公园里。跟这座创意十足的公园相反,高迪的家中陈设十分简单,甚至可以说简陋,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个设计师的家,据说这所房子也不是高迪自己设计的,所以光这座房子本身并没有太多可看的价值,好在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不少高迪生平的资料。
由于高迪十分厌恶拍照,留下的照片不多。年轻时的高迪十分俊朗,满脸的大胡子也遮不住眸子英气十足,看起来很像巴塞罗那队的后卫球员皮克,那时候的他穿着也十分讲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眼神越来越内敛,衣着也越来越随意,中年时还剃了个光头。在他全身心投入圣家族大教堂建造的最后十二年,他的外表已经跟一个穷困的西班牙小老头没什么区别,以至于当1926年高迪被一辆电车偶然撞死时,除了一个老太太,已经没有人认得出这具衣衫褴褛的尸体竟然就是巴塞罗那这座城市的骄傲。
▲圣家族教堂完工后3D模型
据说,在加泰罗尼亚语中,高迪的意思是“享受快乐”,他这一生听起来真不像是一个享受快乐的人的生活。不过,也许这就是他享受快乐的方式,高迪留下了十八座惊世骇俗的建筑作品,他本人被安葬在他最后作品圣家族大教堂的地下,这座教堂仍然在不断修建之中,直至实现他当年设计蓝图上的样子,这是那些生前安享尊荣的人也未必能得到的成就。
——摘自《拉丁欧洲,走过没有围墙的艺术馆》(蚂蜂窝旅行家系列丛书)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