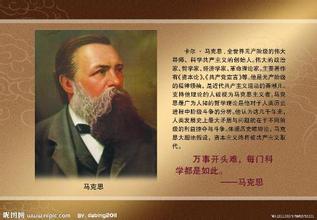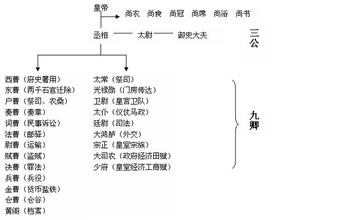一、白话诗主潮: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
在中国新诗历史上,白话诗几乎已经成为“五·四”时期新诗的独有称谓,无论其科学性与否,作为一段历史,已保存在诗歌的记忆里;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改变其历史原状,在此,我仍然继续加以沿用。白话诗主潮的当代性是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而在争取人的权利的过程中,白话诗作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急先锋、新文化运动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兴起则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它直接卷入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乃至于卷入社会革命,具有强烈的社会变革的政治诉求。此举是否合乎艺术规律抑或反艺术规律,在此,我们姑且不论。但由于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中国在此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历史阶段,一直讳言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似乎把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当成了西方资产阶级独有的专利,而很少谈及,甚至是不敢提及,给白话诗研究设置了一道严重的思想障碍。其实,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简单地否定个性自由与解放,而是在批判资本主义个性自由与解放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把个性自由与解放看成是未来人类社会所追求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明确地阐释了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的关系,也即人的自由发展,就是个性解放,就是人的解放,以为,人类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的不断解放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争取自由的历史。
白话诗主潮的个性自由与解放,早期突出表现在突破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晚清“诗界革命”的局限性基础上的诗的形式解放上,也即“诗体的大解放”(胡适语),并以“诗体的大解放”来张扬其个性自由与解放。其主要原因,“五·四”运动主将陈独秀在他的那篇著名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得明明白白,他说:“……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因此,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胡适,为践行“反对旧艺术”思想主张,在他的白话诗纲领性诗论《谈新诗》中指出:“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于是,他便及时而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并开始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打破诗的格律,换以“自然的音节”。这样,“诗的音节全靠两个重要分子: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至于句末的韵脚,句中的平仄,都是不重要的事。语气自然,用字和谐,就是句末无韵也不要紧。”一切“顺着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胡适《谈新诗》语)。二是以白话写诗。不仅是语言文字上的,而且也是语法结构上的,“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胡适《谈新诗》语)这样,在“诗体的大解放”的旗帜下,当时诗界掀起了白话诗热潮,并涌现出当年被传诵一时的周作人的白话诗《小河》:“一条小河,缓缓的向前流动。/经过的地方,两面全是乌黑的土;生满了红的花,碧绿的叶,黄的果实。?一个农夫背了锄来,在小河中间筑起一道堰。?下流干了,上流的水被堰拦着,下来不得,不得前进,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乱转。?水要保持他的生命,总须流动,便只在堰前乱转。?堰下的土,逐渐淘去,成了深潭。?水也不怨这堰,——便只是想流动。?想同从前一般,稳稳的向前流动……”虽然这首诗现在看来,诗体、诗意都还十分稚嫩,但这首诗在当时几乎被大家异口同声地称赞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总体而言,初期白话诗几乎都一致地遵守着诗体解放的原则,做到了“作诗如作文”要求,进而涌现出第一批白话诗人,诸如:胡适、刘半农、刘大白、沈尹默、俞平白、康白情等。
然而,随着第一批白话诗的“尝试”成功,白话诗人们已经不能仅仅满足于“诗体的大解放”和“作诗如作文”的要求了。于是,他们开始了白话诗史上新的长征:向着由形式到内容上的个性自由与解放的目标进发。不过,早期的白话诗在思想内容上虽然也抒发了追求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的精神,或表现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的同情,如:胡适的《人力车夫》、刘半农的《学徒苦》等;或表现出对人性的揭示,如:刘大白的《邮吻》等;或表现出对新世界的憧憬,如:《红色的新年》、《劳动节歌》等,但都十分粗浅。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后,经过民主与科学精神洗礼的郭沫若、汪静之、徐志摩、戴望舒等诗人的隆重登场,白话诗主潮的这种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的当代性思潮才显得更加突出。但此时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已非是单一性思想主题所能概括得了的了,而是呈现出或二元化并进或分化的态势,即:一是个体的独立自主,这就是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二是民族群体的独立自主,这就是民族的自由与解放。
“五·四”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着双重的历史任务,一是反帝,二是反封建。因此,这个时期有识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包括诗人一般都具有双重精神动力,一是“救亡图存”这个自近代以来的强大主题,换而言之,就是民族主义。二是思想解放,人格独立,换而言之,就是自由主义。尤其是自由主义,它站在民主与科学的背后,是民族主义通往民主主义之间的一大精神媒介。关于民族主义,陈独秀在其《新青年》创刊号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明确指出:“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固有人之伦、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于消灭也。……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于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亮出了“五·四”精神的主基调:“科学与人权并重”,并逐步演化成后来的“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关于自由主义,陈独秀在其《新青年》创刊号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引用了德国大哲学家尼采关于道德的两种分类法,即:“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目的在于说明:“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语)视个性自由与解放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根本所在。
因此,受此两种精神的激励和鼓舞,“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诗人郭沫若以彻底反抗、破坏、创造精神,“怀着改造社会的朦胧的思想和振兴民族的极大热情”,(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一方面把“五·四”白话诗运动的“诗体的大解放”精神推向极致;另一方面使诗的思想内容、艺术表现得以充分的解放与自由。这些都可以从他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写下的他一生中最光辉的诗篇《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天狗》、《匪徒颂》(1921年集结《女神》出版)等中可以看出,充满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以及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语),诗中所抒发的自我,有民族、国家之“大我”,如《凤凰涅槃》中的凤凰,就象征着民族的新生;也有诗人个人之“小我”,如《晨安》中的“我”,就是诗人自我“在‘千载一时的晨光’里,向着‘壮丽的山河,向着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的呼唤,等等,竭尽郭沫若张扬个性自由与解放的极端个性。同样,白话诗主潮的这种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理想的追求,在闻一多那里,则表现为由一开始《红烛》中郭沫若似的热情奔放式的满腔对祖国的热切之情和祝愿:“烧吧!烧吧!?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也救出他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到《死水》中对现实极度绝望和黑暗的控诉与诅咒:“这是一沟绝望如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在徐志摩那里,则表现为由对“新的政治、新的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的失望,转向对现实黑暗的揭露,最后走向情感王国,寄情于《再别康桥》似的山光水色的大自然中“做一条水草”,然后作“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般似的空灵。在戴望舒那里,则表现为《雨巷》中悠长而寂寥的愁怨:“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冷漠,凄清,又惆怅。”在汪静之那里,则表现为《惠的风》中“五·四”新人追求爱情的勇敢:“伊的幽香潜出园外,?去招伊所爱的蝶儿。?雅洁的蝶儿,?薰在蕙风里:?他陶醉了;?想去寻着伊呢。”等等。但“五·四”时期的白话诗人们所追求的个性自由与解放的突出特点是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精神主体的严重冲突中进行的,而民族主义则是属于集体主义的,自由主义则又是属于个体主义的,这对矛盾在当时中华民族危亡的特殊历史环境和“救亡图存”高于一切的情形下,得以暂时解决;但也为日后诗界埋下了深刻的隐患,存在着不可弥合的裂痕与分歧。也正因为如此,此后决定了他们当中相当大一部分诗人(如郭沫若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放弃了自由主义立场,转向马克思主义,走上了诗歌为战争或政治服务的道路,结束了“五·四”白话诗开创的争取个性自由与解放的自由主义历史,并让另一部分继续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白话诗人们在后来的历史中尝尽了命运的苦果。
二、朦胧诗主潮:人的崛起
无论是谢冕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也好,还是孙绍振的文章《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的文章《崛起的诗群》也好,从表面上看,这“三个崛起”都是在谈论诗的崛起,实质上,就其本质而言,他们谈论的都是人的崛起——作为朦胧诗主潮当代性的人的崛起。“五·四”时期白话诗人们因为没有人权而争取的是做人的权利,到朦胧诗时代,由于“文革”对人权的破坏,而使人丧失了人权;因此,朦胧诗人们争取的则是重新做人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讲,朦胧诗是“五·四”白话诗后断裂的人本主义历史的再次承接和延续,有所不同的是前者追求的是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后者追求的则是作为“大写的人”的人性复归。这一点,我们从创刊于1978年后来被称为朦胧诗民间诗刊《今天》的创刊号代发刊词《致读者》中完全可以看出:“……‘五·四’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
“文革”当时以其极左的方式严酷地摧毁了人本主义思想,以至于使得那个时期成为中华民族建国以来失去理智、失去人性的文化最恐怖时期。著名诗评家刘登翰在他的文章《一股不可遏制的新诗潮》中曾经如此准确地描述过“文革”这个黑暗的年代:“在十年浩劫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剩下一种抽象的‘阶级关系’;而‘斗争哲学’又被视为处理人的关系的唯一准则。革命不是在关心人和发展人的个性的轨道上推进,而是把所有尊重、关心和爱护人的美好情感统统当作资产阶级人性论打倒,代之以封建专制的兽性。”而具有同样思想但却一直被排斥在朦胧诗群之外的朦胧诗人黄翔,早在他1968年创作的一首诗《野兽》中,就表达了他对“文革”黑暗年代罪恶的批判和控诉:“我是一只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我的年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诗人痛心疾首地感受到:别人在践踏我,我也在践踏别人,人践踏人,人与人之间在相互践踏的混乱历史现象。足见那个年代简直就是只有兽性,没有人性的相互践踏的年代。
然而,人性终究不会因压抑而湮灭,相反,当噩梦结束的时候,它会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喷发出来。“文革”浩劫结束后,第一个公开站到诗界面前的是北岛的不屈的人。1979年3月,中国诗坛最权威的杂志《诗刊》发表了北岛的诗《回答》,诗中诗人高亢地向世界宣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而且同时以无比抗争的精神力量表达出作为“大写的人”的坚强不屈与勇敢自信:“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北岛《回答》诗句)从此,中国诗坛人影攒动,而最先感受到这股人的崛起力量的是谢冕,他急忙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中惊呼:这是“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他们是新的探索者。这种情况之所以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也带来了令人瞠目的‘怪’现象。”虽然谢冕仍有些顾虑,但最终在文章的结尾他还是坚定地对此加以肯定:“我以为是有利于新诗发展的。”接着孙绍振也感受到了这股力量,撰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予以支持;徐敬亚也感受到了,同样撰文《崛起的诗群》加入进来。这样,在“三个崛起”的推动下,整个中国诗坛都感受到了这股人的崛起的力量,一时间,被“文革”极左思想中断了的“五·四”白话诗运动中倡导的人本主义精神,又重新回到了再度崛起的朦胧诗歌当中。
不过,此时的朦胧诗主潮的人本主义思想用孙绍振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的话来说:“在年轻的革新者看来,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精神敌对力量,那种‘异化’为自我物质和精神的统治力量的历史应该加以重新审查。”走出了初始时期诗人对“文革”政治异己力量摧残与蹂躏的反抗与抗争,转向对人的价值、地位、权利以及人性的追寻与确认。于是,从最初的粉墨登场到最后的悄然落幕,朦胧诗人们先后塑造出了各式各样的人的形象;北岛的人,除了反抗和不屈的人之外,还有渴望美好情感的人:“我也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北岛《结局或开始》诗句)。舒婷的人是背负历史苦难和理想的人:“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舒婷《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诗句),是独立自主的人:“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舒婷《致橡树》诗句)是渴望美好爱情的人:“和鸽子一起来找我吧/在早晨来找我?你会从人们的爱情里?找到我?找到你的?会唱歌的鸢尾花”(舒婷《会唱歌的鸢尾花》诗句)。顾城的人是寻找光明的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诗句),“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顾城《我们去寻找一盏灯》诗句);是童话的人:“我希望/每一个时刻?都象彩色蜡笔那样美丽?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诗句)。梁小斌的人是反思探索的人:“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诗句)。食指的人是亲情与关爱的人:“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诗句)。江河的人是见证民族历史的人:“我想?我就是纪念碑?我的身体里垒满了石头?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沉重?我就有多少重量?中华民族有多少伤口?我就流出过多少血液”(江河《纪念碑》诗句)等等,无数诗人以其自我形象化身的人构建起了朦胧诗又一意识形态话语中心——人本主义话语中心。总之,这场自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孕育到80年代达到高潮的朦胧诗运动,实质上,就是一场人的崛起运动。在这场人的崛起运动中,正如李泽厚在《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中所说的:“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一个造神造英雄来统治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回到了五四期的感伤、憧憬、迷茫、叹惜和欢乐。”随后,人性、人道主义、人的异化不再成为思想禁区,而在这场人的崛起运动中崛起的人也不在是“五·四”时代的“旧人”,而是“具有现代特点的自我”的“新人”,正如徐敬亚在《崛起的诗群》中所说的:“他们坚信‘人的权利,人的意志,人的一切正常要求’;……他们的‘自我’,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中国现代公民。”一句话,朦胧诗主潮崛起的当代性正如北岛在他的诗《宣告》中所呐喊那样:“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把人凸显到再大不过的程度了。
三、低诗歌主潮:人的解构
到了低诗歌时代,诗歌中的人已经走下了崇高而完美的圣坛,成为全人、真人;同时低诗歌也开始了全面的审视人性,发现人性并非完美,人性中既包含着善的因素也包含着恶的因素。其实,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在低诗歌诞生之前,中国新诗一直未意识到这一层,而盲目地在追求单一化的审美功能,以崇高的现象掩饰崇低的本性,直到低诗歌才有勇气敢于“在美学上追求多元化,集审美与审丑于一体,以崇低的精神解构现实,以反饰的力量建构未来,……摆脱‘真、善、美’的绝对崇高控制,同时展开对‘假、丑、恶’全方位的审丑与解构。”(丁友星《低诗歌狂潮》语)而且将解构深入到人性的深处。
低诗歌在其浮出水面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潜藏期,当第三代诗人喊出“崇高真累”,打起“反崇高”的旗帜,让于坚“戴眼镜的脑袋”“从尚义街六号?法国式的黄房子?老吴的裤子”胯下钻出来后,又“渴望钻进一条裙子”(于坚《尚义街六号》诗句);韩东“从远方赶来”,爬上大雁塔,“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韩东《有关大雁塔》诗句);唐亚平“把女人拉出来?让她有眼睛有嘴唇?让她有洞穴”,然后“在女人的乳房上烙下烧焦的指纹/在女人的洞穴里浇铸钟乳石”(唐亚平《黑色洞穴》诗句);李亚伟“撒在干土上的小便”掀起中文系这条“撒满钓饵的大河”(李亚伟《中文系》诗句)波涛使人都变得平庸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信号,又一个新诗潮运动开始了它元初的孕育。直到1989年这个具有转折性历史意义的年份的到来后,诗坛才隐隐约约感受到些什么,然后,出现了类似于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后,“西方知识分子从左派激进主义运动的失败中退回语言学的领域,寻求一种想象的,以低调的社会姿态包裹着的彻底的不妥协的思想意向”(陈晓明《无望的叛逆》语)现象一样,中国新诗开始了中国新诗史上从未有过的最痛苦的反思,以至于后来出现了下半身写作对人的肉体的解构与审丑,以及新世纪通过网络推动的垃圾写作对异化的物的解构和反饰写作对人的精神即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解构的诗潮。在这一解构下形成的诗潮被我们命名为低诗潮,诗歌被命名为低诗歌。关于这个命名,张嘉谚在他的文章《中国低诗潮》中称:“中国低诗潮是若干低诗歌写作支流从各个起点汇集而成的诗写潮流。”同时,他进一步补充阐释说:“但又不是一般的状态与潮流,它汇聚的是所有从事低诗歌或阳性诗写作的诗人、流派或团体。……正在成为牵动中国诗歌整体向前发展的潮流。”丁友星在他的《低诗歌狂潮》中称:“低诗歌正在不约而同地从下半身、荒诞、反饰、后政治、垃圾、撒娇、放肆、无限制、平民、俗世此在、民意说唱、赶路、草根写作等诗歌的各个方向朝一起涌来,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网络诗坛汇集成了一股被我们已经命名了的低诗歌狂潮,并且已经开始逐渐影响到传统媒体诗歌的发展。”
低诗歌有三句最著名的口号:一句是“谁牛逼,我操谁!”(典裘沽酒语);一句是“就是让你不舒服!”(凡斯语);还有一句就是“没有什么不可以!”(丁友星语)。虽然这三句话说起来文字上有点糙,但理却一点也不糙,它们已经成为低诗歌解构一切中心主义、消解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原始动力,使之从现代主义直接推进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关于解构,美国解构主义大师杰·希利斯·米勒阐释说:“‘解构’这个词暗示,这种批评是批某种统一完整的东西还原成支离破碎的片断或部件。它使人联想起一个比喻,即一个孩子把父亲的手表拆开,把它拆成毫无用处的零件,使其根本无法重新安装。”为了达到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目的,解构主义中心人物——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借助了一个词语“差异性”作为他们解构的共同活动方式。而低诗歌为了实现其解构一切中心主义、消解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目标,却借助了“崇低”与“反饰”两个词语作为他们解构的共同活动方式而争取话语权力,这一点,丁友星在他的《低诗歌狂潮》一文中作过这样表述:“低诗歌的出现似乎就是为争取诗歌话语权力而来的。……其在诗学追求上具有二求性,即:崇低与反饰。”其实,和德里达一样,低诗歌也完全可以只借助一个词语“反饰”作为解构的共同活动方式就够了,因为“反饰”也包含着崇低、审丑和解构,“反饰主义原则就是以解构、审丑、批判、崇低为主的原则”(丁友星《低诗歌狂潮》语),只不过是为了更加突出“崇低”在崇高独裁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作用而已。
在“赵丽华事件”令新诗遭恶搞的诗人专访中,伊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中国人是天生的后现代主义者,可以解构一切。”这话一点不假,在人的解构问题上,低诗歌的策略就是首先借以“崇低”的活动方式,把现代主义建立起来的人的主体性作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崇高”堡垒瓦解掉,从而降低做人的标准,在一个真正的“平面”上建立起无任何负载的、轻松自如的、自由敞开的“去中心”艺术。在这个“平面”上,杨春光的人可以是愚蠢幸福的:“这一天?早晨起来解小便?却把大便从小便里解出来??中午?我一觉起来?以为还是早晨?便磨蹭着去刷牙?一挤牙膏?却把老婆刚生完孩子的奶挤了一地??下午?我爬起来写作?写了一万五千字?却忘了写题目?我便满屋子去找题目?找来找去找到了一条上吊的绳子在房梁上??到了傍晚?我回忆我若有这样如此完整的愚蠢的一天?我一生也就只有满足了……”(杨春光《我有愚蠢的一天》诗句);徐乡愁的人也可以是自暴自弃、自甘平庸的:“我的理想就是考不上大学?即使考上了也拿不到毕业证/即使拿到了也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了也会得罪领导?我的理想就是被单位开除??我的理想就是到街上去流浪?且不洗脸不刷牙不理发?精神猥琐目光呆滞?招干的来了不去应聘?招兵的来了不去应征?我一无所有家徒四壁?过了而立还讨不上老婆?我的理想就是不给祖国繁衍后代??我的理想就是把自己的腿整瘸?一颠一拐地走过时代广场?我的理想就是天生一副对眼?看问题总向鼻梁的中央集中?我的理想就是能患上癫痫?你们把我送去救护?我却向你们口吐泡沫”(徐乡愁《我的垃圾人生》诗句);丁目的人还可以是无聊病态、自轻自贱的:“我是一个喜欢被虐待的家伙?如果你打我左脸?我的右脸就会不舒服?如果你打我右脸?我的左脸就会难受?所以你要打最好是左右开弓?把我的脸打烂?可只打我脸我的头又会难受?那么你也把我的头打烂吧?不要犹豫放开你的手脚打?就当我是一条死狗?你把我的身体也打烂吧?你把我的屁股也打烂吧?我是天生的贱种?你要打就要打得我屎尿横流?那样我就会舒服极了”(丁目《贱人》诗句)。此外,低诗歌还借以“审丑”的活动方式,解构人的肉体和异化的物,把性和粪抽空加以鞭挞,如典裘沽酒的诗《谁牛逼,我就操谁》、小蝶的诗《我要翻身做主人》、杨瑾的诗《我渴望和所有的美人都有一点关系》、丁友星的诗《性别的反饰》、尹丽川的诗《舒服些,再舒服些》、老德的诗《电话做爱》、野狼的诗《我渴望裸体的生活》、徐乡愁的组诗《屎诗系列》、散心的诗《把俺的屁放在媒体头条新闻》等等,抵达从来没有抵达的“低贱化、世俗化与肉体化”(张嘉谚《丑陋现世主义》语)状态。但低诗歌解构话语“场在”中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还是其对人的精神,即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解构,因为这是一切“逻格斯中心主义”里的中心来源的专制。同时,低诗歌因为强调崇低、审丑、解构,也使一些诗人错误地、毫无顾忌地、无度地揭示自己的个人隐私,比如性欲、死念、羞辱、绝望、精望失常,以及对妻子、父母、兄妹、子女等的扭曲和变态心理,表现出其虚无主义精神,以及混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对政治、社会、理想、前途、人民的命运、人类的未来等等,统统漠不关心,完全以感观主义把握世界与人的一切。其实,低诗歌解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并不是不要理想和英雄。相反,低诗歌也需要英雄和理想,只不过是低诗歌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背后发现了一种完整的形而上学的专制,于是改变过去传统诗歌——高诗歌沉湎于完美的、虚幻的乌托邦的自慰,开始了低诗歌范式的进一步逆转,并借助“反饰”作为他们解构的共同活动方式,由原来的从外在呼唤人的解放、自由、理想、正义等堂而皇之的话语转入人的意识的拓进与剖析,给予诗人以极大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空间。试看伊沙就在车过黄河的过程中,道是无意却有意地把尿撒向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黄河:“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我深知这不该?我应该坐在窗前?或站在车门旁边?左手叉腰?右手作眉檐?眺望像个伟人?至少像个诗人?想点河上的事情?或历史的陈账?那时人们都在眺望?我在厕所里?时间很长?现在这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流远”(伊沙《车过黄河》诗句)。丁友星就在爆破长城过程中,找到了具有思想精神象征意义的症结具象长城:“它的一端系着秦朝的开始?另一端系着未来的延伸将?中华民族的腾飞捆绑于?铜鼎铁柱的专制”,并声称:“爆破长城是我夙愿的已久?模拟千遍万遍的现实何止?长城早被我的意识深处爆破/在它残垣断壁的废墟中?我拾到了孔子孟子诸子百家?拾到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拾到的一个又一个熟悉与陌生?都是炎黄子孙的过往匆匆??爆破的纷飞与散落?远于历史近于现实?高于天空低于海洋?大于世界小于尘埃?深于意识浅于物质?每一片?都伤及历史现实未来的既往”(丁友星《爆破长城》诗句)。此外,还有典裘沽酒、大路朝天、丁友星、赵造等的“天安门”系列诗歌等。这些诗歌分别以不同意指合流直通意识形态的内核,造成了对形而上学传统中心主义“深度精神模式”拆除的可能性。
至此,通过对中国百年新诗主潮当代性及其嬗变过程的分析研究,我们还意外地发现:中国新诗三大主潮:白话诗主潮、朦胧诗主潮、低诗歌主潮,正好也把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近百年的诗歌艺术发展描绘为与之相对应的三个艺术模式,即依次是:模拟尝试模式、现代主义模式和后现代主义模式。虽然由中国新诗三个主潮描绘出来的这三个艺术模式,不能完全概括近百年中国新诗发展的全部内容,正像三个主潮一样;但除却战争诗歌和阶级斗争诗歌两次历史性偏移以外,其余诗歌现象几乎基本上都可以归纳进这三个艺术模式和三大主潮,比如白话诗主潮模拟尝试模式涵盖了创造社、新月派、象征派、湖畔派等在内三、四十年代以前的诗歌创作,朦胧诗主潮现代主义模式涵盖了“文革”地下诗歌、西部诗歌、新边塞诗歌、朦胧诗歌以及朦胧诗后的一部分诗歌写作和流派在内的诗歌创作,低诗歌主潮后现代主义模式涵盖了朦胧诗后的一部分诗歌写作和流派写作、下半身写作、垃圾写作、反饰写作以及所有崇低写作在内的诗歌创作。因此,我以为,把握住中国新诗这三大转折、三大主潮和三大理论,以及依此归纳延伸出的三个艺术模式,也就基本上把握住了整个中国新诗;这也就是我著此文研究中国新诗主潮的当代性及其嬗变过程的目的所在,并寄期望于以此推进中国新诗的进一步发展,使其真正融入世界诗歌潮流的同步律动。
责任编辑常智奇
丁友星男,安徽省无为县人,文学学士,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级研讨班(中青年文学理论评论家班)毕业,系安徽省阜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现供职于安徽省阜阳市政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