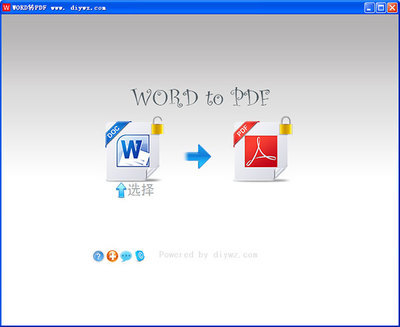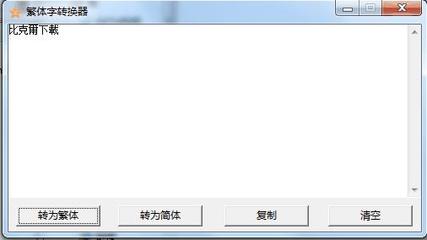[摘要]“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
1933年1月1日,《东方杂志》第30卷第一号(新年特大号)用了78页篇幅刊登了142人的梦想。 (南方周末资料图)
1932年底,《东方杂志》发起了“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的征文活动,许多答案充满“载道”与“言志”的成分,有些完全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有些干脆就是一篇社会改良设计书,有些答案比较悲观,有些答案颇为有趣,从大的背景看,虽然难脱时代的烙印,今天重读当年应征的文章,仍然饶有兴味。掩卷遐思,有着难以言说的感慨。
1932年11月1日,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为纪念创刊30周年,发起“一九三三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的征文活动,向全国各界著名人士遍发通启(编者注:普遍通知的启事,这里就是征稿函),就以下两个问题征询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通启发出四百余份,到了12月5日征稿截止日,收到一百六十余封答案,其中有一小部分是《东方杂志》的读者看到了通启自动应征的。1933年1月1日,《东方杂志》第30卷第一号(新年特大号)用了78页篇幅刊登了142人的答案。丰子恺、陈升洪别出心裁,用八张漫画作答。
梦,从来都是个人的精神活动,天马行空,诡异离奇,几人梦到过国家的未来?所谓“中国梦”也好,“生活梦”也罢,都是方便说,只不过是个人对国家、对生活的未来的憧憬而已,许多答案充满“载道”与“言志”的成分,有些完全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有些干脆就是一篇社会改良设计书,有些答案比较悲观,有些答案颇为有趣,从大的背景看,虽然难脱时代的烙印,但八十年后读起来,仍饶有兴味,掩卷遐思,有着难以言说的感慨。
一、大同世界
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1887-1958)的答案在乌托邦梦想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一个大联邦。这大联邦内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世自由。而我们中国呢,当然也是这个大联邦中的一个部分,用不着多讲了。”
银行家俞寰澄(1881-1967)的梦比柳亚子要具体一些:“我想未来中国,一定是个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连高丽、台湾,或者日本都包括在内。未来两字是无穷无尽的,我希望实现在三十年之内。”
中央研究院部干事杨杏佛(1893-1933):“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人们有合理的自由,同时有工作的义务,一切斗争的动机与力量应用在创造与服务方面。物质的享用应当普遍而平等。”
镇江民政厅盛止戈:“未来的中国,因人心悔祸而善而无内争;政治入轨而贪污绝迹;实业振兴而外货滞销;交通发展而商贾载途;教育普及而无一文盲;乃至国防齐备,失地收复,不平等条约悉数取消;遂执国际之牛耳,解除世界弱小民族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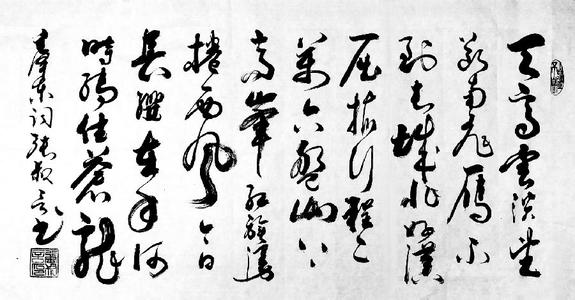
二、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1898-1958)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人类的生活是沿了必然的定律走下去的。未来的中国,我以为将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因了我们的努力,我们将会把若干年帝国主义者们所给予我们的创痕与血迹医涤的干干净净,我们将不再见什么帝国主义者们的兵舰与军队在中国内地及海边停留着。我们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个人为了群众而生存,群众也为了个人而生存。”
与郑振铎有同样理想的还有豫丰纱厂毕云程(1891-1971):“在我梦想中的中国,没有榨取阶级,也没有被榨取阶级,大众以整个民族利益为本位,共同努力,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以提高整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并努力充实国防,以保障整个民族的安全。”
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1893-1986):“我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我理想的中国的人都是能纯客观,都懂得唯物辩证法,并都是能实践唯物辩证法的。”
暨南大学教授李石岑(1892-1934):“(一)经过若干年军阀混战之后,又经过几次暴动之后,中国必然走上科学的社会主义之路。(二)……老庄哲学在某部分特别为中国人所推崇,尽去一切消极颓废的解释,建立中国哲学上的认识论。(三)关于中国未来的道德思想,儒家的学说定遭一般人的唾弃,而墨家的实践精神却会在发挥而特发挥,建立中国未来的新道德。”
暨南大学教授漆琪生(1904-1986)依据国际形势,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冷静的推断:“中国今后的姿态如何?纯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何种势力获得最后的胜利而定。如果帝国主义的势力获得最后的胜利,则中国今后必将夷为纯粹的殖民地;如果世界革命的机运已熟,以苏俄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势力获得胜利,则中国亦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
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讲了三个梦,第三个梦是,他来到一个山水明媚的村庄,土地有千余亩,耕种不用牛,不用犁,而用最新的洋机器,收成比用机器前增加一倍,生活一天天优裕,不独吃的不错,而且穿得很整齐,村中有小学,有幼稚园,有托儿所,有治疗所,有合作社,有巡回图书馆,甚至有临时电影场。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到农村公共食堂去吃……他们在休息时爱唱一首歌,其中有一节是:“这儿不是什么人间天国,也不是什么世外桃源,不过已挣脱了锁链,大家种自己的田。”
丰子恺漫画。 (丰子恺/图)
三、政治现实主义
外交是现实和严酷的,外交部长罗文幹(1888-1941)即使谈梦,也是现实的:“政府能统一全国,免人说我无组织。内争的勇敢毅力,转用来对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
实业家穆藕初(1876-1943):“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选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以肃官方。经济上必须保障实业(工人当然包括在内),以促进生产事业之发展。合而言之,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
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1901-1968):“我梦想中未来的中国,包含下列几种元素:第一,我梦想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我们现在什么都依赖政府:让他‘强’我们,要他‘富’我们,而政府内说是要富要强必先‘训’我们(编者注:此指国民政府的“训政”,1931年5月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但是结果上他们又觉得孺子不可教,以为非管束住我们,他们不能干。然而社会是管束住了,政府还是干不好……第二,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那么我就梦想一个政府,他至少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怎样才能有这样一个政府?我梦想它。”
光华大学教授诸青来(1878-?):“(一)本国人民不论属于何种阶级,信奉任何主义,均有参政权。……绝对不用武力。”
94岁老人马相伯(1840-1939)的中国梦是由弟子徐景贤笔记的: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专政,亦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
四、悲观的艺术家
与教授们相比,艺术家则比较悲观。小说家巴金(1904-2005)答道:“我现在的这种环境中,我连做梦也没有好的梦做,而且我也不能够拿梦来欺骗自己。‘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总感到冷,觉得饿,我只听见许多许多人的哭声,这些只能够使我做噩梦。”在回答“梦想的个人生活”时,他说:“我的希望是什么?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
小说家老舍(1899-1966):“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即使偶得一梦,甚是吉祥,又没有信梦的迷信。至于白天做梦,幻想天国降临,既不治自己的肚子饿,更无益于同胞李四或张三。”
画家钱君匋(1907-1998)对未来悲观透顶:“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我深信着我的梦想是千真万确的。因照着目前的情形而看,而推测,要他不一团糟,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我们的生存的苦,将跟着逐渐加浓。”
小说家茅盾(1896-1981):“梦想是危险的。在这年头儿,存着如何如何梦想的人,若非是冷静到没有气,便难免要自杀。”
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1885-1967)从自编的《看云集》摘了两句话作答:“信仰与梦,恋爱与死,也都是上好的麻醉。能够相信宗教和主义,能够做梦,乃是不可多得的幸福的性质,不是人人所能获得。”
五、梦见叉麻雀
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1900-1990):“绝对的开明专制的阶段是必须的。(编者注:民国时期,军阀割据,社会上有久乱求治之思,因而曾兴起一股歌颂开明专制、甚至法西斯的思潮)中国历史上当得起这个名字而无愧色的只有秦政。然而他是失败了。以中国之大,真的专制之治本不容易,加以近代思想之庞杂,国际关系之错综,更不容易。况且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所以假使我有了梦,也只是大大小小的噩梦。这明明与我自来怀抱的理想相反。但我觉得中国无救则已,有救大约非走过这一阶段不可。至于谁来干这桩大事情,反正不会是我们,我不配说话。谚曰:‘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又曰‘左右做人难’,此之谓也。”
开明书店编译所长夏丏尊(1886-1946):“我常做关于中国的梦……惊醒时都要遍身出冷汗,梦不止一次,姑且把它拉杂写记如下,但愿这景象不至实现,永远是梦境。我梦见中国四万万人都叉麻雀,最旺盛的时候,有麻雀一万万桌。”
六、希望与梦想
《论语》半月刊主编林语堂(1895-1976)说,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革命,眼看一个不贪污、不爱钱、不说空话的政府几乎就要实现,如今南柯一梦还是南柯一梦;其后人家又一次革命,我又一次热心,又在做梦,不过此时的梦,大都做得不长,到了革命成功,连梦也不敢做了,每夜总是一觉睡到天亮。“我不做梦,希望民治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我不做梦,希望全国有代议制度,如国民会议、省议会等,只希望全国中能找到一个能服从多数,不分党派,守纪律,不捣乱的学生会。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第一流政治领袖出现……。我不做梦,希望监察院行使职权,弹劾大吏,只希望人民可以如封建时代在县衙门击鼓,或是拦舆喊冤。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一点事绩。我不做梦,希望国中有许多文学天才出现,只希望大学毕业生能写一篇文理通顺的信。我不做梦,希望政府能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及向农民加息勒还账款。”
北京大学教授李宗武(1895-1968):“梦想中的未来中国的轮廓,我实在写不出来,所以我只写了下面的几个希望来替代:我希望中的军人不要只能内战,不能抗外;我希望军事当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我希望学者们不要相率勾结军阀,联络要人,忘却了你们的本来工作;我希望要人们摆正良心,多为国家做些好事,不要今日发表谈话,明日发表宣言,以欺骗民众混蒙是非;我希望我们能杀尽一切贪官污吏;……我希望商人们能放出天良,多推销国货;我希望新闻记者能负起指导民众思想及社会改革的责任,不要只搬运些不重要的消息就算毕其能事;我希望中国青年都能具有耐劳负重救国自强的伟大精神,不要专学那浮躁轻薄的下流勾当;我希望中国民众能监督政府,使政府不为少数军阀所私,使政府为民众全体的政府。我想,如果我的希望达到了,我的梦想中的未来中国,也就实现出来了!”
七、一个环保主义者的百年梦想
暨南大学教授张相时(1894-1989)用一段故事讲述了他的中国梦: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重重压迫下苦战了50年,于1983年建立了一个理想的、真正平等的、和平的新国家。在新社会生活的中国人,每天工作三小时,便能得到很丰富的物质享受,他们的社会情调到处都呈现着音乐的、美术的和诗歌的和谐。但他们并不因此懒惰下去,他们利用有余的时间,下了一个动员令,要把全国所有的大江小河的两岸和河底都用青石砌成,目的是在使全国境内不见一滴污浊之水。
这个清水动员令自然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所以只费了40年的工夫便完全做到了。这个千古未有的伟大工事完成了五年,不单是全国的巨川细流不见一滴污水,连在中国海岸荡漾了千万年的赤水也清且漪了。
中华理想国五十年(2032年)正月元旦,正是他138岁的生日,他虽住在喜马拉雅山的长江源头,全国各地的朋友,乘坐时速500英里的飞机来向他祝寿,劝他出山观光,国家的物质建设和进步,任他们说得天花乱坠,都不足以动心,惟有“江河之水清且漪”是他所梦想维劳的。因为他在100年前就提倡“清水运动”,一百年前的理想现在既已实现,岂可不去亲自看看?“于是驾了一只轻便小艇,顺江而下,沿途所见果然水天一色,清漪可爱,舟行一月而达数十年足迹不到的上海。”
八、宗教信仰
翻译家查士元把中国的未来寄托于宗教:“未来中国的国民,应各有一个健美的宗教心,即信仰。没有信仰的个人,其努力不待说是放纵的,害社会、伤国家的。有了信仰,思想上即有许多差别,但各人将都能出其优长之处,来装饰一个国家。”
国立上海商学院教授俞颂华(1893-1947)宣传以学佛解脱人民的烦恼与苦厄:“在这乱离之世,精神上真是痛苦极了。在精神上痛苦的时候,我觉得佛学书中所讲的解脱人生苦厄的方法,有几种是颇有道理的。于是我对于个人生活,亦做了一个梦想。我每天能够抽出两小时至四小时的时间,作为静坐的修养工夫。(现在困于尘劳,不能如此)养得此心无罣碍,非常圆明。一切烦恼苦厄,都不足以扰我心灵。在最短期间,我于寂静中能够领悟到解脱烦恼苦厄的简便方法,俾得将这方法说与别人,使别人亦能受用。”
九、朴素的愿望
开明书店编辑顾均正(1902-1980):“我梦想在未来的中国《东方杂志》每年至少有四千万份的销路,《东方杂志》的排字工人每天只要做四小时的工作,便足以维持生活。”
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1889-1996):“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文中人物生卒年系据网络资料添加,容或有误,引用时请注意核对。个别人物未能查到,只好付之阙如——编者)返回腾讯网首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