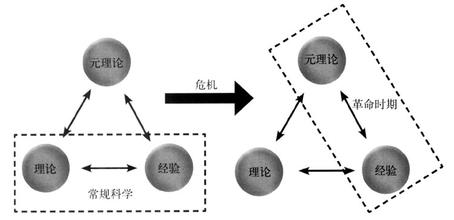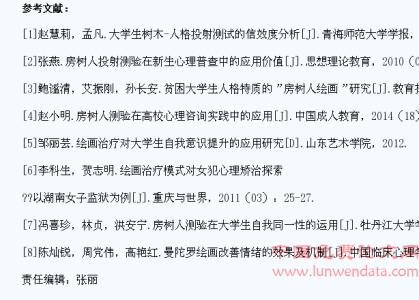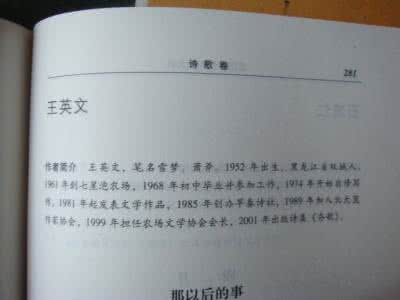
黑土之上的龙江美丽而神奇;但地处偏远的边缘,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龙江诗坛更是边缘的边缘。在当代文学潮起潮落的五十余年里,龙江的诗歌创作时而惊涛拍岸,时而悄无声息,可是始终不绝如缕,踏实稳健地默然前行着。它缺少领骚全国潮流的殊荣,当然也没有关内某些身份“跟风”文学速朽的悲哀;它没制造过巨大的引人注目的轰动效应,却在中国当代诗歌的每个转折处都不乏它的介入和影响。它众多的诗章共同推出的那道五光十色、令人目眩神迷的艺术风景线,尽管其间菁芜夹杂;还是形象地浓缩着龙江半个多世纪的社会风貌,构成了龙江儿女心灵世界的一份活档案,提供了许多富有魅力的现代性艺术质素。
客观地说,龙江在历史上与缪斯并不是绝缘的。远在清代就有吴兆骞等的流人诗歌崛起;上世纪30年代,杨靖宇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歌》、李兆麟的《露营之歌》等抗联战士的诗篇,和金剑啸、萧军等写作的文人诗歌一样,所抒发的战斗情怀与献身精神,强悍铿锵、气贯长虹。解放战争时期,方行、熏风等一大批成名诗人和年轻的歌者,从延安、晋察冀等革命根据地随军闯入关东,写下共和国在龙江大地上最初的诗行,他们的创作可视为龙江新诗的源头。上世纪50年代后,大量铁道兵和十万转业官兵相继“移民”到龙江这个在全国最早解放的工、农业强省的版块上,他们在拓荒黑土地的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黑土地的精神文化。至此,梁南、林子、陆伟然、彩斌、王忠瑜、沙鸥、严辰、吴越、陈国屏、黄益庸等辗转而来的南方诗人,和王书怀、刘畅园、满锐、中流、王野等本土诗人汇聚一起,借助1950年创刊的《黑龙江文艺》和《北方文学》等报刊园地,竞相挥毫泼墨,共同支撑起龙江第一个绚烂壮观的诗歌繁荣时期。
回视那个诗歌时代我们惊喜地发现,龙江诗坛原本具有一批可以问鼎全国诗界的优秀诗人和一个很高的艺术起点。当时,鲁琪、陆伟然、彩斌、王忠瑜的北大荒开垦心曲,满锐、中流、周蒙的森林吟唱,赤叶、李志、黄益庸的煤矿情怀,王书怀的乡土精神掘进,梁南的国际友情抒怀,沙鸥对北国自然物象的风景扫描,严辰对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深情凝眸,吴越对革命年代优卓品性的张扬,刘畅园对细微、弱小生命和事物的诗意抚摸,林子爱情心理的大胆袒露,这些林林总总、魏紫姚黄的选材和情思风貌,在国内都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诗人们或长于激情抒放,或注重技巧雕琢;但历史的规定性敦促着他们无不把书写置身于北方,展示黑土地上开拓者重塑历史和现实的使命感和浪漫的理想,表现历史前进中的本质力量,作为自己诗歌的美学风范;并将这种美学风范一直隐性地持续到文革的发生。事实上,他们也正是以黑土气息和向上品格的高扬,走进了全国乃至全世界读者的期待视野。如陆伟然的《垦荒诗草》从平凡的劳动中捕捉诗美讯息,其中的《雨中》写到“隆隆的雷声滚过草间/仿佛是千条大江从天上泻下/霎时间天地一片白烟/垦荒的拖拉机突然消失了/消失在茫茫的暴雨里边//只看见闪电把黑云撕破/只听见雷声炸碎整个草原/连老槐树都把腰弯下/啊雨点好猛烈的雨点//沼泽被雨点敲起了一身水泡/野鸭子夹起了翅膀逃窜/这时候拖拉机却从雨中钻出/像一列舰艇破浪向前……”凌驾于残暴的风景线上,耸起与奔突的是垦荒队员坚强不屈的人生观念,相生相克的人与自然对立互补的视角里,跳荡着作为一代开拓者高昂奔放的进取心音,自我意识与使命意识达成了谐和共振。即便是巴波隶属于个人化视境的《我的故乡有一条小溪》,唱出的也是歌颂的调式,“如今,十年后我回到故乡访问小溪/这里,寻不见垂柳,也寻不见芦苇/我在陌生的建筑群中走来走去/望不尽的车间使我忘记了寻找小溪”,平朴的语言跳转中对建设者的赞美和对生活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必须承认,上世纪50年代的龙江诗歌也有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在以颂歌为主调的抒情模式里,大部分诗人追逐激情的宣泄而疏于技巧的经营,视野相对狭窄,个我的情感基本被对现实、历史、时代的歌唱遮蔽,此间重要的政治事件、运动乃至时事都不同程度地在诗歌中有所反映,但对新生活建设中的矛盾和黑暗面却缺少必要的警惕和分析。显然,这是时代痕迹的烙印,而非龙江诗坛本身的过错。
大跃进时期,龙江诗歌自然无法超越时代的苑囿。它也曾放过“卫星”,使民歌满天飞。甚至像王书怀这样优秀的诗人也难以脱俗,写下《大萝卜》一类可笑的诗歌。1959年出版的一部《黑龙江民歌选》表明,当时的龙江诗歌除了个别作品把镜头对准劳动、爱情和少数民族风情,还有一定的艺术品位之外,其结果就是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浮夸臃肿的笑话。当历史的脚步跨进文革的门槛之后,龙江诗坛更是风雨飘摇,破败不堪,遭受到了空前的虐杀。且不说大部分诗人被剥夺了歌唱的权力,能够出笼的诗歌也都因为意识形态的高度统摄,而蜕变为文攻武卫的政治武器和工具,发挥着“匕首”和“投枪”的效用。从遗存下来的《哈尔滨红卫兵报》、《兵团战士》报和《新曙光》、《黑龙江个人》等杂志,可以看出那时所谓的诗歌从情感状态、想像路线乃至语汇的选用,都是高度模式化的,歌颂毛主席,表现战士的斗志,记录文革真相和过程以及被批斗者的心理痛苦是其主要的价值取向。它们以一种“伪现实主义”的姿态,为那个特定的疯狂时代做了一次清晰的历史定格。但是,真理无法被永远蒙蔽,人们的精神是不屈的,在“帮派文艺”甚嚣尘上的黑暗时分,仍然有林子、李凤清、谢文利、鲍雨冰等一些诗人,在颂歌的规范和主潮之外,携着缪斯的火种巧妙地在政治的空隙里穿行、歌唱,以感情的真切和对生活的深入发掘赋予了作品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另外,在大庆工人的歌唱中也不时涌现出一些比较优秀的诗篇,如《铁人诗抄》就典型地表现了他们冲天的豪气和献身精神,今天读来仍会给人一种力的震撼。
一经从十年浩劫中走出,雨过天晴后的龙江诗歌便重新焕发出生机。梁南、刘畅园、赤叶、吴越等老一代“归来者”雄风不减,特别是梁南在《我这样爱过》、《追随在祖国之后》等诗中,把文革中受尽折磨却始终深爱祖国的复杂情感传达得沉郁顿挫又别致异常,风靡一时。而文革后如雨后春笋一般成长起来的诗人马合省、庞壮国、李琦、韩作荣、邢海珍也纷纷尽显风采,捧出自己个性的太阳,在传统的合唱里奏出强劲的音响。尤其令人振奋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随着地域性文学意识的觉醒强化,龙江的抒情群落也和国内的西部诗派、巴蜀诗派、红土诗派、黄河诗派相呼应,亮出黑土诗派(也称北大荒诗派、黑水诗派)的旗帜,并进行积极而稳实的构建。诗人的触角纷纷回归自己脚下的视野,用本土的自然景观、文化背景承载心灵的多元情绪与地域精神意向。这种普泛操作无疑契合了沈从文的湘西魂、孙犁的白洋淀系列、周涛杨牧的西部鸣唱等众多成功范式,开拓了龙江诗歌走向辉煌的最佳途径。其间,朦胧诗时代即走向缪斯的张曙光、冯晏、文乾义、朱永良、罗凯和被誉为第三代的朱凌波、包临轩、潘洗尘、杨川庆、马永波、李德武等从高校走出的诗人渐次崭露头角,上世纪90年代初桑克、迟慧、杨勇、杨拓、吴铭越等大量更年轻的新生歌者陆续加盟,龙江诗歌的队伍愈加壮观。几代诗人之间团结协作,相互尊重,没门户之见,无宗派之嫌,多元并举,群芳荟萃,龙江诗歌进入了最活跃、最辉煌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龙江诗歌,首先是题材、情感与风格在不同的诗人那里像八仙过海,各臻其态。如庞壮国有关沼泽荒原系列的地域性吟唱,因契合了龙江向上的意识,把北中国撩拨得激情四溢;马合省的《苦难风流》里旋起了一股男性的力的风暴,极具理性张力;李琦的诗和她诗的题目《天籁》一样,呈现出一种出水芙蓉般的天然之美;邢海珍对世道和人生的智慧洞察,宣显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由、良知和达观的生命态度;王长军的鹤乡悄吟、陈士果的野性森林、罗凯的水之天地建构,也都堪称独步。但在抒情的地平线上都屹立着一个大写的自我形象,从集体抒情到彰显个性,张扬人的价值、尊严和情感即主体意识成为诗人们不约而同的审美选择;并且和抒情视野的日益开阔同步,理性质素明显加强,对生活的认识趋于深层,这是这个时期龙江诗歌的又一个变化。这一点不说男性诗人梁南的《我追随在祖国之后》那种反思悲剧历史的情感深度,马合省的作品《陵园》对人们赞美的烈士、英雄“疼痛而安宁”灵魂关怀的人性深度,也不说桑克在《夜景》里对乡村的“冷”、“穷”和安静背后“恐怖”、“孤寂”的命运咀嚼中透出的思想深度;光是女诗人李琦向生命本质与人生究竟凝眸的《新年快乐》就让我们确信龙江诗歌的思考力是如何的深厚。“岁月带走了岁月/五十年前我的母亲在江边跳绳/五十年后我的女儿在江上滑冰/从父亲的玩具到我女儿的玩具/那盏老式的台灯/好像只亮了几个黄昏……楼上一只钢琴曲响起/像是为我的心事伴奏/很轻很忧郁/弹琴的人 也弹奏着时间/已经有什么/从十指间流过”。诗人谛听着生命的剥落声,她仿佛悟出现实的每一瞬间都有一个超时空的存在,它左右着生命的向度和进程。诗是借时光飞逝内蕴人生逃不出时间控制的哲思禅理,一种苦乐莫辨的“新年快乐”祝福中,已有一种超绝时空、等齐生死的意味,时光生命的千古浩叹也令人澄静。再次是艺术手法和技巧的成熟度在不断攀升,而且愈到后来先锋派、现代派愈唱了主角。传统艺术方式在优秀“老”诗人那依旧强劲有力,大部分诗人则大胆吸纳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以及朦胧诗的思想和艺术血液,实验的创新的先锋探索更具有了市场潜力。上世纪90年代初大器晚成的张曙光,在温和而睿智的外表下潜伏着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其叙事性探索引领了全国风气之先。他的《1965年》对一些事件、细节、场景等因子的复现,展开的是某种生活本质以及作者在精神上对它们的人性理解,个体和时代、历史遭遇时的心理痛感的揭示不乏深刻的自省和反思的意味;自我分析、叙事和抒情的适度调节把诗歌的主旨传达得节制而含蓄。潘洗尘的《六月,我们看海去》、《饮九月初九的酒》等诗歌,以长长的絮絮叨叨的句子铺展情思,其独特的宣叙调曾令当时很多大学生诗人着迷。马永波的语言纯度相当出色,翻译背景赋予了他一定的思考性质,他最钟情复调和客观的叙事,其《电影院》通篇运用了小说的笔法,“她仿佛一下子/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像一场空气中蒸发的小雨/她转学了?得了肺炎?我不知道/现在我已记不得她的模样了……”客观场面、心理活动、解剖评论搅拌,情节、细节、氛围兼俱,有种非诗体的芜杂,但童年性觉醒的意识流遐想和自言自语的独白却被表达得别开生面。进入21世纪以来,龙江诗坛群星闪烁、诗人辈出的喧闹景观更不必细说。除了许多极具才华和潜质的龙江诗人在全国继续书写辉煌,除了龙江的主流载体一如既往地支持诗神之外;老牌的和新生的民刊和网刊竞相亮相,如张曙光、文乾义、桑克等支撑的《剃须刀》,杨勇、杨拓等创办的《东北亚诗刊》,马永波领衔的《流放地》,白帆主持的《星光》,尤其是龙江打入北京的中岛坚持近二十年的《诗参考》,都已引起国内诗界的广泛注意,成为龙江诗歌生长的理想沃野。它们昭示着龙江诗歌的后继力量让人充满希望。
纵向的梳理可以看出,与生活、时代保持同步的密切联系,是龙江诗歌的优良传统和不断向前发展的必要保证。但这和其他省份的诗歌创作是同声相应的,不足以标示出龙江诗歌的独特个性。我以为龙江诗歌在当代五十多年的诸多艺术积累中,能最集中、最鲜明体现自身的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形到质地雕塑出了北方的影像。应该说在表现日常性次元的情思方面,龙江诗坛涌现出了许多心灵表现能手,方行的《我的歌》、刘畅园的《微笑》、林子的《给他》、孙玉洁的《少女的心》、李玲的《那时花开》等,它们以抒情主体心理结构的投入,从感性接近诗的内向化追求,在某种程度上都契合了诗的本质。潘洗尘《六月,我们看海去》更是把情思调得潇洒自如,得心应手,“看海去看海去没有驼铃我们也要去远方……我们是一群东奔西闯狂妄自信的探险家啊……” 一代青年烦恼甜蜜乃至调皮的青春期心理骚动在诗人笔下表现得异常娴熟、细腻与优美;那种一往直前的进取意识真真催人感奋。但是代表龙江诗歌风貌的多数作品还是把注意力放在对北方影像的捕捉和塑造上。诗人们通过在姿色纷呈的龙江风光中纵横驰骋的普泛操作,以一江一山、一草一木散点扫描的集聚,筑起了平原黑水、林海雪野为骨架的北方自然雕像。它的世界,饱孕着兴安岭绿色的思绪,回荡着黑龙江滚滚的波涛;有松涛怒吼的澎湃,有冬天溃败的嘶嚎。它的世界,闪耀的是寒风是飞雪,是鄂伦春人疾驰的雪橇,是冰城人火一样炽热的心。它的世界,悬映着火山熔岩的奇景,充满了达子香扑鼻芬芳的诱惑;也记录着乌裕尔河的汛期和鹤群,镂刻着瑷珲城沉淀的耻辱和不屈的沉思……这是北疆,是一幅幅情趣酣畅的风景风俗图画,是其他世界不可企及的特殊存在,是读者熟悉而陌生的崭新世界。但是黑龙江诗歌生命魅力的亮点还不在这独特风景的客观性再现,给北方涂画肖像;而在于超越外在事像原生态恢复,对边疆人精神领域的深入探询,雕刻出了渗透着深刻思考力量的粗犷而坦诚的北方灵魂,使地域色彩浓郁的组合意象无不洋溢着心灵的新渴望和新吁求。如“矿山路已被风雪遮盖/用手脚重趟开路来/喜井下矿工频传捷报/笑风雪错认了矿山女人//茫茫雪白了矿区世界/步步齐深了行人身腰/卷扬机声引导她们去处/红绿色头巾在风雪中飘摆”(赤叶《瑞雪》),在肆虐的暴风雪中,矿山女人飘摆的鲜艳头巾渲染出她们的泼辣和热烈,一列列满载原煤矿车见证着一群女强人的勤劳与坚强。“痛苦消失得太快了/一个短暂而快乐的雷鸣/我又能依偎大地/这次不是一只脚/而是全身,是全身//在这片号称酱缸的死沼/我和我的弟兄/肩并肩,挨着挤着/躺成一条洁白的路……既然车轮奔行的时代/必须从这里出发/我们负重/我—们—负—重”(庞壮国《沼泽里,白桦躺成路》)。那白桦分明是北方精神的隐曲的外化,它躺倒的同时却崛起了一种豁达悲壮的信念,笑对“丢失”和“奉送”的命运承担,勇于负重,不正是北方人性格的写照吗?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殊的的环境孕育了人们特殊的性格和心理结构,冰天雪地和野性十足的大森林、大草原铸就了北方人的骁勇彪悍,豪放刚毅;偏远闭塞的地域使他们承继了祖先的豪爽肝胆、热情品德。李光武的《野仙人掌》、岛子的森林组诗、潘洗尘的粗豪歌唱也都表现着类似的审美情趣。诗人们对自然的介入与认同,为北方人健康向上的心态找到了感性寄托的合体衣裳,自然世界也成为他们追求价值的部分体现。
二是龙江诗歌大多充溢着一股沉郁、阳刚之气。龙江诗人们歌唱黑土地,更歌唱黑土地上回荡的时代风云。阔大深厚、广袤无垠的黑土地,本身既有一种美学状态上的阳刚之美,而它那饱孕激情与使命意识、发端现实又指归现实的审美意向统摄,使对人生历史、自然心灵的多向度观照在烙印着当代性和历史感特征的同时,都或浓或淡地传达了中华民族建国以来的进取情绪,尤其是展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华民族转折时期的改革雄姿,跳动着时代精神的脉搏。“对岸又在倾倒炉渣了/太子河边像竖起一道火墙/我像看见了那些工友/怀着水蜜桃般饱满的快乐与热情/紧张地工作在炉旁//发电厂的蒸汽隐隐可见/月亮像一面明镜嵌在天上/谁把满天的星星都摘了下来/你看,那工人住宅区的电灯/比星星还多,还亮”(沙鸥《太子河的夜》)。“为什么流动着那么多的歉意/我们的民族不该这样/看着你土地一样慈爱丰厚的脸庞/我真想叫声‘爸爸’扑进你的怀里/把我年轻而骄傲的头/紧紧贴进你粗布衣内温热的胸膛……既然我是你的儿子,是你并不属于你的大手大脚的儿子/那么,就让我在这个崭新的黎明/用忠诚和钢铁在民族的脊梁上/为你,为北方的农民/为我的父亲,塑起一座不朽的雕像”(潘洗尘《北方的农民啊,我的父亲》)。这些腾发于工厂周边、生活细节等葱郁现实风景线的诗思,都是把现实看成历史的一段流程一个断面,放在整个历史的广阔背景下考察,使现实题材超越了自身而具有纵深的历史感和深远的哲理思辨力量。它们在展示工人的劳动身影、农民和作者心灵起伏流程时,铺展了一幅幅城镇、乡村变迁的历史画轴,传达了作者一腔爱与礼赞的肯定性情怀;并且在深情赞美中渗透着深刻的哲理:工人、农民是生活的缔造者,历史的主人。哲理不是诗,但理性思辨的介入无疑加强了诗的深厚度和情感涵量,使诗通向了高维境界,龙江诗歌沉郁、阳刚之气的形成和这种追求是休戚相关的。如梁南的《我追随在祖国之后》写到,“我是滚滚波涛中微不足道的一滴水/我是银河系中最渺小的一颗星/我是横越荒寒的天鹅翅上的一片羽毛/我是组成驼铃曲中的短促一声……昨天已经过去,明天即将诞生/探索的岂止是我,是一支欢乐的队伍/一个自强的民族,我是走在最后一个人”。诗内站在昨天和明天交界点上的理性思考,使本来瘦弱的诗人变成了精神上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硬汉子,其悲喜混杂的沉郁豪气和高尚的人格追索在十年浩劫刚刚过去之时,因为契合了民族求强的心理,和时代精神达到了同构;所以曾经令无数读者震撼和动容。龙江诗人的很多歌唱即便是纯个人的心灵鸣奏也都具有上述诗歌质的一致性。冯晏的《敏感的陷入》、《复杂的风景》已不再满足于单向度的情感抒发,而走向了经验和哲学的经营,貌似书写个人的体悟和思绪,实则是人类共有而不易为人理解透彻的质地铸造,其女性细敏的感觉里带着一股男性的“硬气”。宋歌、王野、庞壮国、聂振邦、李凤清、范震威、刘海岳等人的一些诗歌也都具有这种功能。龙江诗歌正是以这种沟通心灵和现实、统一个体认识和群体意向的向上意识指归为灵魂,使一扇扇现实的窗口里映射着民族、人类的希望、思考、欢乐和前景,扩展了诗歌的冲击力和共鸣层。
三是复合型艺术风格的建构。龙江诗歌因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所以形成了以阳刚为主的刚柔相济的复合状态。一方面是庞壮国、岛子、梁南、潘洗尘的苍健沉约、质朴诡奇的雄风;一方面是刘畅园、李琦、雪村、鲍雨冰的泊淡空灵、美丽清新的秀气。并且同时呈现多样的个人风格,如庞壮国的诗沉雄潇洒,李琦的诗深沉纯净,桑克的诗唯美睿智,马合省的诗恢宏浑厚,王书怀的诗质朴诚挚,罗凯的诗悠远静穆,沙鸥的诗奇巧缜密,文乾义的诗神秘奇诡……这是北方伟力与秀美、豪气与柔情、神奇与富足并存的双重特征土地上腾升的全新诗美。龙江诗歌的主流美学形态是阳刚的,它也讲巧思,但缺少南方人的精雕细刻,而大多大起大落,纵横开合,刀刻斧削,棱角分明;语言选择上比较注重地域性,乡土气浓郁,语言格调也是在多元化前提下,多豪放慷慨,粗犷朴实。如庞壮国的《关东第十二月》就呈现着这种风貌,“是黑钙土在大雪壳子里怀孕的季节/是桦皮小船扣在石滩上憋憋屈屈单相思的季节//是苇塘子剃了光头叫小兔子在清清亮亮头皮上打出溜滑的季节/是棉靰鞡毡疙瘩走上毛毛道让西北风也在脚底下吱妞妞哼起二人转的季节……充满传奇充满生机充满矛盾充满笑话充满土地与人的庄严感啊关东十二月/我的乡情我的骄傲我的苦中乐我的人之初或许又将是我归宿啊关东十二月”,大量铺排饱蕴北大荒泥土味的风景风情风俗,浩大壮观;既不是单纯的直吐心曲,又不是纯粹的意象暗示,而是调和二者,使诗情在写实与象征间飞动,急缓适度,浓淡相宜。整体抒情格调豪迈沉稳,如雷鸣闪电,似狂狮怒吼,又像大江涌奔、高扬澎湃,贴切地再现了北方粗犷的性格。再如“总感觉有风/自某一高处吹来//那只扭转乾坤的巨手/曾以一枝中楷羊毫的锋芒/穿透历史/勾勒出一幅气吞山河的北国风光”(白帆《读毛泽东书法》)。诗人神思独运地采用象征艺术,抓住和毛泽东个人的生命、生活乃至精神密切相关的书法,做不可复制的精神解读。但绝非拖泥带水,啰里啰唆,只几个中国革命历史“点”的攫取,就读出了毛泽东书法之遒劲与自然,读出了毛泽东书法“高远之意境”与“磅礴之气势”,读出了一个完整的伟人形象。原来书法意象乃是毛泽东神采、性情、精神、思想与业绩的象征和隐喻。而老诗人刘畅园的小诗则体现着龙江诗歌的另一种审美情趣。她常常从生活的细波微澜里透视事物的本质,淡雅清新,鲜脆自然,形神兼备,虚实相生,玲珑剔透。“牛儿/不要生气/给你一片芳草地//沉重的颈轭/已有几千年了/应把它交给机器//你在树下休息/歇荫凉/爷爷牵着你”(《山村·孩子》)。物境和心境的契合,烘托出了一个类乎于古典意境的审美天地,它细腻轻柔,风味浓郁,犹如一幅乡间优美恬淡的画轴,舒缓中透着敏捷的灵气,明朗的生活节奏与轻轻点点的语言节奏融为一体,恰切地传达了生活的灵秀和作者的爱慕、亲近情愫,煞是可爱。对于龙江诗歌的复合型艺术状态,也许有人会说它风格不够鲜明集中。我以为一个诗派的形成绝非众多个体求同的过程。只要在龙江精神的灵魂统摄下,反映出龙江风貌,体现出生活的本质趋向,传达出龙江的别有气质;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和途径都属于龙江诗;并且它们会增强龙江诗整体风格的肌体和绚烂美感,开拓读者的期待视野。我这样描述龙江当代诗歌并不是就认为它没有缺点;相反我们必须直面如下残酷的现实:如今的龙江诗歌向内已远难与翘楚关内的北大荒版画和迟子建、阿成的小说比肩,向外更无法同喧腾的江浙、川蜀诗坛抗衡。在这片丰饶、神秘的土地上,拳头诗人与拳头诗作寥若晨星,屈指可数;几年前为构建黑水抒情群落摇旗呐喊的才子才女们已云散星消,呼声日渐沉寂。诗坛重心开始再度由北中国向长久统领风骚的杏花春雨江南回归,黑土精灵们的鸣唱再也获取不了太多的青睐与掌声。龙江诗歌沉寂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于以下的探索偏失造成的。
它在发掘北方坚韧豪爽、粗犷而坦诚的灵魂内质的同时,却对北方文化心理中的迟缓保守、散惰闭塞、竞争意识淡薄的负面积淀审视不够,没触摸到北方强悍而忧郁的精神内核。要知道,高纬度的寒冷气候、大开大合的雄壮风景线、偏远落后的生存状态和众多抒情者的移民结构,规定了黑土诗人无法完全吟起江南柔婉顺畅的小调,只能产生粗豪而忧郁、沉重又悲壮的心态,这里的人间烟火并不就是田园牧歌和静美的山水,真正的气味是艰难沉重的。可是龙江大量的城市诗歌和乡土诗中偏偏找不到这些,对于它们开拓进取主题的呈示只是单色调的乐观豪情,而高亢与孤独交错的忧患心理根本不予表现。尤其是充斥报刊的那种表象描摹加生硬议论的钢厂、啤酒厂抒情诗和几位善写田园牧歌诗人的歌吟,认人感到北方人的情绪透明乐观得难以置信。而书写心灵的诗篇则大多缺少对人类生存和命运的终极关怀。过度强调个体经验而滋长出的自恋情结,把诗当作盛装圆熟甜腻无伤大雅或个人隐私的器皿,个人欲望的暴露和宣泄把诗搞得面目皆非。黑土诗情感和思辨冲击力薄弱的致命原因是缺少哲学意识的支撑。
由于对地域色彩的极度高扬、扩张,使处于精神遨游中的诗人把“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鲁迅语)理论尊为神明奉为圭臬,甚至作为探索的唯一取向,渐渐地审美观念便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偏狭与倾斜。驱使诗人仅仅为北方画像,蜕化为民俗演绎、事件罗列,沉入了民间文学的泥淖。在文化热论的隐性统摄下,有的一头扑入了野性大森林;有的紧紧追逐鹤乡悄吟;有的踏上了逐遥的采金路;有的则迷失于魔鬼荒原的沼泽地……充斥感官的意象是驿站古道、鱼刺兽骨、原始松涛、熔岩陈迹;是桦皮船边沉闷的拉网号子,是木刻楞旁呻吟死去的梅花鹿;是粗犷与野性交混,是荒凉与神秘并存。仿佛文化仅仅存留于历史古迹之中。这种向传统洪荒深掘的寻根意向使曾于诗中绵延的现实风景线悄然退却,风化为岁月的烟尘。许多龙江诗人只是罗列大量地名、景观、风俗,犹如块块石头堆在一起呼风唤雨、天玄地黄,缺乏生气的灌注,只是东方的而非现代的,只是生态的而非心态的。这样不可避免地疏离、淡化了社会现实,失落了时代制高点,失落了文学的价值所在。其实寻根本身并没有错,黑土地文化的本土性和移民性的交合构成是一块理想的耕耘领地。遗憾的是黑土诗歌的寻根并没表现出黑土文化移民变衍过程中寻到了些什么,丢失了些什么,对中原文化有何扬弃和发展等诸多有价值的因素,而只停浮于北方文化的表层。
诗歌观念的偏颇也是龙江诗歌的一大缺憾。很多人以为诗歌就是主观情感的自然流露,这种迷信必须击破。因为诗是主客契合的情思哲学,优秀的诗要使自己获得深厚冲击力,必须先凝固成哲学然后再以感性形态呈示出来。而黑龙江的很多诗人的诗探索恰恰没有达到这一点,他们的笔在每一次景象过程中很少受到理性对诗的规律性认知的控制。为什么?因为在这片土地,哲学意识文化智慧本来就十分薄弱、贫瘠,时下商品经济冲击和功利诱惑,尤其是地域观念铸成的封闭文化心态无时不在牵扯着诗人的目光,致使他们只能贴伏在地面上挪移或跟在他人身后亦步亦趋,难以潜入生命本体、博大宇宙等空间进行形而上思考,究明人类本质精神,从而进行一种智力操作;只能产生一种情思漫游,缺少智性的自娱诗。大量泛泛之作都视野狭窄,意蕴形态平面浅白,多半停浮在春天、梦、蒲公英等浅层次,充满亮色的范畴天地,无形地削弱了诗的情绪容量与情绪宽度;传达上往往少内敛与约束,常使诗沦为情思的放纵。零星的哲理诗也因思辨力肤浅而成为一种意志教诲的简单载体。诗的肌体失去了哲学的筋骨,自然也就失去了深刻度与穿透力,崛起大手笔的诗人与诗作也就失去了可能的契机。事实上,黑土青年诗之所以远远落后朦胧诗乃至于坚、韩东、周伦佑等新潮诗人,关键不在艺术技巧的好坏,而在诗本身所包含的哲学意识强弱上。
另外,龙江诗歌界传统的断流、群体思想淡薄也是造成其影响不大的原因。相对于文化丰饶的中原各省来说,黑龙江毕竟地处边塞、开发短暂、文风不盛、传统稀薄,时断时续。立足这片土地,诗人们面临的是漫天荒芜遍地荆棘,是缺少承继的大段历史空白与文化断裂。他们没有规律可循,缺少传统可以借鉴,每一步精神跋涉就必须依靠自己艰难而痛苦的摸索,付出巨大代价来独立完成;而探索本身并不仅仅意味着永恒与成功,这样创作上就难免菁芜交杂、瑕瑜互见、泥沙俱下。尤其是几次文学运动对这块土地的轮空,使诗人们形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他们怯于同先锋诗潮诗人抗衡较量,缺少进攻性;而这种被动文化心态又反过来牵制创作实践,愈不敢向诗的峰顶冲击,心理上就愈加保守萎缩。渐渐地,他们一边承认本土的贫瘠;一边又满足于在本土性环境中生存,导向了一种恶性循环,只能长期囿于自己的一方天地苦心经营,重复自己与过去,做原地踏步运动,如此就根本无法窥视到自己天地外诗坛的风雨潮汐、态势走向。面对纷纭流转的人生现实,仍承袭固有的思维方式、艺术技巧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发生错位与冲突,表现上出现误差趋于贫困,与新潮艺术审美流向拉开距离。与黑土地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相对应,黑龙江诗人很少像关内诗人那样,常常聚在一起把酒临风研磨诗艺;而总如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一样,各自经营一方天地,你钻入森林探宝,他走向黑龙江兴安岭渔猎,我则稳坐责任田埂。松散、游离,单打独斗,相互间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个体游勇格局,处于“散”的原生状态,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漫山遍野到处噼噼啪啪放小鞭,很难一下子放出几枚响当当的二踢脚,很难有一个共同目标做大面积的定点辐射轰炸,形成整体轰动效应,完整集中地凸现出北大荒的灵魂影象。
我们应该认识到:龙江以白山黑水、林海雪原为骨架的雄性地理文化风貌,与龙江乐观与忧患并存的社会心理现实,呼唤着诗歌巨星的诞生,可龙江诗坛却因种种迷失很少崛起大气的诗人诗作,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不可小视的遗憾。但只要龙江诗歌注意寻找新的理论支点,重新确立恰切的抒情位置,在走向地域的同时再走出地域,接通个体情思与群体意向,达到地域意识与时代精神的同步共振,自娱性与使命感的双向平衡;不断强化诗人的理论素质,构筑感性与理性契合、情绪与智慧交汇的诗歌本体;大胆汲取西方艺术与兄弟省份诗歌艺术的经验、营养;向北大荒整体精神风格凝聚,龙江诗坛就会告别目前身陷的沼泽地,拥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