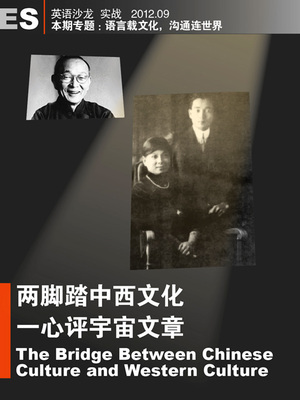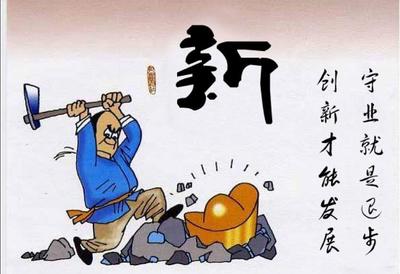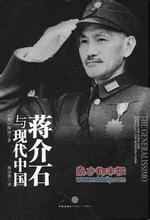《易经》的宇宙观
应该说这个题目是比较大的,我似乎没法完成,给自己出个难题吧。《易传》对《易经》的阐发,已经上升到哲学的层次(远超过我的理解能力),加之古今学者的无穷延展与深入,一定会有“《易经》的宇宙观”这种东西,虽然它可能因人而异。
我拟此题目,出发点是:《易经》分上下,上经起于乾坤,终于坎离,下经起于咸恒,终于既济未济。不管古今的专家学者对此有多少种的解释,亦或是其中有人与我的理解相同,在我看来其中所包含的宇宙观是极其朴素和容易理解的。
阴阳,是古人的最大发明。把世间的万事万物及其性质,抽象为阴阳,是一种高度的抽象,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在《易经》乾之卦爻辞解一文中,我写道:“这里仅略作解释,世界上事物及其性质,都可以抽象为阴阳,在用于人事时,强弱、实虚男女、积极消极、富贫等,是最为基本的取象。在这里,阳爻在人可取象为能人,在事可取象为富足。”
这是非常容易认识的,我也不必再啰嗦。
那么上经起于乾坤,是什么用意呢?
在这里,我不赞同乾父坤母,化生万物的说法。也许有这种意蕴,但这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作易者应该是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按不同的比例、不同的顺序所组成的,乾为纯阳,坤为纯阴,所以列作起首,仅此而已。
上经终于坎离,又是什么用意呢?
大家都同意,坎指月,离指日。我认为,作易者应该是认为,万事万物的运行,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在古代,人们所发现的自然的最明显的规律性就是日月运行。上经终于坎离以明之。
所以上经起于乾坤,终于坎离,可以概括为“宇宙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以不同比例、不同顺序构成的,其中有如同日月运行一样明显的规律性。”
而下经起于咸恒,终于既济未济又是什么用意呢?是不是象有人说的上经讲天道,下经言人事?应该不是,因为上经与下经中大事与小事交替错杂出现,并没有分属上、下经。
请大家注意,上经中,乾与坤、坎与离各自的上三爻与下三爻均不相应,而下经的咸与恒、既济与未济都是上三爻与下三爻一一相应的卦。而阴与阳的相应,表示着它们之间的某种联系。所以,下经起止卦所表示的意义,应该是——“万事万物中最为普遍的规律是联系” 。
但这两组卦除相应却有另外的不同。
因为阴与阳的关系,除了应以外,还有比的关系,即阴与阳相邻,这也是一种联系,这种联系似乎比应的联系更为密切,这里我不去讨论究竟密切到什么程度,只是想把这两种联系放在一起来考虑。
既济与未济向我们展示了最为复杂的联系,每一爻不但与邻近的爻比,而且还与远处的爻相应。初爻、上爻,比一应一,其它二、三、四、五均为比二应一。
这还是第一层的联系,如果加上由所应之爻带来的间接联系,关系就复杂了。比如,初爻比二爻,应四爻,而四爻又比三与五,这样,初与二、三、四、五诸爻都可以轻易地建立联系。是如果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作比喻,这可是一种最为复杂的人际关系,当然也就是最难于处理的人际关系。
可以打一个比方,将这六爻比作三对夫妻。他们之间不管是通过丈夫或是妻子,建立了很好的联系,使得同性之间、异性之间都非常熟悉,也时常会有大团体、小圈子的活动。这样好不好呢?我们可以说好,多好的人际关系境界呀!但这种联系极难长久,说得轻松一点,可能会发生什么争风吃醋的小事,说严重一点,可能关系破裂,互生怨恨,甚至产生祸患。这就是既济卦辞“初吉终乱”的意思,其中一个“乱”字,极为形象,可谓用意深刻。
这是拿夫妻做例子,换作上下为两个单位,也同样,每个人与其它同事及另一个单位的人建立的这种联系,使得这两个单位的管理变得极为困难。
而古今的易家,不断地鼓吹既济卦为阴阳各爻均“当位”,是完美的排列,是所谓的“定”,因为不可以永远“定”,停止了发展,所以才全部倒了个个,接上未济,就全都不“当位”了,再接着向“当位”发展呗!极为荒唐。这些说法的根源,恐怕就在于《易传》,而我们的老学究们死抱着《易传》,就是不肯放手。
所以,在下经,作易者其实是在提出严峻的问题:怎样处理事物之间的这种联系?怎样处理那种几乎无法处理的混乱联系?如何避免混乱局面的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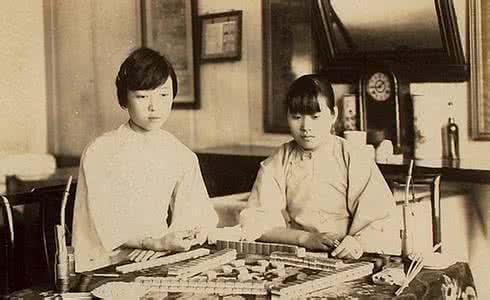
勉强为之,难免粗陋,唯盼高人指点。
中国古人的宇宙观
晋代是中国山水情绪开始与发达时代。阮籍登临山水,尽日忘归王羲之既去官,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山水诗有了极高的造诣(谢灵运、陶渊明、谢朓等),山水画开始奠基。但是顾恺之、宗炳、王微已经显示出中国空间意识的特质了宗炳主张“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王微主张“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而人们遂能“以大观小”又能“小中见大”。人们把大自然吸收到庭户内。庭园艺术发达极高庭园中罗列峰峦湖沼,俨然一个小天地。后来宋僧道灿的重阳诗句:“天地一东篱,万古一重久。”正写出这境界。而唐诗人孟郊更歌唱这天地反映到我的胸中,艺术的形象是由我裁成的,他唱道:
“天地入胸臆,
吁嗟生风雷。
文章得其微,
物象由我裁”!
东晋陶渊朋则从他的庭园悠然窥见大宇宙的生气与节奏而证悟到忘言之境。他的《饮酒》诗云: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
中国人的宇宙概念本与庐舍有关。“宇”是屋宇,“宙”是由“宇”中出入往来。中国古代农人的农舍就是他的世界。他们从屋宇得到空间观念。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击壤歌),由宇中出入而得到时间观念。空间、时间合成他的宇宙而安顿着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是从容的,是有节奏的。对于他空间与时间是不能分割的。春夏秋冬配合着东南西北。这个意识表现在秦汉的哲学思想里。时间的节奏(一岁十二月二十四节)率领着空间方位(东南西北等)以构成我们的宇宙。所以我们的空间感觉随着我们的时间感觉而节奏化了、音乐化了!画家在画面所欲表现的不只是一个建筑意味的空间“宇”而须同时具有音乐意味的时间节奏“宙”。一个充满音乐情趣的宇宙(时空合一体)是中国画家、诗人的艺术境界。画家、诗人对这个宇宙的态度是象宗炳所说的“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六朝刘勰在他的名著《文心雕龙》里也说到诗人对于万物是:
“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味如答。”
“目所绸缪”的空间景是不采取西洋透视看法集合于一个焦点,而采取数层视点以构成节奏化的空间。这就是中国画家的“三远”之说。“目既往还”的空间景是《易经》所说“无往不复,天地际也。”我们再分别论之。
宋画家郭熙所著《林泉高致·山川训》云:
“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其人物之在三远也,高远者明了,深远者细碎,平远者冲澹。明了者不短,细碎者不长,冲澹者不大。此三远也。”
西洋画法上的透视法是在画面上依几何学的测算构造一个三进向的空间的幻景。一切视线集结于一个焦点(或消失点)。正如邹一桂所说:“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而中国“三远”之法,则对于同此一片山景“仰山巅,窥山后,望远山”,我们的视线是流动的,转折的。由高转深,由深转近,再横向于平远,成了一个节奏化的行动。郭熙又说:“正面溪山林木,盘折委曲,铺设其景而来,不厌其详,所以足人目之近寻也。傍边平远,峤岭重叠,钩连缥缈而去,不厌其远,所以极人目之旷望也。”他对于高远、深远、平远,用俯仰往还的视线,抚摩之,眷恋之,一视同仁,处处流连。这与西洋透视法从一固定角度把握“一远”,大相径庭。而正是宗炳所说的“目所绸缪,身所盘桓”的境界。苏东坡诗云:“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真能说出中国诗人、画家对空间的吐纳与表现。
由这“三远法”所构的空间不复是几何学的科学性的透视空间,而是诗意的创造性的艺术空间。趋向着音乐境界,渗透了时间节奏。它的构成不依据算学,而依据动力学。清代画论家华琳名之曰“推”。(华琳生于乾隆五十六年,卒于道光三十年)华琳在他的《南宗抉秘》里有一段论“三远法”,极为精彩。可惜还不为人所注意。兹不惜篇幅,详引于下,并略加阐扬。华琳说:“旧谱论山有三远。云自下而仰其巅曰高远。自前而窥其后曰深远。自近而望及远曰平远,此三远之定名也。又云远欲其高,当以泉高之,远欲其深,当以云深之。远欲其平,当以烟平之。此三远之定法也。乃吾见诸前辈画,其所作三远,山间有将泉与云颠倒用之者。又或有泉与云与烟一无所用者。而高者自高,深者自深,平者自平。于旧谱所论,大相径庭,何也?因详加揣测,悉心临摹,久而顿悟其妙。盖有推法焉!局架独耸,虽无泉而已具自高之势。层次加密,虽无云而已有可深之势。低褊其形,虽无烟而已成必平之势。高也深也平也,因形取势。胎骨既定,纵欲不高不深不平而不可得。惟三远为不易!然高者由卑以推之,深者由浅以推之,至于平则必不高,仍须于平中之卑处以推及高平则必不深,亦须于平中之浅处以推及深。推之法得,斯远之神得矣!(白华按“推”是由线纹的力的方向及组织以引动吾人空间深远平之感入。不由几何形线的静的透视的秩序,而由生动线条的节奏趋势以引起空间感觉。如中国书法所引起的空间感。我名之为力线律动所构的空间境。如现代物理学所说的电磁野)但以堆叠为推,以穿斲为推则不可!或曰:将何以为推乎?余曰‘似离而合’四字实推之神髓。(按似离而合即有机的统一。化空间为生命境界,成了力线律动的原野)假使以离为推,致彼此间隔,则是以形推,非以神推也。(案西洋透视法是以离为推也)且亦有离开而仍推不远者!况通幅邱壑无处处间隔之理,亦不可无离开之神若处处合成一片,高与深与平,又皆不远矣。似离而合,无遗蕴矣!或又曰:‘似离而合,毕竟以何法取之?’余曰:‘无他,疏密其笔,浓淡其墨,上下四旁,明晦借映。以阴可以推阳,以阳亦可以推阴。直观之如决流之推波。睨视之如行云之推月。无往非以笔推,无往非以墨推。似离而合之法得,即推之法得。远之法亦即尽于是矣。’乃或曰,‘凡作画何处不当疏密其笔,浓淡其墨,岂独推法用之乎?’不知遇当推之势,作者自宜别有经营。于疏密其笔,浓淡其墨之中,又绘出一段斡旋神理。倒转乎缩地勾魂之术。捉摸于探幽扣寂之乡。似于他处之疏密浓淡,其作用较为精细。此是悬解,难以专注。必欲实实指出,又何异以泉以云以烟者拘泥之见乎?”
中国人的最根本的宇宙观是《易经》上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我们画面的空间感也凭借一虚一实、一明一暗的流动节奏表达出来。虚(空间)同实(实物)联成一片波流,如决流之推波明同暗也联成一片波动,如行云之推月。这确是中国山水画上空间境界的表现法。而王船山所论王维的诗法,更可证明中国诗与画中空间意识的一致。王船山《诗绎》里说:“右丞妙手能使在远者近,抟虚成实,则心自旁灵,形自当位。”使在远者近,就是象我们前面所引各诗中移远就近的写景特色。我们欣赏山水画也是抬头先看见高远的山峰,然后层层向下,窥见深远的山谷,转向近景林下水边,最后横向平远的沙滩小岛。远山与近景构成一幅平面空间节奏,因为我们的视线是从上至下的流转曲折,是节奏的动。空间在这里不是一个透视法的三进向的空间,以作为布置景物的虚空间架,而是它自己也参加进全幅节奏,受全幅音乐支配着的波动。这正是抟虚成实,使虚的空间化为实的生命。于是我们欣赏的心灵,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神理流于两间,天地供其一目。”(王船山论谢灵运诗语)而万物之形在这新观点内遂各有其新的适当的位置与关系。这位置不是依据几何、三角的透视法所规定,而是如沈括所说的“折高折远自有妙理”。不在乎掀起屋角以表示自下望上的透视。
早在《易经》《系辞》的传里已经说古代圣哲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俯仰往还,远近取与,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而这观照法表现在我们的诗中画中,构成我们诗画中空间意识的特质。
诗人对宇宙的俯仰观照由来已久,例证不胜枚举。汉苏武诗:“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魏文帝诗:“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曹子建诗:“俯降千仞,仰登天阻。”晋王羲之《兰亭诗》:“仰视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又《兰亭集叙》:“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谢灵运诗:“仰视乔木杪,俯聆大壑淙。”而左太冲的名句“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也是俯仰宇宙的气概。诗人虽不必直用俯仰字样,而他的意境是俯仰自得,游目骋怀的诗人、画家最爱登山临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唐诗人王之涣名句。所以杜甫尤爱用“俯”字以表现他的“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他的名句如:“游目俯大江”,“层台俯风渚”,“扶杖俯沙渚”,“四顾俯层巅”,“展席俯长流”,“傲睨俯峭壁”,“此邦俯要冲”,“江缆俯鸳鸯”,‘缘江路熟俯青郊’,‘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等,用俯字不下十数处。“俯”不但联系上下远近,且有笼罩一切的气度。古人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诗人对世界是抚爱的、关切的,虽然他的立场是超脱的、洒落的。
中华易经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天人宇宙观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