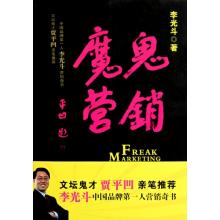为什么墓葬艺术在传统中国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几千年而不绝?在古代日本,建造大型室墓的本土传统在佛教传入之后就基本上消失了。但是在中国,佛教艺术的引进并没有阻碍墓葬艺术的发展,而是导致了两个并行不悖的传统。甚至当一些皇帝以佛教或道教为国教之后,他们也并没有丧失为自己建立豪华陵墓的热情。
▲ 河北宣化张文藻墓门上的鬼神图
文 | 巫鸿
宣化张氏墓地中的张文藻夫妇合葬墓建于1093年,属于中国墓葬艺术史上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装饰以大量壁画,充实以大量随葬品,这个墓反映出千年以前发展起来的,分别以马王堆汉墓与满城汉墓为代表的两类建筑和装饰程序,在此时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综合体。
与宋、辽、金时期的很多壁画墓类似,张文藻墓煞费苦心地以砖模刻仿木构建筑,创造出材料的幻视。此墓的修建者和装饰者把雕塑与绘画合而为一,用不同形状的砖组装成立柱、斗拱、椽子和假窗,再以艳丽的图案精细装饰。潜藏在这一做法下的仍然是明器的概念:“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借助于把一个砖墓转化为木结构的视觉呈现,生死之间的中间状态通过两种建筑类型的“杂交”而得以实现。
▲ 河北宣化张文藻墓棺室打开时内景
此墓墓室坐落在十一级台阶组成的陡峭墓道尽头,位于地下4.3米处,模拟了一座微缩的房子。参观者惊讶地发现这座著名的墓葬竟是如此窄小:穹顶的前室直径不足3米,垂直的墙壁仅有一米多高,几乎达不到成年人的胸部。棺床置于后室后壁的一扇假门之前,假门的门扇高度不足60厘米。
我们不能把这种缩小的体积归结为出资者的节俭。实际的情况是:张氏家族在设计和建造这一地下微缩建筑时遵循了中国丧葬建筑的一个既定传统。中国历史中唯有秦始皇定制了原大的俑人,汉代统治者旋即回到了微缩的传统。宋代理学家进一步明确声称,明器应该是“象平生而小”。在建筑方面,尽管高级墓葬往往被称为“地下宫殿”,很多装饰奢华的墓葬实际上故意做得很小。要真正认识它们的尺寸,人们必须亲自访问原址。例如,位于山东沂南的一座著名的东汉“地下宫殿”实际上非常低矮,其中的一个仿制茅坑只有实物的三分之一大小——墓主的死后灵魂想必是大大地“缩水”。张文藻夫妇的墓葬说明这种转化可以通过特殊的丧葬仪式获得:尽管张文藻的墓志将其描述为“状貌魁伟……力敌二三夫”,夫妇二人位于陀罗尼棺中的“复原的身体”只有90厘米和80厘米。
▲ 河北宣化张文藻墓棺室后壁假门
这座地下墓室不仅是一个微缩建筑,而且是一个“反转”的建筑。在建造过程中,工人在地上挖一深坑、在坑中建筑墓室之后再以泥土掩埋,只留出大门的正立面。他们随后把室内的所有墙壁覆以白灰泥,在上面画出建筑细节和壁画。这一装饰过程把墓室内表转化为外表和外部空间:彩绘的仿木结构模仿着地上建筑的外部特征;壁画描绘了仙鹤在竹林中漫步;后室顶上是蓝色天穹,上面散布着日月星辰。这些特征使得梁庄爱论(Ellen Johnston Laing) 以及其他学者声称,墓室壁画表现的实际上是一个象征性的庭院。但这可能只是说对了一半——如李清泉注意到的,墓内壁画也图绘了家居内景和室内活动。供祭的饮食还把棺室转化为一所祭堂。其他的因素又把墓室与禅房以及超验的仙境联系起来。
▲ 河北宣化张文藻墓视幻建筑装饰
在李清泉、沈雪曼、梁庄爱论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此墓作一个综合性阅读。概括地说,这座地下建筑以棺室为轴心,由三个真实的和暗示的空间所构成。空无一物的前室是连接墓室和生人世界的过渡区域。在较为简单的墓葬中这个区域可以省略,如我们在宣化墓地中的张恭诱墓和张世本墓中所见。在带有前室的墓葬中,这个空间被一扇厚厚的墓门与后室隔开,显示出两个空间的非连续性。一些墓在前室墙上画着空鞍之马——我们知道这是象征死者身后之旅的传统形象。在其他属于此类的墓中,如张文藻墓,前室壁画描绘了乐舞和备茶场面。鞍马题材明显延续了在墓道中描绘仪式队列的传统。至于第二个题材,有的学者认为由于饮茶可以净化人体,它成了中古时期宗教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除了这两种常见的绘画场景以外,绘于张文藻墓门上方的一幅独立画面描绘了五个小鬼,手中拿着各种器具。考古报告认为这些形象表现的是墓葬的保护者,但没有为这一论点提供任何证据。另一种可能是:这一画面把墓门定义为地下世界的进口。如我们即将看到,后室墓门上方对应位置上的绘画表示的是仙境的入口。
▲ 河北宣化张文藻墓前室壁画备茶图
如果前室界定了棺室前端的起点,那么一系列隐含空间则界定了棺室另一端的边界。这种空间之所以是“隐含”的,乃是因为它们并非以三维建筑形式表现,而是通过绘于墙上的假门和假窗来加以暗示。早在东周时期,人们已经在棺上画上门窗以方便灵魂的运动。一些东汉壁画墓进一步描绘了墓室的“窗外”场景。这种对视幻性建筑装饰的兴趣在宋、辽、金时期臻于极致,反映在这一时期墓葬中反复出现的假门和假窗上。
张文藻的棺室有三门一窗,其中只有南壁上的门(即连接此室与前室的门)是真的。与此门相对的是前文提到的那座微缩门。它半掩于棺床之后,其半立体的砖雕形式和华丽的人字形山墙把它与西壁上的一座假门区别开来。西壁上的这个门是绘制的,不是雕刻的;是二维的,不是三维的。一个或为侍女的年轻女子手持一把锁,似乎正在把这个门锁上。旁边的另一个侍女正在给灯添油。如同我们在此墓的其他地方见到的,这第二个形象是将实物与二维、三维形式结合所创造的一个视幻图像:女子和红色的火苗以绘画表现;高大的灯座是浅砖雕,突出的灯台上则原来托有一盏真实的灯。对面东壁上绘有一方桌子,桌上陈列着笔、砚和空白纸张,上方是棂窗。
▲ 河北宣化张文藻墓棺室西壁装饰
学者们一直在考虑宋、辽、金墓中的这些假门和假窗的意义。大部分的解释仍然是推测性的,但是李清泉最近的一个阐释使我们认识到一部分假门可能属于与表现时间有关的一个图像程序。简言之,他认为门的开闭——这种场面多出现在宣化辽墓东西两壁上——表示的是早晨和傍晚这两个时刻。比如说在张世卿墓中,一个侍者正穿越东墙上的门进入后室;而另一侍者正要跨过西门离开这个房间。其他图像进一步强化了这两扇门的时间性意义。如在一些墓中,东门(或东窗)附近的画面描绘了侍女正手持梳洗用具,侍奉着(无形的)墓主早起梳洗更衣。在相邻的一张桌子上,文房四宝已经准备就绪,暗示着墓主抄经的日课即将开始。西壁上的门(或窗)附近——如前文所述——一个侍女正在点灯,而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堆放着抄完的经卷。壁画的一个细节更锁定了这种时间意义:两组表现晨、暮的壁画正好和室顶上东西相向的日月对应。
这一解读丰富了我们对棺室作为时空统一体的理解。正如我们在很多其他例子中见到的,这一空间通过融合不同的功能和界域而实现了它的象征性。这些功能之一是向死者进献供品,主要是酒食。因此这个空间的一种意义是一个地下的祭堂。与空荡荡的前室形成鲜明对照,棺室中的随葬器物多达96件;棺前桌上的22种瓷器更盛放有水果、干果和烹调好的菜肴。与这些制作细腻的供器形成对比,置于棺木两侧地面上的是质地粗糙的陶明器和一个微缩陶仓,构成了一组专门为死者准备的“鬼器”。
▲ 河北宣化张世卿墓棺室壁画:东壁(左)、西壁(右)
也正如在其他墓中见到的那样,死者被想象为“生活于”此处。这一想象在宣化辽墓中通过两种不同方式实现,一是在东西壁上饰以晨启暮闭的假门,二是在两壁前放置两组日常生活的家具和器物,其中包括几把椅子、一张放有餐具的桌子、若干铜镜、一件三彩釉脸盆、一件木衣架以及镜架和脸盆架。有意思的是类似器物也见于墓室壁画之中,沈雪曼据此提出一个理论,认为在一些宣化辽墓中,壁画形象和随葬实物有意识地呼应和互动。在我看来,这种呼应和互动所见证的仍然是缔造生与死、真与幻之间的时空隐喻的愿望。
宣化辽墓中的很多因素可以溯源到满城汉墓和马王堆汉墓。但是在张文藻墓中,已故夫妇的灵魂不再用空座象征,他们的身体也不再被转化为不朽的玉体,而是以装殓在陀罗尼棺中的两个盛有骨灰的稻草人来表现。作为虔诚的佛教徒,这对夫妇相信火化将最终消除他们对红尘的执着,陀罗尼棺将进一步庇佑“其影映身”的芸芸众生。他们因此从佛教礼仪获得新的方法使自己不朽——我们也不难发现稻草人和汉代玉体在“转化”这个概念上的相通。在更深层的意义上,通过把佛教(和其他外来)元素融入墓葬艺术,张氏夫妇得以把“多中心”的墓葬设计发展到一个更新的层面。事实上,有足够证据表明在设计这些墓葬时,出资者和建造者有意识地吸收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传统。正如以前的作者们所注意到的,宣化辽墓中的壁画把佛经和道经一起描绘为礼拜对象;墓志铭也强调死者在世时不但修行这两种宗教,而且还秉承了儒家的忠孝原则。墓中图像的多种来源进一步提供了文化融混的证据:这些装饰图像——包括佛教的莲花、道教的云鹤和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明显来自不同的文化和艺术传统。
▲ 河北宣化张文藻墓后室门上壁画
张文藻棺室入口上方的半圆形画面自觉地表现了这种兼容并包的倾向。图中描绘了三个人物,正聚精会神地卷入了一场棋赛。从图像学的角度看,这一构图融合了两种传统的图像主题:一种是下棋的仙人或道教隐士,另一种描绘了儒释道的“三教合一”。第一个主题早在汉代墓葬艺术中就已获得相当的流行,被刻画在石棺上或墓室中以象征死者希望进入的超验世界。“三教”图像或许出现于唐代,当儒释道的融合开始主导社会精英们的思想倾向并渗入他们的哲学思辨和政治修辞。无独有偶的是,传统绘画著录记载唐宋画家创造了多幅题为“三教”或“三教图”的作品。李清泉曾把张文藻墓中的画面与这一文献信息联系,确认绘画中的三个人物从右到左为僧人、儒生和道士。值得注意的是这幅画在墓中的位置显示出它在丧葬语境中的特殊含义:画在棺室入口上方,它的目的并不在于宣扬某种政治哲学或意识形态,而是宣告“三教合一”是通往不朽的道路。
▲ 四川东汉画像石棺仙人六博图,公元2世纪
这个例子也回答了贯穿本书的一个潜在问题。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墓葬艺术在传统中国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几千年而不绝?在古代日本,建造大型室墓的本土传统在佛教传入之后就基本上消失了。但是在中国,佛教艺术的引进并没有阻碍墓葬艺术的发展,而是导致了两个并行不悖的传统。甚至当一些皇帝以佛教或道教为国教之后,他们也并没有丧失为自己建立豪华陵墓的热情。我以为,正如张文藻墓中的“三教图”所示,墓葬艺术千年不衰的一个原因在于它吸纳不同信仰和实践以丰富自身的能力。受到绵绵不绝的祖先崇拜和孝道的支持,它在中国古人的社会活动和艺术创造中保持了一个核心位置,在黄泉世界造就了变化无穷的建筑结构、图像程序和器物陈设。这一传统甚至在中国进入20世纪之后也没有完全消失,而是继续影响着现代中国的礼制建筑和视觉文化:南京巍峨的中山陵中埋葬着现代中国之父孙中山,天安门广场上壮观的毛主席纪念堂则象征着新中国奠基人留给历史的遗产。

*文章节选自《黄泉下的美术》(三联书店 2016年1月刊行)“尾声:写照中国墓葬”。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
巫鸿作品精装(五种)
《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
《时空中的美术:巫鸿古代美术史文编二集》
《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
《美术史十议》
《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
巫鸿(Wu Hung)早年任职于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硕士。1987年获哈佛大学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博士学位,后在该系任教,1994年获终身教授职位。同年受聘主持芝加哥大学亚洲艺术的教学、研究项目,执“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2002年建立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现当代艺术的研究与交流,并撰写和编辑有关专著。所培养的学生现多在美国各知名学府执中国美术史教席。
此次三联书店出版的“巫鸿作品精装五种”以统一的形式呈现作品之间的关联与架构:《礼仪中的美术》、《时空中的美术》、《黄泉下的美术》三本论文集,提炼了巫鸿理解和阐释中国古代艺术之独特性的三个重要维度和概念;《美术史十议》提供了美术史学研究发展变化的背景;《武梁祠》则是对中国早期美术做出深入解读的范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