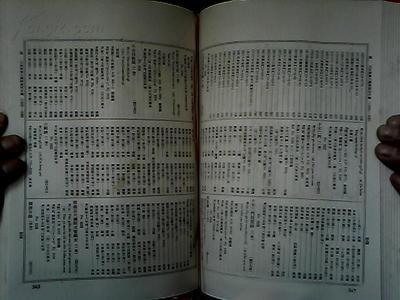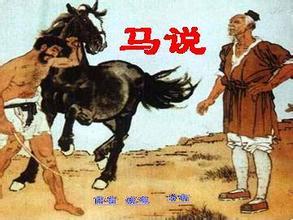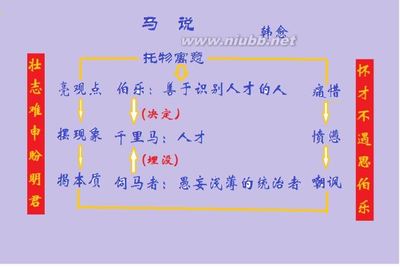《趣说汉字》
“犇”“麤”搞拧了 ?
“犇”,意为牛惊。《集韵》曰:“奔古作犇。”
“麤”,从三鹿,音粗。《说文》曰:“行超远也。”段玉裁注:“鹿善惊跃,故从三鹿。引伸之为鹵莽之称,今人概用粗,粗行而麤废矣。《字统》云:(麤)警防也。鹿之性,相背而食,虑人兽之害也。”
苏轼对“品形字”颇有研究。但他性情恢谐,常常借用“品形字”逗乐。据传,苏轼曾对王安石说:“‘犇’‘麤’二字搞拧了”,竟弄得王安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王安石一生有个嗜好,爱琢磨汉字的“字源”,凭主观臆断,胡乱评说造字的缘由,竟然写下了《字说》二十五卷。苏轼对王安石这种“望文生义”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多次当面予以嘲讽。如,王安石曾以丰富的想象力解释:“波”者,“水”之“皮”也。苏轼调侃说:“‘波’若是‘水’的‘皮’,那想必‘滑’就是‘水’的‘骨’了。”直弄得“拗相公”啼笑皆非,无法应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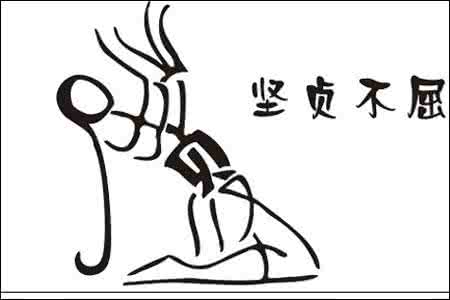
有一次,苏与王闲谈时,苏突然发问,“鸠”字为什么是“九”与“鸟”组合而成?王一时语塞,苏随即引经据典地说:“诗经上有:‘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两个老鸟,不是九个鸟吗?”
那么,“‘犇’、‘麤’二字搞拧了”,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天,苏轼恭恭敬敬地向王安石请教:“学生对‘犇’‘麤’二字,百思不得其解。牛比鹿体壮,鹿比牛敏捷,为什么三个‘牛’合成的字和三个‘鹿’合成的字,竟然意思全反了呢?”
王安石极其认真地思考起来:是啊,牛没有鹿动作敏捷,“犇”却读作 “奔”,意思倒成了奔跑快速;鹿没有牛健壮,“麤”字不仅读音是“粗”,而且意思也是粗暴,怎会这样的呢?王安石冥思苦想了许久,也没想出个所以,这时他的“字源说”压根儿用不上了,这是何等尴尬呀!
2010-09-17作 2015-6-12修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