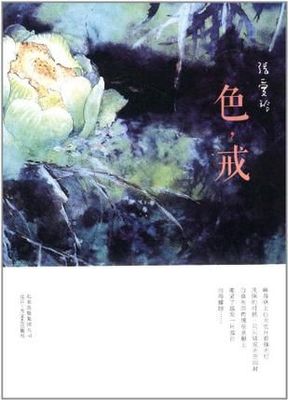<?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雷峰塔》、《易经》与“回旋”和“衍生”的美学
张爱玲研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显学。近年随着旧作不断出土,张的文名与时俱进,各种相关著作也层出不穷。但其中有一个面向仍然没有得到充分探讨:那就是张爱玲一生不断重写、删改旧作的倾向。我以为她的写作其实是以一种“否定的辩证”方式体现历史的复杂性,也为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察,提出发人深省的观点。
张爱玲研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显学。近年随着旧作不断出土,张的文名与时俱进,各种相关著作也层出不穷。但其中有一个面向仍然没有得到充分探讨:那就是张爱玲一生不断重写、删改旧作的倾向。她跨越不同文类,兼用中英双语,就特定的题材再三琢磨,几乎到了乐此不疲的地步。因此所呈现出一种重复、回旋、衍生的冲动,形成张爱玲创作的最大特色之一。
2009年,张爱玲的两部英文小说《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和《易经》(The Book of Change)重被发现,经过整理,于2010年问世。这两部小说皆写于张爱玲初抵美国的50年代中后期。两部小说都有浓郁自传色彩,也为张爱玲反复改写与双语书写之美学提供了最佳范例。张爱玲对自己生命故事的呈现无时或已;从散文到小说到图像、从自传式的喁喁私语到戏剧化的昭告天下、从中文到英文都多所尝试。正是在这两部新发现的英文小说中,我们得以一窥她种种书写(和重写)间的关联。
20世纪文学的典范以革命和启蒙是尚。严守这一典范的作家和批评家自然不会认同张爱玲的创作意念和实践。但我以为她的写作其实是以一种“否定的辩证”方式体现历史的复杂面,也为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察,提出发人深醒的观点。
(一)
1938年,上海的英文报纸Shanghai Evening Post(《大美晚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十八岁的中国女孩,名叫Eileen Chang(张爱玲)。在这篇文章中,张爱玲描述自己在一个衰败的贵族之家成长的点滴,她与父亲和继母的紧张关系,以及曾被父亲禁闭在家中一个空屋里的经历。其间她患了伤寒,因为没有及时用药而几乎送命,最后她在奶妈的帮助下得以逃脱。
这篇文章是张爱玲初试啼声之作,也预告了20世纪中国天才女作家的登场。历史的后见之明告诉我们,张爱玲未来写作生涯中挥之不去的主题已然在此出现:颓靡的家族关系、充满创伤的童年记忆以及对艳异风格的迷恋等。这篇英文文章同时也预示张爱玲穿梭于双语之间的写作习惯。“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发表六年以后有了中文版本《私语》(1944)。同一时期的其它中文文章如《童言无忌》也有所印证。到了1950年代后期,这些文字统统化为了她的英文小说《易经》的素材。
《雷峰塔》原是《易经》的第一部分,后来却被张爱玲取出独立成书。在撰写英文《易经》的过程中,张已经开始构思写作它的中文版。这便是张1976年大致完成、却积延不发的《小团圆》。此书迟至2009年方才出版。
从散文到小说、从自传性的“流言”到戏剧化的告白,穿梭于中英文之间的张爱玲几乎用整个一生反复讲述“What a Life!”的故事。但就她重复书写与双语书写的美学而言,这远非唯一例证。从《十八春》(1950)到《半生缘》(1968),从英文的“Stale Mates: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1956)到中文的《五四遗事》(1958),都是如此。我已在别处讨论过张爱玲的英文小说The Rouge of the North(1967)的多个分身:1943年张创作了中篇小说《金锁记》,50年代将其翻译为英文,并在1956年扩充为长篇小说Pink Tears。Pink Tears经过60年代的多次重写,最后以The Rouge of the North 的面貌问世。同时,她又将The Rouge of the North题为《怨女》,译回了中文。就这样,在二十四年的时间里,张爱玲用两种语言至少写了六遍《金锁记》。
对于张爱玲来说,重写既是袪魅的仪式,也是难以摆脱的诅咒。尽管写实/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形式,张爱玲穿越修辞、文类以及语言界限的重复书写却孕育出一种特殊的创作观。她的写作不求“重现”而只是“揣摩”过往经验;它深入记忆的洞穴,每下一层甬道,就投下不一样的光亮。更重要的是,通过写作,记忆转化为技艺:藉由回忆,过往的吉光片羽有了重组的可能,并浮现种种耐人寻味的形式。书写与重写是探索性的艺术。追忆似水年华并非只是宣泄和耽溺,新的、创造性的欢愉(和痛苦)也随之而生。
以《雷峰塔》的标题为例,张爱玲在她给宋淇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塔”指的就是《白蛇传》里“永镇白娘子”的雷峰塔。张在此援引一个具有鲜明的异国情调的传说,也许是为了迎合英语世界的读者。除此,对雷峰塔的指涉也为张爱玲自己那段遭到禁锢和侥幸逃脱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有神话意味的潜文本。
更意味深长的是,“雷峰塔”把我们带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互文世界。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大概就是鲁迅著名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国新文学中至少还有三个文本以塔为象征∶殷夫的诗歌《孩儿塔》;白薇的剧本《打出幽灵塔》;台静农的小说集《建塔者》。在这样的阅读脉络里,我们要说现代中国文学里以“塔”形成的“感觉结构”其来有自,张爱玲的《雷峰塔》只是一个迟到的版本。然而对于雷峰塔的倒塌,张爱玲毕竟别有感悟。鲁迅、白薇和殷夫等人都是革命阵营的作家。他们有多期待推倒代表封建中国的雷峰塔,就有多期待看到一座新的、现代巨塔在原地建起。这座现代之塔可以名为革命、政党、或民族国家。准此,他们也是建塔者。
张爱玲则不在建塔者之列。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者和极端的讽世者,她对一切以崇高为名的主张和架构永远充满怀疑。如果“雷峰塔的倒掉”在中国文化的想象图景中代表一个天启般的瞬间,那么对于张爱玲来说,这天启的意义就在于塔的倾颓,而非任何重建的可能。在雷峰塔倒掉以后写作,意味着反省原初建塔的虚妄和野心,观察游荡在断壁残垣间的幽灵,或更诡异的,“欢迎”那阴森幽密的氛围从此笼罩中国大地。
张爱玲的《雷峰塔》中投射出一种内倾性的回旋话语。与革命话语不同,“回旋”的展开并不依靠新的元素的注入或运作,而是通过对思想、欲望和行为的现存模式的深化、重复、扭曲来展现前所未见的意义。它就这样盘旋着,卷向自身内部。这样的倾向可以视为保守甚至颓废。但张爱玲未尝不以此提供了一个警醒的视角,让我们一窥历史上每一座人造的巨塔之下,都潜伏着幽灵——白蛇也似的幽灵?
而在1950年代,又有什么能比新中国的成立所投射的象征巨塔更雄伟,更崇高?张爱玲却选择在这个时候永远地离开祖国。她从任何奉民族、国家之名的建构抽离,退居到自己所发掘的记忆洞穴中。在那潮湿阴暗的所在,她默默探究中国——社会,文明,人性——最曲折扭曲的面向。她回到那“荒唐的,古代的世界”,反而揭露了“阴暗而明亮”的现实。五十年代后期,张爱玲以最离经叛道的方式为中国招魂,也同时为中国祛魅。她写的不是奉任何名义的塔的高高崛起,而是塔的倒掉。
(二)
张爱玲从未以通晓《易经》著称。她将小说命名为《易经》,不免使人好奇她的动机何在。她也许是想借重这部经典的“东方”魅力来吸引西方读者,也许真是希望求助古代的智慧来参详琵琶或她自己的命运,又也许是对前夫胡兰成微妙的反戈一击——胡兰成自战时起就以《易经》的阐释者和实践者而洋洋自得。撇开这种种可能,我认为,奉《易经》之名,张爱玲不仅在“东方主义”与个人命运之间多所玩味,更力图从中汲取一种创作哲学:小说创作不正如《易经》,以其多变的“象”诉说着人生种种起落无常?
《易经》的“易”字在中文里意涵丰富,它可以指“变易”,同时也可以指“不易”,又有“简易”、“交易”、和“交换”的含义,张爱玲以此来表达自己复杂的战争经验,用心不难理解。虽然小说《易经》主要是描述香港沦陷和女主人公回到上海的历险,但张爱玲写作此书时已经是50年代后期。回顾将近二十年以前的经验,她其实是有着历史的后见之明的,也必然明白回忆性的写作在操作已经发生的和尚未发生的事件上,所产生的时间和知识的多重落差。1950年代末在美国写作《易经》时期的张爱玲已是一个两度结婚,移民他乡,依靠非母语写作的中年作家了。回望1938年初入文坛以来的种种遭遇,她有理由为自己所经历的变化唏嘘不已,从而理解“易”的意义所在。
在更深的层面上,《易经》这一标题指出生命流变和人世兴衰中的种种悖论:生老病死、花开花落既然已是恒常的定数,“易”也就成为千古“不易”的道理。貌似相反的两种力量互为印证,轮回辩证的模式才得以生出,而恰恰是这些展示出了“易”之道。这个“道”虽然难以言诠,传达的却是直指本然的真理,是简单的、“容易”的易道。
相应地,时间也不只意味着线性发展,而是一种“空间的流转”,在其中变与不变、交相变化与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结构。这就带出了“易”的第三层含义:作为一种打破现状的力量,“易”总蕴含着无休无止的变化——也是生发的——动力,是为“生生之谓易”。“易”构成了开启生命宇宙论的基本法则。只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才能理解张爱玲有关重复书写所暗含的哲思。重复既不是对现有事物的乏味的复制,也不是回归事物的原点。重复是“生生”的过程,是脱胎自现存事物而又对其作出反应,也是原点的微妙位移,由此“易”的力量相应而起。
在关于《雷峰塔》的讨论中,我提出张爱玲写作的“回旋”美学。这种叙事实践一反线性、前进的序列,代之以反转内敛的倾向。我认为在《易经》中,张爱玲不仅将回旋的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更展开一种衍生的美学。所谓衍生,指的是叙述的动力并不在于(浪漫主义定义下的)原创性,而在于一种赓续接踵的能量,或是修辞意义上的代换与变形,从而颠覆一般对于“真实”、“发生”、“缘起”的诉求。
就此而言,《易经》既是张爱玲早期《烬余录》的再造,也是未来《小团圆》的预演。而《易经》本身也有它自己衍易与分合的过程。现在独立出版的《雷峰塔》原来就是从《易经》一分为二、衍生出去的。
张爱玲写作中回旋、衍生的倾向至少还有两个重要的例证可以参照。众所周知,张爱玲心仪晚清作者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海上花列传》当时并不受欢迎,但张爱玲却对它情有独钟,因为它颠覆了狎邪小说的传统。用日常琐屑来装点、填充(家族)历史,并在一切人生华丽的表象下看到那彻骨的荒凉,在这方面《雷峰塔》和《易经》的写作都追随《海上花列传》所留下来的印记。
《海上花列传》本身的结构与风格特征也有所本,那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也是张爱玲灵感的源头。张爱玲八岁第一次读《红楼梦》,1934她甚至尝试创作现代版的《摩登红楼梦》。《红楼梦》之所以打动张爱玲,想来是因为她从中看出了同样家族盛极必衰的命运,更不必说青春与伤逝的色彩,以及繁华苍凉总成一梦的启悟。

更引起我们关注的事实是:随着年岁渐长,张爱玲越来越理解曹雪芹终其一生不断修订——重写——手稿的苦乐。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最终仍未能完成这项大工程。《红楼梦》随着作者个人际遇的变化而不断改换面目,死而后已。而张爱玲晚期书写不正演示了类似命运?
我认为张爱玲在她写作生涯的后四十年里一再重写自己的生命故事并非巧合。在写《易经》、《小团圆》的同时,她也从事了两项平行计划。她将吴语版的《海上花》翻译成国语,又从国语翻译成英文。另一方面,她孜孜不倦地细读《红楼梦》,文本分析、文献考据、传记研究三路并进。她的红学考证后来以《红楼梦魇》(1977)为名结集出版。
对张爱玲而言,这三个书写计划——创作、注释、翻译——密不可分,更确切地说,它们构成了一个文本互涉、跨文类、多重语言的网络,这一网络正指向张爱玲衍生美学的多个层面。
张爱玲在《海上花》国语翻译的后记里回顾自己所下的工夫,不无反讽地写下:张爱玲五详《红楼梦》,看官们三弃《海上花》。
这不仅是张爱玲对两部古典小说杰作的命运有感而发,也是对她个人阅读与写作的心得总结。正如小说标题所暗示的,《易经》体现了张一生的写作随着生命发展不断变化,辗转曲折,死而后已。每一次尝试都显示她面对早年经历的不同态度,以及不断更新的叙述策略。就这点而论,张爱玲不啻是在书写她自己的《追忆似水年华》。以此她证明“往事”并非是冰封在时间彼端的静态事物,任我们予取予求,而是记忆中的活跃成分,时刻与创作者的当下此时互动。
传统观点认为张爱玲在1952年离开大陆后,创作力急遽下降。如果我们根据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有关“原创”、“创新”、“突破”等定义来看待“创作力”的话,这样的结论并不为过。但《雷峰塔》、《易经》这类作品的出土,促使我们从不同角度思考张爱玲的创作立场。当中国的大部分作家回应着“五四”所标榜的现代性召唤,孜孜不倦地弃旧迎新,并期待着“史无前例”创举时,张爱玲选择回望那些被进步作家和批评家们视为颓废、反动、私人的题材和形式。也由此,她示范出一个“回旋”而非“革命”、“衍生”而非“揭示”的书写谱系。我们一直要等到另一个新世纪来临后才理解,张爱玲的许多同辈作家所信仰的“现代”可能未必那么现代,而张爱玲所坚持“传统”其实一点也不传统。王德威
(此内容为作者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有删节。原文为英文稿,由复旦大学<?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王宇平博士译为中文。《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六期刊发全文)
2009年,张爱玲的两部英文小说《雷峰塔》和《易经》重被发现,经过整理,两部作品的英文版与繁体中文版于去年问世,简体中文版也即将于今年推出。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学者王德威日前在题为《雷峰塔下的张爱玲》的演讲中指出,虽然张爱玲研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显学,但其中有一个面向仍然没有得到充分探讨:那就是张爱玲一生不断重写、删改旧作的倾向。他认为,张爱玲的写作其实是以一种“否定的辩证”方式体现历史的复杂性,也为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察,提出发人深省的观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