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马》剧照
经公众号且听沧老师说(微信号:canglangyun2000)授权转载。
同治九年(1870年)8月22日,上午十点左右,南京城督署府衙西侧校场外,两江总督马新贻刚刚循例检阅将士操练完毕。据当天身处金陵的士人张文虎所记,昨日细雨绵绵,故今日放晴且不闷热。天气晴爽,自然观者如堵。行经箭道时,忽一人从百姓中冲出“拦前喊冤”,马“方接状,一人自后至刺刃,亲兵急救不及”。马肋部要害被刺,“已不能言,气息如丝,刃处无血而口中反流血”。大夫束手无策,马遂于次日不治而亡。刺客当场捕获,名叫张汶祥。此事件即轰动晚清朝野的“刺马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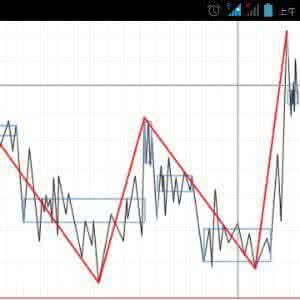
堂堂朝廷一品大员、封疆重吏,居然于光天化日之下遇刺殒命,不啻如晴空惊雷一般,令百官惊愕,使中枢震怒。本来尚关注津案的千百双目光瞬间聚焦于该突发事件上来!
马氏之死,对于位居近似官职的督抚而言,好比闷棍打在别人身上,却疼在自己心头,颇有戚戚之感。仍处津案泥潭中的曾国藩,听闻噩耗后的第一反应为“曷胜骇愕”:
马帅中正和平,得之天性。莅任以来,一切用人行政,无一不允惬众望,似不致招人仇怨。忽尔罹此奇祸,殊出意料之外。怀贤念旧,感喟良深。
与恩师相同,甫至天津上任的李鸿章得知进士同年死于非命,亦慨叹“骇痛殊深”。时任浙江巡抚的杨昌濬更是称“毂帅之事真是天外飞来”!
疆吏愕然,京官也皆表惊惧。如翁同龢认为刺马案实在是“三百年未有之奇事也,嘻,衰征矣!”
翁同龢
重臣遇害已令人恼火万分,加之官场中负面情绪渐趋蔓延,清廷颇觉外患未靖,内忧纷至,自然极为震怒。两宫表示“不胜骇异”,“凶犯张汶详,胆敢伺隙行刺,戕杀总督重臣,实属罪大恶极。必应研讯确情,从严惩办,以申国法”。于是谕令江宁将军魁玉“督饬司道各官设法熬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情事,一一审出,据实奏闻”。数日后,清廷又著派漕运总督张之万会同魁玉查案,“务将其中情节,确切研讯,奏明办理,不得稍有含混”。
按理说,如此“高配置”阵容办案,自当很快水落石出。孰料魁、张二人审讯足足数月,竟因“供词尚属支离,自系因一时未得实供”,迟迟不能结案。后经中枢严斥,二人终于勉强拿出一个难以服众的结论:
对此案情汇报,两宫绝对无法满意,认定其间“尚有不实不尽”之处。一句“尚属可信”,如何瞒得过南北众人之目,塞得住天下悠悠之口?倘以此结案,“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谳”。
既然这一届主审官不行,那索性换一拨。于是两宫命调往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于抵任后会同严讯,务得实情。著再派郑敦谨驰驿前往江宁”审理。
曾国藩
前脚刚从津案漩涡迈出,后脚又被清廷推入刺马迷局当中,曾国藩叫苦不迭,愁断了肠。其实对于两江总督一位,曾氏本就无丝毫贪恋。当收到朝廷调令时,曾函告儿子曾纪泽“余目疾不能服官,太后及枢廷皆早知之,不知何以复有此调?”“趁此尽可隐退,何必再到江南画蛇添足”。然曾上书请辞,迅即被中枢驳回,只得待津案完结后赴任。
曾氏心中的如意算盘,当是先在天津、京城延宕时日,等刺马案尘埃落定,再徐徐南下,走马上任,尽量避开此等是非麻烦。谁知魁、张审案不力,清廷便促其尽早起程。离京前夕,曾氏两度面圣。一次是10月20日,慈禧先与曾略谈津案情形,突然话锋一转,问道:“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曾对曰:“这事很奇。”慈禧又道:“马新贻办事很好。”曾答:“他办事和平、精细”。后曾旋即退出殿门。慈禧与曾国藩此番对话,看似稀松平常,虽双方都认为刺马一案“甚奇”,但彼此心中的“甚奇之处”恐大相径庭。
慈禧之“甚奇”在于,清廷费尽气力扶植以掣肘湘淮势力的心腹马新贻怎会突遭不测?
马新贻,字毂山,号燕门,别号铁舫,谥号端敏,山东菏泽人,进士出身。自27岁分发安徽太和知县,二十年间一路升迁,先后出任安徽按察使、布政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等职。47岁那年,马接替曾国藩,执掌两江。由其履历可知,马氏任职之地,包括皖、浙、闽、苏、赣五省,此乃太平军、捻军肆虐之处,亦是湘淮军之主战场。马以一介书生,能够于战乱中少受贬黜,屹立不倒,背后自有清廷力挺。故深谙内情的王闿运一语点出玄机:
他与官文、吴棠诸督抚一样,是中枢用来节制湘淮的锁链。荣膺此位,马氏亦不辱使命,在裁撤湘军、镇压淮军索饷等问题上不遗余力。如他曾上《留存水路防军数目及现在布置情形折》,认为“浙省湘楚两军,马步水陆共计二万七千余人”,“经臣挑留水陆五千余人,合之现升藩司杨昌濬所部楚军,共计一万四千余人”。大笔一挥,27000名湘军被裁掉一半。因而在不少湘淮大佬眼中,马新贻堪称惹不起、招人烦的狠角色。恰恰是与湘淮势力针锋相对的作用,马氏猝亡不禁令两宫深疑此背后或有湘淮军头目主使,作为执牛耳者,曾国藩是否参与其中?
曾国藩之“甚奇”在于,湘淮军虽向来对马新贻打压异己的做法不甚苟同且颇为忌惮,但尚不致采用如此极端手段解决之。况且此招亦非湘淮对付政敌的惯用手法。曾、左、胡、李诸辈,对于政敌,一般要么私下贿赂,从而与之结好;要么上折抵制或弹劾,令其无法在势力范围内久待。而此案迥乎寻常,若真牵涉湘淮嫡系,曾该如何处理?显然帝后对自己已起疑心,那为何又命之去主审?
依照君臣双方皆十分矛盾的心理,仔细揣摩,便能探知:
李鸿章也在此时致信恩师,猜透了清廷的这种考虑:“毂山近事奇绝,亦向来所无。两江理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然而既非曾氏莫属,也就意味着若此案主谋乃曾国藩,那么清廷便不可能追查到实情。这也意味着不及曾国藩南下,最高层已变相地赦免了其“弥天大罪”。而对曾国藩来说,帝后命他执法,虽说可保己身免于不测,但一旦查出背后元凶与湘淮有关,该如何处理真是极其棘手。
质言之,清廷不满初审结果,于是向曾国藩施压,令其破案,既欲探其虚实,又确属无奈之举;曾国藩本不愿陷入此案,其间的是非纠缠丝毫不输于津案,然上意难违,故他心中满是无奈之情。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于此昭然若揭。
曾国藩书法
11月1日,曾国藩再度面圣,颇为案件着急的慈禧问曾:“几时起程赴江南?”曾对曰:“臣明日进内随班行礼,礼毕后两日即起程前赴江南。”慈禧再次催促道:“江南的事要紧,望你早些儿去。”
七日后,在京滞留许久的曾国藩总算出发。本该为重臣洗冤的行动,已暗暗定下了中枢与地方角力博弈的基调。
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曾国藩终于12月3日抵达金陵。掌印后,曾国藩终日走访新朋旧雨,却不急于审案。因为他在等待另一位主审官——郑敦谨。
郑敦谨,字小山,湖南长沙人,时任刑部尚书,向以治事严苛著称。此番朝廷委此重任,自有望其一查究竟之意。曾氏心知肚明,断不敢在湖南老乡驾临前贸然独立审理。1871年2月6日夜里,曾“将张汶祥之案细阅一过,将凶党余犯及承审之名开一清单”。直到二更四点,曾氏方才入睡,且内心“殊为焦虑”。他知道,这种焦虑不单单属于自己,恐怕明日抵达的郑敦谨亦是如此。
果不其然,下车伊始,郑便着手调查,正月初二即审理张汶祥。虽然白加黑、连轴转,案件却进展甚微,“初二日即关门审案,今已研讯十四日。该犯一味狡展,毫无确供,将来只好仍照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于是二人只得在量刑上做文章,加重罪名,将张汶祥“比照谋反叛逆”处理。
不成想这一拨主审官也不行,清廷也只得买账,“既据郑敦谨等审讯确实。验明凶器,亦无药毒,并无另有主使之人。著即将张汶详凌迟处死,并于马新贻柩前摘心致祭,以彰国法而慰忠魂”。可以说,最终裁决的结果达成了皇权与官僚集团间的妥协。清廷试图通过重审对曾国藩施加压力,以期尽可能触及真相,而曾国藩甚或郑敦谨却借助既有律法、条例及情理消解了上峰的意志。钱穆先生曾言:“现代的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于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实指王法森严,规则重重,束缚之余,也为官僚集团提供很大的发挥空间,成为抵抗皇权的依据。
《刺马》剧照
案情办到这里,已是接近尾声,张汶祥终究被定性为无后台主使、无固定职业、有私人怨恨、有犯罪前科的社会游民。曾国藩事后致函郑敦谨赞道:“大旆南来,折衷至当,实足全息浮议,以清望素为人所敬也。”事情真如曾氏所言,疑云全消吗?
种种迹象表明不是。
其次,在写给其它同僚的信中,曾国藩反复提及刺马案处理结果“尚恐不足惬众望而息浮言”。
再次,结案不久,曾暗自派手下张兆栋给郑敦谨送去赆仪(路费)白银千两。虽曾氏声称此“盖诸君之公意,非一人之私忱”,但郑坚决拒收。
当然最令人费解的是,数十年后的《清史稿》作者在为郑氏撰写盖棺之词时,特意留下“江宁之狱,论者多谓未尽得其情,敦谨未覆命,遽解官以去,其亦有所未慊於衷欤”一段,可谓暗藏玄机。
那么,曾国藩是否有所掩盖?郑敦谨究系存何隐衷?二人之微妙关系到底怎样?
其实倘仔细审读曾国藩关于刺马案的奏稿,即可发现其已略泄天机。在上呈两宫的结案陈词中,曾氏提到张汶祥的一段经历:
黄少春乃曾国藩手下将领,张投靠黄,意味着其进入湘军效力。而黄给张路费,将其遣散,则恐怕与曾国藩裁撤湘军的大背景有关。张汶祥沦为社会无业流民且走向谋刺政府大员之不归路,当一定程度上拜此所赐。这实已牵涉到平叛之后大量裁军所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
民国著名军事家蒋方震先生曾如此评价湘军:
蒋氏此言虽短,却精炼地梳理出湘军攻下金陵后分化的脉络:书生蜕变为官僚,此为上层;民兵演变成会匪,这是底层。
应当说,当年曾国藩裁撤湘军,确是大势所趋,一来历经十数年作战,军队已暮气沉沉、不可复用;二来为消弭清廷疑忌,从而“避权势、保令名”,曾亦须自剪羽翼、以示忠心;三来多数将士思乡情切、普遍厌战,命他们解甲归田顺乎人心。故自同治三年五月拿下天京,曾国藩递上《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决定将湘军裁撤始,至同治五年底,湘军先后被遣撤约30万人。如此数目巨大的退役军人,妥善安置便成为关键问题。倘处理不当,这批昔日拿过屠刀、杀人如麻的兵勇,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甚或政局的潜在因素。
曾国藩
曾国藩恰恰在该问题上鲜有良策。
其次,湘军营中盛行“拜盟”之风。早在编练湘勇之始,曾国藩就“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寄希望于练勇“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这实际上是鼓励练勇歃血盟誓,结拜兄弟。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审视,将士间彼此义结金兰,才能消除“趋向一致性”的心理压力,从而获得认同感、安全感。故“拜盟”之盛行,显然与湘军的组织结构息息相关。但这也助长了湘军内部的江湖气,并不利于军纪维护。
再次,湘军上层统领与基层士兵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左宗棠曾描述过军中士兵流传的一种说法:“诸将擢至总兵,则位尊金多,自为之念重。军中所以有‘顶红心黑’之谣也。”“顶红”,代指官阶高,“心黑”,比喻心肠毒。“顶红心黑”,就是说将领品级越高内心越坏,对士兵越是敲骨吸髓,横加盘剥。
总之,积欠巨饷、“义气”横行、将士不睦,兵勇们“不料一旦裁撤,置散投闲,既不得从事耕耘为农夫以没世,更不能略权子母与商贾逐什一之利;文墨非其所长,医卜非其所习;江湖落魄,年复一年,糊口无资,栖身无地,其流而为匪者,情也,亦势也”。诸多因素导致湘军将士裁撤后如同脱缰野马,很容易被地下秘密社会组织所吸纳。这便为哥老会的壮大提供了可乘之机。
哥老会组织
哥老会起源于“啯噜”。道咸年间,在青莲教、天地会、边钱会、江湖会的推动下,啯噜最终衍化为哥老会。同治时期,由于唆诱大批退伍湘军入伙,哥老会的发展堪称迅猛,该组织以四川、湖南最盛,湖北、江西次之,福建、广西、广东、江苏、浙江、安徽、山西、陕西、甘肃亦颇有势力,甚至部分成员已蔓延到直隶、新疆、台湾地区。哥老会触角所及,便暴动频仍。同治一朝,由哥老会发动的较大规模叛乱就达60多起。其中湖南最为严重。难怪湘军大佬们对此极为关注,左宗棠指出该组织“势之既成,遂若积重难返,黠桀者倡之,愚懦者附之,其患盖有不可胜言者”。赋闲在湘的刘蓉目睹哥老会肆虐,预感湖南必定要出现大乱,“要不出三数年间,不待智者而言矣”。屡次参与镇压哥老会的刘坤一更是慨叹:“前则为国剿贼,今竟自陷于贼,将来为人所剿,良可痛心!”
毫不夸张地说,作为后起之秀的哥老会,其规模和声势已凌驾于彼时活动不多、相对沉寂的天地会及斋教等秘密组织之上,成为同光年间势力最大、人数最多、活动最多、斗争最烈、活力最猛的一支秘密结社。
曾国藩的“心病”
对此情形,曾国藩自有清醒认识。早在咸丰八年,鉴于军中哥老会蔓延,曾出台营规:“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其态度不可谓不严。
然伴随湘军裁撤进程深入,大量昔日子弟兵涌回湖南加盟哥老会,若再采用雷霆手段,既不利于乡梓安定,又会大失人心,曾国藩不得不转变策略,确定了“但问其有罪无罪,不问其是会非会”的指导思想,并根据兵士犯事程度不同,区分为“大罪”、“中罪”,“小罪”,即“所论罪者,大罪一条谋反叛逆是也。中罪三条,一曰杀人伤人,二曰聚众抢劫,三曰造蓄军器是也。……或犯小罪更不问其是会非会矣”。可见除了“大罪”,对于“中罪”,曾不愿株连过深,采用“就案问案”的方式,只问具体案情,不问是否入会,尽量缩小打击面。对于“小罪”则更是忽略不计。要之,曾期望用此方法,达到“会中之千万好人安心而可保无事,会中数千恶人势孤而不能惑众”之效。
湘军
不过但凡退役将士的待遇没有根本性改变,任何宽严相济、刚柔并用的办法俱是徒劳。同治八年二月,哥老会首领赖荣甫率六、七百人径扑湘乡县城,并欲“直下湘潭”,以犯省垣;同治九年五月,另一头目邱志儒等约期先抢浏阳县城,烧署劫狱,进犯长沙;同治十年,湖南哥老会再度大规模集结,先后攻破益阳、龙阳县城。面对如此燎原之势,曾国藩惟有喟叹:“湘省年年发难,剿之而不畏,抚之而无术。纵使十次全胜而设有一次迁徙,则桑梓之患不堪设想,殊深焦虑。”
就在哥老会在西南肆虐且逐渐波及沿海之际,曾为湘军效力、后被强行遣散、极具会党嫌疑的张汶祥一刀结果了两江总督马新贻的性命,于公于私,曾国藩都绝不能让裁撤湘军、哥老会与朝廷要案三者间挂钩。一旦此事曝光,对于数十万退伍军人,将是灭顶之灾;对于在职湘楚大佬,亦会深受诛连;对于地方政局,恐不免带来极大震动。是故,曾国藩只得能掩一时算一时,且瞒一日就一日。但他清楚:“该匪聚散无迹,起灭无端,勾结蔓延,牢不可破。将来承平日久,难保不乘间窃发,非惟吾乡之隐患,抑亦各省之深忧耳。”
这样的“中兴”靠谱吗?
同为湖南人,郑敦谨想必亦深深体味到曾国藩之“焦虑”,以及刺马案处理上的为难,所以于乡于君于国于民,他必须选择缄默,与曾联手保守此秘密。然而,此权宜之计的后果便是把恶果留给后人。之后数十年的各种暴动、民变、教案、起义乃至革命,我们都可以清晰窥见哥老会的踪影。曾国藩当年一手培育的湘军,在功成之际,居然转化为未来覆灭清廷的力量。这就是历史悖论的冷酷逻辑!
于此可见,张汶祥一刀下去,不仅刺死了位高权重的马新贻,更刺穿了大清帝国的“中兴”神话。
【国家人文历史】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