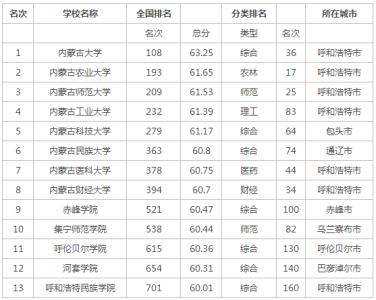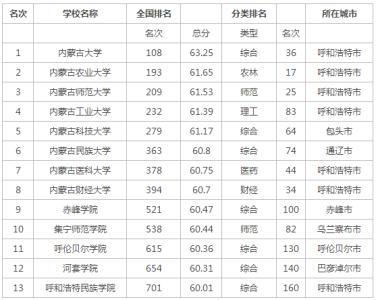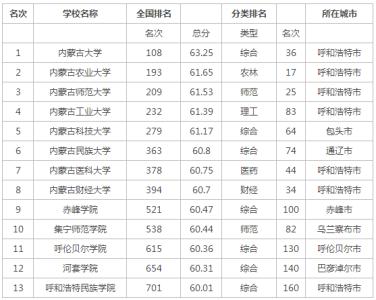●《隐身的串门儿》,杨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4月版
●《人物速写》,林文月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
●《阳光猛烈,万物显形》,阿乙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版
●《电影考古记》,胡文辉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9月版
●《我书架上的神明》,刘小磊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版
●《京都古书店风景》,苏枕书著,中华书局2015年8月版
●《悲伤与理智》,(美)约瑟夫》布罗茨基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4月版
●《巴黎速写》,(法)乔里-卡尔.于斯曼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3月版
● 这是一本作者的读书随笔,读的也多半是外国文学,譬如萨克雷的《名利场》、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中文的有一本《红楼梦》阅读,却是1959年写下的。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小说和戏剧,写才子佳人的恋爱往往是速成的。譬如《西厢记》里的张生和崔莺莺,又譬如《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和柳梦梅,皆是“天缘”偶得之。这种一见钟情式的快捷,西方文学也不遑多让,如莎剧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男女主角也是在舞会上一见倾心。宝玉和黛玉虽然相认之后,痴如宝玉也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但是情感的发生和发展却是一个漫长的困难重重的过程。杨绛一语道破地引用十六世纪意大利批评家科斯特维特罗的名言:“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南翔)
● 林文月过去写过不少文化名流。她本来出身望族,在学业上又多遇名师,写那样的文章自是当行;以其学养才情,若是像章诒和、齐邦媛那样写回忆录,必是游刃有余的。但这本集子却偏偏避熟就生,舍易求难,不写名人———事实上,她刻意隐去了人物的名姓,仅以字母指代。她写的是自己接触的“普通人”,即便写的不算“普通人”,也是作为“普通人”来写,描写的重点完全落在人物的日常言行细节上。而她捕捉到的这些言行细节,这些言行细节所构成的情境断片,却是最有感染力的,或许比她过去写的所有文字都更有感染力。大约正因为写的是“普通人”,才更写出了人生中更本质的东西吧。
林文月是真正的“美女作家”,她过去的文字似乎多少有些矜持。文如其人,美女往往是如此的。但这本书成于近岁,红颜已作素颜,文字也归于平淡,反而更加直达内心。(胡文辉)
● 阿乙除了是好的小说写作者,更是这个耐性稀缺的时代真正凤毛麟角的文体家。这本最新随笔集的宣传语是“每一个选择了孤独的人,都走在少有人的路上”,又说,“这是无尽时间里的一小段,旷日持久之事它可能的来源”,并决意要“拨开雾障告诉我们”,“人有活在云端的可能”。作为同样有语言洁癖的写作者,我相信这腰封上大多数文字都曾经阿乙本人同意,因此这本调性别致的散文集除了文章由首字母A排到Z的独特排版方式之外,更值得读者注意的,也许是阿乙对于文体实验的乐此不疲,对于时代国族寓言的隐秘热衷,以及反复排列组合字词、由此抵达汉语所能达到的最大延展性和可能性的科研精神。(文珍)
● 胡文辉的电影艺术品位和他的饮食口味一样令我难以恭维,但是,此公的学术随笔色香味俱足,实在精彩。这本小书是以电影为触发点的漫谈,看似天马行空的推想深藏考据之功,并慢慢引爆三观。可以说这是他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另一本书《拟管锥篇》的电影续集。所谓“拟”管锥篇,即是类似《管锥篇》那样,可以不断发掘新的例证,不断补注,重新阐发,继续增值,那么,《电影考古记》就是一部从电影出发的、可以继续无限生长的书。例如《“打飞机”的文学史》完全可以衍生成一部专著,如菲利普·罗斯的《波特诺的怨诉》,这部小说据说“对手淫的研究和梅尔维尔对鲸鱼的研究一样透彻”;又如《记忆灰烬中的华南海盗》令我想到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女海盗金寡妇》(收入《恶棍列传》),这篇小说末尾关于龙和狐狸的描述很有意思;《“逝纸”小札》则让我想到小时候在汕头家门口不远看到的中越战争阵亡名单———把潮汕地区的牺牲军人用红纸黑字“张榜”贴在街头,那也是一种另类的“逝纸”(准确地说就是日本电影《最后的赤纸配送人》中的“赤纸”),既是烈士光荣榜,又是死亡通知书。(张晓舟)
● 读书通常是有个人偏好的,因此有局限;读书又是需要朋友间互相推荐讨论的,这才不至于走弯路、浪费时间,也才能广见识,避免古人所谓的“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今天,一年出版几万种图书,没有人引导,颇不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书。但所谓的推荐书目,我又总是有些敬而远之。原因跟上面这本书一起来说,似乎比较容易些。给人荐书和谈影响自己的书,对象不同的,前者面对学生、读者,后者面对自己;态度也不一样,前者是为人师,有些居高临下的意思,后者是拜人为师,得虚心虔敬。也许,谈影响自己的书相当于亮底牌,道德文章可能就此被人看破。所以,我以为它排除了许多干扰因素,对有心读书、学习的人,似乎更有指导意义。(秦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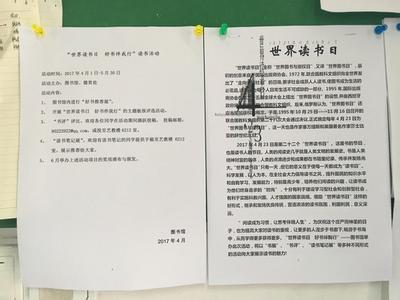
《京都古书店风景》苏枕书 著中华书局2015年8月版
● 苏枕书的文字自是细腻温婉的,但这本书的好处不仅在此。写到古旧书店的文字向来不少,但重心终究在书,在物,大都是到此一游式的猎书记;而此书的重心则真能放在书店,放在维系书业一脉的群体。这当然是凭她能长期居留京都,才能有此因缘;但其实更重要的,在于她的有心,在于她对古旧书从业者所抱有的那种“温情与敬意”。这是一部有情的书,其有情既是对书的,也是对人的。
今年韦力的《失书记》、《得书记》两种,也是有关当今书业的佳作。相比之下,韦力写本土的古籍拍卖,笔下多的是轶闻掌故,更有趣味;苏枕书写东瀛的古旧书店,笔下多的是心意人情,更有韵味。他们共同的精彩处,是写出了古旧书背后活生生的人,有了这些人,才有了故纸精魂永远的聚散。(胡文辉)
● 一位将诗歌视为“语言的最高形式”和“我们整个物种的目标”的大师,其散文写作是诗歌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和延伸,二十一篇文字的共同主题仍是“诗与诗人”,有着诗的精准、强度和密度。在《小于一》之后,于边疆大暴雪中阅读布罗茨基的“天鹅之歌”(最后一部英语散文集),是取暖、提神、告慰,可以强健我们的精神与体格。他探求的“悲伤”与“理智”,是两种对立的情感元素,却是语言最有效的燃料,是永不褪色的缪斯的墨水;他的“颂扬苦闷”,使我们有了“目不转睛直面糟糕”并捍卫热忱的勇气。读这样的书,可以改善我们内心,进而改善语言和思想的现实处境。刘文飞的译笔老道、舒展而有力,恰切地传递了大师的声音,以及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气度与神韵。(沈苇)
● 不要被大路货的书名所蒙蔽,以为这是本普通的风景导览书,展现巴黎旖旎风光。于斯曼所详细绍介的,可能并不是你想去的,比如“涌动着暗绿色的涡流,浮动着星星点点的痰渍”、“会动的厩肥”海狸河。本书中,于斯曼将大半目光投射于下等阶级,赞美底层的一种粗野的活力。如今,人们一说起于斯曼,只会想到“耽美派”、“颓废主义者”之类的标签,但他也有他的现实关怀。景物描写之外,书中还有很多人物速写,读于斯曼写的十九世纪末巴黎的底层妓女、工厂女工、剧院演员、洗衣妇等等,是会让人想起波德莱尔的。如同波德莱尔,于斯曼是观察、通感、设喻的大师,文字比波德莱尔来得更加绵密,更加浓稠,让读者的感官全部舒张开来。(卢德坤)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