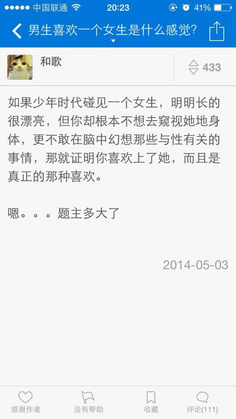时代的风尚转变了,20世纪60年代的理想主义、改变世界的愿望,让位于70年代的幻灭与狭隘的个人主义。嘲讽成了时代的情绪,人们在乎的是姿态,而不是内容。
此刻的中国,人人都在谈论韩寒,他像是越来越压抑、越来越迷惘的时代最后的救命稻草。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说他头脑清醒,媒体欢呼他是“青年领袖”、“年度人物”,青年人觉得他不仅很酷,还有思想。
没人能否认韩寒的魅力。他能把赛车冠军、畅销书作家、叛逆小子和即兴讽刺者等多重角色集一身,并能在种种诱惑面前保持警惕,况且他才27岁。人们尤其着迷于最后一点,他在自己全球浏览量第一的博客上,嘲讽这社会中的种种愚蠢和不公——它们绝大多数与这个越来越膨胀和傲慢的官僚系统相关。有些时候,他不仅嘲讽,还期待创造意义,尽管他还不清楚这意义到底是什么。
作为一个青年,这似乎已经够了,他必定是我们时代最可爱、最聪明的明星人物。但很多人(包括一些自认为有思想的人)把他推到了一个令他本人都倍感尴尬的位置——要他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象征着思想的力量,象征着对权力的反抗。
但这不是韩寒,人们越是把他推向这个位置,越暴露出这个时代、这些高声呐喊者的愚蠢、脆弱与怯懦。在某种意义上,韩寒的胜利不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这个正在兴起的庸众时代的胜利。
是的,你可以说每个杰出人物必然与他身处的时代相关联,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名声和有影响力越来越与个人的质量、才能与成就无关。在西方,这是个帕丽斯·希尔顿和苏珊大妈的年代——她因为有名而有名,因为不怕出丑而有名。在中国,这是个李宇春与小沈阳的年代——人们因她小小的个性,或是他的自我贬损,而把票投给他们。
韩寒与他们不同,却也是被同样一种力量推到今天的舞台上。他是这个时代明星文化与成功文化的产物,也符合这个时代所推崇的业余精神——赛车、写作、表演,你都要会一点;他还下意识响应了日趋匆烈的反智倾向,他的文章总是如此浅显直白,没有任何阅读障碍,也不会提到任何你不知道的知识;还有他嘲讽式的挑衅姿态,显得如此机智;他还熟知挑战的分寸,绝不真正越政治雷池一步;他也从来不暴露自己内心的焦灼与困惑,很酷。
于是谈论韩寒、成了一次全方位的心理按摩。你沐浴了青春、酷、成功、机智,还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反抗,同时又是如此安全。你不需要付出任何智力上、道德上的代价,也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彷徨,他是这个社会最美妙的消费品。
但世上真有如此美事吗?用刘晓波来比较韩寒,既不恰当也不公平。但是,公众对两者的态度,却最好不过地映衬了这个时代的特征。人们不谈论刘晓波,是因为他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公共话语空间,也因为这有点危险。但集体性的沉默与忽视也在表明,其实我们对于真正的自由与反抗毫无兴趣,甚至心生恐惧。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它不仅要反抗,而且有明确的主张。这需要智力与情感上的成熟,并愿意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
对韩寒的热烈推崇,是整个社会拒绝付出代价的标志。当我们沉浸于只言词组的嘲讽时,一定误以为自己已消遣了这可恶的权力体制,其实一点没变,嘲讽只是为上面裹了一层糖衣,但我们进行自我麻醉,还将此视作一次反抗。
而且,人们或许也觉得,韩寒也不需要为行动承担任何后果,他可以进行象征性、边缘性的反抗,然后还全身而退,像是去商场进行一次购物。韩寒成了所有人的借口,人们借着他撒娇,卖弄自己那可怜的“小心思”。
但公众必定要为这种愚蠢和怯懦付出代价。既然他们对于真正的成就缺乏兴趣,不去赞叹那些卓绝的道德勇气,不去准备接纳真正的思想,他们就只能在这个烂泥塘中继续打转,相互抱怨、相互麻痹。因为这庸众的数量是如此的巨大,他们还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中国已经影响世界。中国的确影响了世界,但它只是数量上的造就,而非真正值得尊敬的成就。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时代内在的苍白、可悲、浅薄—— 一个聪明的青年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
(刘海博荐自《时代青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