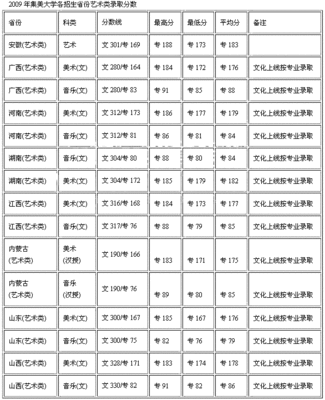报社新来了一个实习生,嘴甜人靓,报到的头一天,依次走到办公室每个人面前自我介绍:“某老师您好,我叫某某,请多多关照。”一同奉上的,还有甜美微笑和亲手冲的雀巢咖啡一杯,虽然是速溶的,也够暖人心了。
带她出去采访,总是一口一个老师,我开始让她直呼其名,后来见她执意不肯,也就由她去了。
小姑娘很讨人喜欢,就是对于从事这一行缺乏最基本的常识。再重要的会她也是踩着点儿到,偶尔还会迟到,坐在会场埋头就玩手机。回去时试着让她写个初稿,她连出席领导的名字都记不全。后来我就很少带她去采访了。
一天深夜,我去报社拿点东西,走进办公室看见这小姑娘正对着电脑奋战,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熬得通红。
我问她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去。
她一听,眼泪刷地掉了下来,抽咽着告诉我,她的实习期快到了,一直想争取留下来,可是领导列举了她实习期间种种不合格的表现,告诉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们说我开会不知道提前十五分钟去,写的稿子连五要素都不全,可是这些,都没有人手把手地教过我啊。”小姑娘圆睁着一双无辜的眼看着我。
我不知怎么才能告诉她,在新闻行业,永远都不要太过指望有人会手把手教你,老记者也带实习生,培养出师徒情谊的还真不多。
不过,在我的记者生涯里,倒确实碰到过这样一个人,如果不是他那么耐心教我的话,我很有可能和这个深夜哭泣的小姑娘一样,独自摸索了几个月连新闻的门都摸不到。
我从来没有叫过他老师,但在我心目中,他就是我师父。
我初到这个报社的时候,还只有二十出头,研究生还没有毕业,表面上看起来骄傲无比,实际内心充满了惶恐。
还记得刚来那天,我跟着人事科的人走进采访部,偌大的一个办公室,黑压压的坐满了人,见我走进来,大多数人连眼皮子也不抬一下,继续埋头赶稿。
我被分配到一个角落里坐下,指望着能有谁告诉我应该做些什么。这个报社没有老带新的制度,实习生们被随便塞到哪一个组,就只能等着记者们乐意时带出去做些采访。做为一个羞怯到死的新人,我一开始只有对着电脑枯坐的份,所有人都在忙碌,只有我无所事事,那个下午,我真害怕会这样一直枯坐到天荒地老。
快下班时,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到主任面前去,让他给我点活干。
主任问我:“你会干什么?”
我想也没想就答:“我什么都不会。”
现在想起来真是欠揍。
主任是个老好人,宽慰我说没事看看报纸先,坐在旁边的一个男记者倒是发出了忍俊不禁的笑声。
我只好回到角落里继续枯坐,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隔壁的格子间探出了一张笑脸,有人对我说:“嗨,你好,我明天有个采访,你愿意跟我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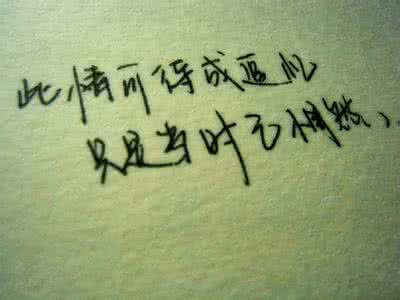
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张笑脸无比灿烂,尽管眼角边的褶子多了些。
他就是刚刚那个笑我的男记者,后来他说,认识我的第一天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怎么会有那么傻的人,居然敢当着领导的面说自己什么都不会。”
我觉得他更傻,既然已经知道我这么缺心眼,还主动请缨带我去采访。
这个笑我的男人后来成了我师父。
回想起来,他的笑脸对当时的我实在太重要了。你可以想象,一个还没毕业的姑娘,只身南下,举目无亲,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要多无助就有多无助。这时候有人愿意向你示好,哪怕是根稻草,也会拼命抱住。
其实他只不过比我先来报到几天而已,不过在这一行,已经很资深了,据说写过一些很牛逼的稿子,拿过大大小小的奖项。
我那时还是个想在这一行业有所发展的人,不可否认,那段牛逼哄哄的从业经历让他增色不少。
更何况,他长得还真不错。一米八的个子,瘦削,挺拔,头发剪得很短,剑眉星目的样子。连楼下子报的同行见了都说,这个小伙子可真精神。
其实,他哪是什么小伙子啊,对于我来说,三十好几的他简直就是个半老头子了。我不知道他到底大我多少,不过从他笑起来眼角的褶皱来看,应该是大了很多的,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是视他如师长的。
他是扬州人,头一次听他自报家门时,我惊叫了一声说:“呀,原来就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那个地方啊。”
他很骄傲地补充说:“还有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扬州遥不可及的月色给他增添了一圈光环,再看他时,觉得他有点像金庸笔下的江南侠客,白皙、俊朗,侠骨柔肠。不同的是,侠客用的是剑,他用的是笔。
事实上,他爱的是古龙。我们为金古二人谁优谁劣争论过几个回合,谁也没说服谁。他批评说金庸著作冗长、拖沓,男女主角都装纯情。我反驳说古龙作品良莠不齐,笔下人物都像一个模板铸出来的。比如说,楚留香和陆小凤,两个人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他回答说:“当然不一样,楚留香是踏着月色而来,陆小凤是四条眉毛一颗自在心。”
在我听来,还是一个样。可是他自认为已经说服了我,脸上露出洋洋自得的笑容来,他是个固执的人,普通话中苏北口音很重,很奇怪,扬州话不像上海话那样嗲,而是有些硬气,特别是在他嘴里更有种斩钉截铁的味道。
这种固执表现在工作中就是莫大的新闻热情。
印象中的江南书生应该是斯斯文文、温润如玉的,他的外表也许会给人这种错觉,可是言行举止却偏执顽固,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有同事叫他新闻疯子,他接到新闻线索,半夜都可以从床上爬起来,只要想做的新闻,再敏感都会想方设法说服领导。他到这里没多久手里就有了批“线人”,隔三岔五地向他报料。
我常常被他的热情所感染。有时冲了凉正准备睡觉,他一个电话过来说:“快出来,有个猛料,十分钟后集合。”我立马一激灵从床上跳下来,随便换套衣服就冲[www.aIhUaU.com)出门。
我们曾经为了一个新闻线索倒了几趟车去偏远乡下采访,回来的时候车都没了,走了好远的路才打到车,回到报社饭都顾不上吃就赶紧写稿。第二天见报了,整整一个版,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紧紧挨在一起,像是两个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我偷偷把那张报纸收藏起来,有一种隐隐的骄傲和喜悦。
那是我进报社以来的头一个重头报道,尽管不是第一作者,也算是小有成绩了。只有他知道我背后所做的努力,刚来那会儿,我连个导语都写不了,是他教会我,如何去寻找新闻线索,如何和陌生人搭讪,如何巧妙地提问,如何写出一篇像模像样的稿子。
爱华网 www.aIhUaU.com欢迎您转载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