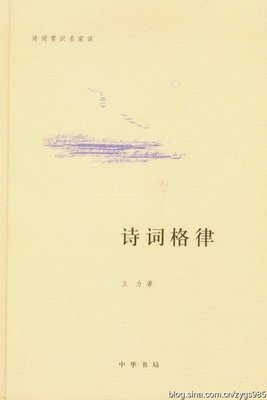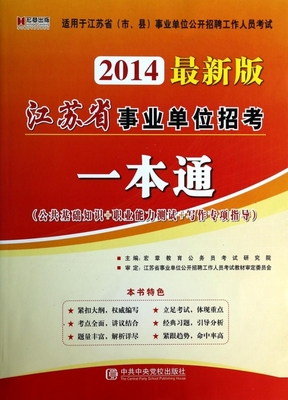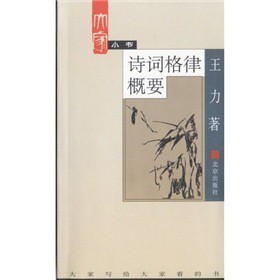写作旧体诗词要通顺合律原文地址:写作旧体诗词要通顺合律作者:剑胆箫心
旧体诗词篇幅短小,予人以容易驾驭的印象,故颇受一些作者青睐,动辄便率尔操觚起来。逢节日如元旦国庆,遇重大事件如香港回归,更是写作发表旧体诗词的高潮。
旧体诗词也是文学园地中的一朵小花,甚至可说是国粹,它受重视得发展,原不能说是坏事。
但从本质上说来,旧体诗词是古代汉语的产物,现代人很难写出合格的旧体诗词。
在封建社会,古汉语——文言文,是书面共同语。学生在学校要接受严格的古汉语教育,而吟诗作对恰又是古汉语教育中重要的学习内容和训练形式。鲁迅先生早期创作的文言小说《怀旧》,就有记述私塾中学习作对的片段:“彼辈纳晚凉时,秃先生正教予属对,题曰‘红花’,予对曰‘青桐’,则挥曰平仄弗调,令退。时予已九龄,不识平仄为何物,而秃先生亦不言……久之,始作摇曳声曰:‘来’。予健进,便书‘绿草’二字曰;‘红平声,花平声,绿入声,草上声,去矣。’”传统蒙学教材,从《三》《百》《千》到《龙文鞭影》到《幼学琼林》,或有大量对偶成分,或全是对偶,更何况还有专门的关于对偶的教材和工具书如《声律启蒙》和《笠翁对韵》之类?夸张一点说,传统语文教育就是培养人作诗,培养人作诗人。凡接受严格的系统的传统语文教育的人,大都能写几首诗词,难怪中国古代诗那么多诗人那么多。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书面语言的地位。现代人既然在生活中已不再运用古代汉语,自然也就无须再下苦功学习它。文科高等教育开设的古代汉语课程,是对汉语规律的总结,并不是进行运用古汉语的训练。即使你在其中学到了一些旧体诗词的知识,不经过专门的训练也写不出合格的旧体诗词。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笔墨祭》中曾慨叹:“作为一个完整世界的毛笔文化,现在已无可挽回的消失了。”我们也可以说,旧体诗词在现代社会中也已失去了了它赖以生存的皇天后土,“不管如何提倡张扬,唐诗宋词的时代已绝对不可能复现。”(出处同前)旧体诗词遂成为现代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奢侈,并因此而不可避免地给旧体诗词的写作带来先天的不足。
现代人写作旧体诗词,最常见的缺点有两个:一是不通顺,二是不合律。
旧体诗词字数句数押韵等均有严格规定,古人受过训练,不是大家也很难做到挥洒自如,今人本不谙此道,勉强为之,就不免词义汗格,捉襟见肘。有时不得不削足适履,割裂语词,生拉硬凑,以就字韵,遂或使意义不通,或使格律格格不入,画虎不成,反类为犬了。
《诗林》1997年第4期刊登的旧体诗词,可算是上述缺点的集大成。如署名晨号的《茶余小品七首》就几乎没有一首是通的。其中,《社鼠如硕》《忆蓬游四首》题目就不通。“硕”本义是头大,(见《说文》)引申为大,如此,“社鼠如硕”岂非等于说“社鼠如大”?这成话么?“蓬游”据诗的内容,是“蓬莱之游”的意思,但“蓬莱之游”能说成是“蓬游”么?它如“绿晓”“登仙”“浪鼓”“森樯”“声飞壮勇”这些词,“醉解权姻眠双月,背应礼士锻独钩”“劝进谀词强项修”“乡愿从来社鼠贼”“老朽茶余品珍爱”“有灵不在高入云”这些句子,都是不通的。譬如“双月”是两个月,还是与单月相对的“双月”?“强项”是秉性忠直、不肯屈服,“劝进谀词强项修”等于说“劝进谀词”是一个忠直不屈的人写的,岂非自相矛盾?宋邢居实撰《拊掌录》载:“哲宗朝,宗子有好为诗而鄙俚可笑者。尝作即事诗云:‘日暖看三织,风高斗两厢。蛙翻白出阔,蚓死紫之长。泼听琵梧凤,馒抛接建章。归来屋里坐,打杀又何妨?’或问诗意,答曰:‘始见三蜘蛛织网于檐间,又见二雀斗于两厢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吃泼饭,闻邻家琵琶做《凤栖梧》。食馒头未毕,阍人报建安章秀才上谒。迎客既归,见门上画钟馗击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哲宗尝艾灼,诸内侍欲娱上,或举其诗,上笑不已,竟不灼艾而罢。”写旧体诗词而意义不通者,大率类此。
同期《诗林》雁翼词《长安情长词五首》,则没有一首合律。如《菩萨蛮》,本来上下阕均为两仄韵转两平韵。但雁翼词《菩萨蛮·西安小景》中,上阕尾句“墙头葫芦绿,墙里榴花红”,下阕首句“更有摩托车,追出一阵风”,均未按词律押韵。再如《鹧鸪天·登始皇陵》,上阕押了仄韵,下阕作“猛悟醒,日月更,他已成历史玩具,贤者说他是鬼魔,愚者玩他是蛟龙。”不但未按律押韵,平仄也不调,且后三句成了一个单位。好好一首《鹧鸪天》,被他大卸八块,亏他下得去手。明冯梦龙《古今谭概》载:“嘉靖间,有织造太监在杭州,征索不遂,为诗云:‘朝廷差我到苏州,府县官员不理咱。有朝一日朝京去,人生何处不相逢。’监司叹曰:‘好诗。’答曰‘虽不成诗,叶韵而已。’”写旧体诗词而不合律,大率类此。
所以,我以为,写作旧体诗词要慎重,总要做到通顺,大致合律,不能出现硬伤。不熟悉古汉语那套语汇语法,可径以口语入诗。古人中也有不少人以口语写诗词,唐的王梵志,专写口语诗,宋的黄庭坚、柳永,都以口语填过词,更不必说浩如烟海的民歌民谣了。不熟悉旧体诗词的格律,可以先学习一些基础知识,写作时,写完后,对照着检查一下,就大致能说得过去了。古人写作诗词,也是要随时翻检韵书之类的工具书的。杜甫曾有诗说:“觅句知新律,摊书解满床”,这满床的书中就应该有关于诗律的工具书在内。
于是就想到了启功先生。启功先生,古典文学专家,诗词一道,尤为精通。他的《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却多以口语入诗,别具一格。诗如悼亡的《痛心篇二十首》之一:“妇病已经难保,气弱如丝微袅,执我手腕低言:‘把你折腾瘦了。’”词如《鹧鸪天·乘公共交通车》:“铁打车厢肉作身,上班散会最艰辛。有穷弹力无穷挤,一寸空间一寸金。 头屡动,手频伸,可怜无补费精神。当时我是孙行者,变个驴皮影戏人。”或沉痛或诙谐,均明白如话家常,但又是地道的旧体诗词。这番以旧瓶装新酒,摧刚为柔,婉转如意的功夫,足资学写旧体诗词者借鉴。而他的《心脏病突发,送入医院抢救,榻上口占长句》中有“填写诊单报病危,小车直向病房推。鼻腔氧气徐徐送,脉管糖浆滴滴垂”的句子。诗后自注云:“诊有平读,见《急救篇》。此首杂用支灰诸韵,以其时实不能检韵书矣,方家赐阅,幸揭过之。”(见《启功絮语》)此固可见先生的谦虚严谨,另一方面,以先生的学问功夫,写作诗词尚需“检韵书”,何况后生晚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