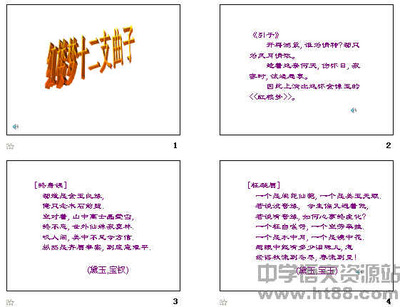<?xml:namespace prefix = o />
泪尽太虚心意冷,愁添红楼梦魂羞<?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开谈不说红楼梦,
读尽诗书亦枉然。
诗书百年能读尽,
红楼一梦终不还。
对于芹溪先生的一部百年巨著《红楼梦》,世俗者多以爱情悲剧谓之,至于文墨骚客、红学大家,乃有“三事”,而后“四说”。三事者,宫闱事、性德事与家务事;四说者,蔡元培的政治说,邓狂言的种族说,景梅九的国运说和季新的挞伐说。各“事”各“说”无不有理有据,无须虎虎,而自生风。纵观百年红学,京城梦断,长安雾隔,正是那“滴不尽的相思血泪抛红豆”和“忘不了的新愁与旧愁”。
《红楼梦》的立场问题,也许就跟它自身的出处问题一样,永远都是一个难解的谜。而我们,也只好藉着可怜而又可笑的猜笨谜的方法去阅读和品味它的内在与深涵了。读《红》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思《红》的过程,悼《红》的过程,忆《红》的过程和叙《红》的过程。想曹翁“满径蓬蒿华不实,举家食粥酒常赊”,文悲青山,泪洒絮酒,断不是宫闱、性德、家务琐事那么简单,更不是所谓爱情悲剧的小女儿情怀。很明显,“三事”是很难站住脚的。回看“四说”,又觉各执一词,各是一说,更多地体现了论述者的用心,而不是《红楼梦》的立场。
在这一点上,我比较认同北大李零先生的观点。《红楼梦》的实质,其实是一部阴盛阳衰的败家史,是“伤心事”和“感怀说”。贾府的由盛而衰,实际上是贾府男丁的由盛而衰。从贾家几代人的取名,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代化、代善一辈,“代”字从“戈”,尚且英武挺拔;及至敷、敬、赦、政,易“戈”从“文”,就已经少了几许阳刚;到珍、珠、琏、玉,则不过挥金弄玉纨绔浮夸之流耳;等到了蓉、蔷、芸、芹,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草包,一个个比女人还要女人。文学看透了就是现实,作为一代文学大家,曹雪芹通过对“梦”的伤心与感怀,完成了他对现实的伤心与感怀。正因为这个缘故,才使得脂砚斋、畸笏叟读《红楼梦》之时,动辄“失声大哭”、“血泪盈腮”。
正如贾志清说的,我们在研究《红楼梦》的时候,往往陷入粗鄙热情的泥沼里而不能解脱自己,把一些本来十分简单明了的东西人为地复杂化了。当然,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对《红楼梦》存在了太多的尊敬与崇拜,而使得我们不能以一颗平常而又理智的心去对它进行最起码的了解与认识。其实,在《红楼梦》的第一回里,作者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解析与暗示。“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食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等等,都表明了同一个立场,那就是对男子不肖到不若闺阁之人的喟叹。
说到这里,让我们好好瞧瞧《红楼梦》中所描述的男性都是些什么德行。要么“酷爱男风”,要么“偏好名伶”,要么“偷鸡摸狗”,要么“勾嫂扒灰”,肮脏得不成样子。百二十回的《红楼梦》,能看到这帮老少爷们干过什么人事?没有,甚至连一件也没。看到的只是“不因为俊俏难为友,正为风流始读书”的想入非非与“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书房”的吃醋争风,“蒋玉菡情赠茜罗帕”的同性相恋与“呆霸王调情遭苦打”的死性不改,“杏子阴假凤泣虚凰”的性别淆乱与“探惊风贾环重结怨”的无能不肖。总之,男人都不像了男人。
“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相反地,“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大观园中的女子却是“历历有人”。像刁蛮能干的凤姐,老练慧重的宝钗和风流婀娜的黛玉自不必说,单那一班子下人丫头就已经足够让贾家儿郎自愧地头撞南墙了。金钏跳井,鸳鸯抗婚,晴雯撕扇,司棋自杀无一不表现了比男儿还有的骨气。如果说司棋的自杀只是一种愚忠的话,那么尤二姐的自杀就具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那就是把自己毁灭给男人看,让那些男子更加显得一钱不值。宝玉作为一个自始至终以女人为中心的男性形象,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女人一个个地被毁灭。自此,作者只好侧面地通过黛玉笔下的女豪杰“红拂”和宝玉诗中的“剑仙”林四娘来实现女性的自立与自救。
清人姜祺说的好,“出梦迷离入梦明”,要真正地读清读懂《红楼梦》,就要把自己和书中的人物融合和统一起来。作者的创意与立场,或多或少地已经通过男一号宝玉的语言和行动有了揭示,宝玉同一干女人情感生活的明媚与萧瑟和这个家族的兴旺与衰落是分不开的。这种无法避免、无法分离的悲性因果,在某些程度上已经成了贾氏家族发展的一种趋势。“月满亏”,“水满溢”,“登高跌重”,“乐极生悲”,“树倒猢狲散”是必然的结局。
但可悲的还不是这种结局,而是引起这种结局的动因。“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大观园的抄检本来就已经成为贾门衰败的前兆,而皇妃元春的薨逝则更成为贾家失势的必然,到后来连顽笑着就有杀伐决断的凤辣子也病倒了,便使得贾家这头拔根汗毛都比穷人家的腰粗的骆驼终于不可再支而轰然倒塌了。到这里,曹雪芹才真正完成了对红楼残梦瞬息间乐极生悲、人非物换的辛酸了结。
细思绛珠二字,本就血泪,是幻来亦真,真来亦幻,亦真亦幻的情节凝聚。空空、无为,则更多的是作者对现实的一种逃遁。心可得逃而身不得逃,以至雪芹曹翁“说到心酸处,荒唐愈可悲”,泪尽太虚,愁添红楼,令我辈情迷性惘而不知其返,不知道是人入了梦,还是梦进了现实。区区在下妄不知狂,撰文以记之,以有斯篇。正所谓:千古辛酸一场梦,世间荒唐醒时休。晚生后辈不知狂,片语只言语众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