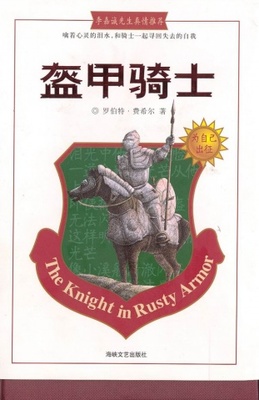在“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一回中,横看竖看,最终明白“意淫”实为一个“痴”。
曹雪芹首先排除了那些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回头来看石头对空空道人的表白“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情笔墨。其淫秽污臭……”,此类鄙陋文人,曹在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中,借老太太之口给予批判。
其次,曹并非是禁欲主义者,他认为“好色即淫,知情更淫”,然“淫虽一理,意则有别”,于是再将 “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的一类排除。
曹最后指出:“意淫不可口传,要可意达神通。得此二字者,于闺中固可为良友,但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如此,“意淫”就只剩一个“痴”,但仅作这样的解释好象还显抽象,于是存稿中,此后的近七十五回里都有一些具体的故事。
从曹雪芹关于这个“天下第一淫人”的痴故事中,可以看出,除开对茜雪撒气外,总体上他对女性的是尊重的,总是关心这些人的命运,过得好不好等,如:二丫头、珍大爷家的那个万儿(那个符号是佛教的而不是纳粹党人的,开口方向不一样)、刘姥姥故事中大雪天里的那个女孩等,至于十二钗正册又副册中的就不用说了。对那个二丫头,秦钟扇情地说,这类女孩最得趣,结果让他“该打!”厉声止住,最后大队人马起程时,他还呆望,用目光找寻。那个“万”儿,他一脚踹开门时,本来是想呵斥茗烟的,结果把那个“万”儿惊着了,虽然早跑了,他又担心吓着她,又追去叫:别当心,我不会说出去的。其实早跑得无了踪影。又问茗烟这女孩子的岁属,茗烟不知,他指责茗烟:人家白跟了你了。刘姥姥那个故事,他一再追问那女孩子的结果,弄得贾母都不耐烦了。对香菱。那几个小丫环把香菱推下水池。香菱为薛姨妈给自己的衣服才穿上就弄成这样发愁时,他让袭人找相同一件,暂且替香菱去掩饰时。读到这,我也不耐烦了。“男”人怎么能成这个样子?可后来,当他痴得恳求王道士开一剂治“妒”的药方,想替夏金桂治好妒病,就可以减少对香菱的迫害时,才理解:他命中真是带着“闺阁良友”。此类故事多着呢,有心者可以慢慢找,一定比我找得多。
除开袭人,对十二钗的情有没有性的成份?有。对林妹妹有,不敢。在二人读《西厢记》时,他无意间说出:我就是那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个倾国倾城貌时,林妹妹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指他要告舅舅时,把他吓得直告饶。其实林妹妹也没有真怒,唉!他的脑筋如何转得赢林妹妹。
对宝钗没有,也不敢。这里有个奇怪的事,就是无论袭人怎么劝他取仕途经济,他并不反感袭人,反而是对宝姐姐,他说林妹妹不说这等“混帐话”,宝姐姐说“混帐活”。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在这位漂亮的大姐姐袭人身上,他找到了一种恋母情结。虽然对宝钗没有性的成份,但他幻想宝钗的那条臂膀要长在林妹妹肩上就好了,嘿!这家伙跟郭末若一个样子。
对史湘云没有,还是膀子的问题,见状,他只说连睡觉也不老实。于是,拿衾被将她盖上。并非史湘云不动人,而是可能就当作一个妹妹,也不是他不在乎,睛霁撕毁的那把扇子正是云妹妹送给“爱(二)”哥哥的,他急了。
对妙玉没有,爱吗?不知道。乞红梅时,“槎枒谁惜诗肩瘦”似乎是掉进了某种情感旋涡,但送拜帖时却又十分认真干净。
对晴霁没有,不敢。对紫鹃没有,因为敬。对金钏有,为此受到笞挞。对鸳鸯有,但赖皮不成。直到见过贾蔷和伶倌那一幕,他明白了:世间眼泪各有所属。
但曹雪芹同时提出这是一个“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劝世人不要学,曹是否对以上所述又作否定?不是,曹提供了两派人物。一派是秦钟、贾瑞,别一派是贾芸、贾蔷。作者对前者基本上是否定的,而对后者则持肯定态度。关于秦钟,幼年丧母,本应当是自己立志的时机,但此君在义学中行龙阳之风,闹得污喧喧,真真一个“早知日后生闲生气,岂肯今朝错读书”,最后竟死在一个“情”上。至于贾瑞,作为义学的教导主任,又是代儒老先生的孙子,无论是研究学问还是管理学校,都处于近水楼台,但他喜好与士族弟子中的坏透了的一干人混在一起。最后死在那“风月宝鉴”里头。
贾芸、贾蔷似乎是曹雪芹替秦钟、贾瑞这派人物提供的正面样板,四人身世相差无几,但贾芸、贾蔷却成为完全不同的一类人。
对此存在异议的应当是贾蔷,他和贾蓉受命于凤姐,一道讹诈贾瑞,逼贾瑞写了一份欠银俩的借条。读者在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认为贾蔷坏得很,确实坏。然读到后面梨园里的那个伶倌在地上画“蔷”字时,读到宝玉想听曲到梨园里吃伶倌一计闭门羹以及随后宝玉看到的那一幕时,蔷哥这个“坏蛋”也有重感情的一面。且不说贾蔷是好人还是坏人,再回来看宝玉和秦钟在义学中闹腾的那一回时,发现贾蔷是珍哥让他离开宁府出去单过,但这个人在这秦钟与金荣的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机敏、世故可见一斑,省亲时他筹办演出班子也表现出少有的干练。
至于贾芸,多数读者不会存在异议,只是有些读者会认他在给凤姐送礼的那一幕有点谦卑,管宝玉叫宝叔也就罢了,还自认作“干儿”,连贾琏都听不过。但话又说回来,在这个世上活,世故一点也是必要的,逗着这些贵族高兴不就有工程做了嘛。宝玉自己不是也撒过谎吗,他不愿参加薛蟠生日拍提,我想主要不是略感小様,而是不愿在那里“吃花酒、狎娈童”,于是事后,假意称病不能去祝寿,去找宝钗倒个歉不就完了嘛。关于陶令采菊东篱,历来给人们一个认知上的误区,就是“独善其身”者一定要忍受贫穷。对此穷困一生蒲松龄在自己的《聊斋·黄英》一篇小说中有过一个故事(百家讲坛马瑞芳老师有过讲述),如今“良菊有信”成了寺庙里掣签时可获良人、财富的预测。看来无论是曹雪芹还是蒲松龄都不希望取仕不弟者一生都忍受贫穷。
过去读红时,觉得此儿是奶油小生,是呆子又有几分傻,现在觉得此人是极精细,精于人情世故的。如给林妹妹送尺幅(绞绡)时,他先把袭人支开,再命晴霁去办,晴霁说凭白无故,送一旧帕有什么意思,这家伙说,送去林妹妹自然知道。彩云偷了茉莉粉,平儿行权时,这家伙一一揽了下来,主要是为了三妹妹探春。这才能,若用于官场,一定比雨村作得好。还有疏才仗义,他身上的配饰每一件拿出去,二十两银子值吧,让小厮们摘了去,他从不在乎,他倒是在乎林妹妹缝的那个香囊,特意装在里间衣内。他在那个家族中的位置太特殊了,一般人不具有这样的条件,只能拼命去挣钱或为日后如何养家糊口考虑,林妹妹见探春将诸位姊妹的生日办得中规中矩,曾叹:难为了三妹妹,也只有三妹妹了,换作别人,早就专横跋扈。这家伙对林妹妹说,再难也少不了我俩花费。臭小子,不当家不知油盐柴米贵!但是,这家伙在一大堆姐姐妹妹小丫环中,亲情、友情、爱情、恋情等旋涡中转来转去,倒是分得清清楚楚,就像稽中散阮步兵那样,不守礼法,但深得其意,曹雪芹也真够难为他了。
因此,曹关于意淫的正解,并不是目前网络中所说的那种现代心理学称的淫幻想,而是他对世间各种情况的归纳作一一排除后,留给读者的一个个故事中的一些细节。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