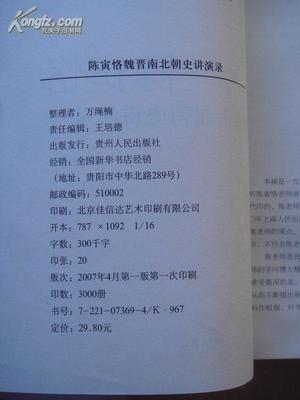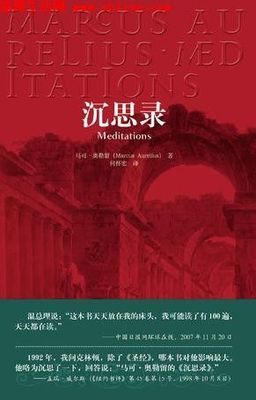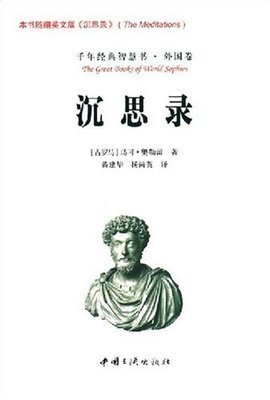《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1
斯蒂芬·杰·古尔德
田氵名译
---------
序言
---------
1959 年,美国著名遗传学家H.J.Muller 抱怨道:“这一百年没有达尔文也一样。”这一特别黯然的评价使当时参加纪念《物 种起源》问世一百周年的许多听众都感到震惊,但是没有人能否 认这一失望中所表达的真理。
为什么那么难以理解达尔文?不到十年,他就使思想界不再 怀疑进化的发生,但他一生都没有使人们普遍接受他自己的自然 选择理论。直到20 世纪40 年代,自然选择理论才被广泛接受;然而即使在今天,虽然自然选择理论已经成为我们进化论的核心,但依然存在对于自然选择理论的错误理解和错误使用。问题并不在于这个理论逻辑结构上的复杂性,因为自然选择理论的基础本 身很简单--两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和一个必然得出的结论:
1.生物是可变的,而且生物的变异可以(至少是部分)遗传给后代。
2.生物产生的后代数量多于可能生存下来的后代数量。
3.一般来说,生物的后代向着环境对起更有利的方向变异,就会生存并繁衍下去。
这三段陈述基本上说明了自然选择的作用,但仅仅这样说还不是达尔文认定的自然选择的根本作用。达尔文理论的本质就在于认为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创始性力量--不仅仅是不适应生物的剔除者,自然选择还必然要建造适应;自然选择通过一代又一代地保留随机变异中的有利部分,必然会建造适应。倘若自然选择是创造性的,我们关于变异的第一条陈述就必须增加两条限制来详细说明。
第一、变异必然是随机的,或者至少不会是向着适应的。因为假如变异已经预定向着正确方向的话,那么选择就不会起着创造性的作用只不过是剔除那些变异途径不妥的不幸生物个体而已。拉马克主义就是这样的看法,该理论坚持认为动物创造性地回应它们的需要,并且将获得的性状遗传给后代。这是一种非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我们对遗传变异的理解表明,达尔文正确地坚持了变异的有利方向并非预先就决定了。进化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混合--在变异水平呈偶然性,在选择方面呈必然性。
第二、变异必然与新物种形成中进化变化的程度关系不大。因为假如物种是即刻产生的,那么自然选择便起不到创造性作用,只不过改善的生物腾出位置而已。再者,我们对于遗传学的理解又支持了达尔文的关于小变异是进化变化的原材料的观点。
所以,达尔文的理论表面上简单,但具有精致的复杂性及另外的要求。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阻碍接受达尔文理论的并不只是科学上的困难,而是由于达尔文理论中所含的基本哲学内容是对于西方人心态的一种挑战,这种心态至今仍然难以抛弃。首先,达尔文提出进化没有目的。生物个体是为了增加它们的基因在后代中的代表而进行着斗争,这就是进化。如果说自然界中呈现出和谐和秩序,那也是因为生物个体尽显其优势所附带的结果而已,即自然界中的亚当.斯密经济学。其次,达尔文坚持认为进化没有方向,进化并不然导致更高等事物的出现。生物只不过更加适应它们所生活的环境,这就是进化。寄生虫的“退化”和蹬羚矫捷步态都是完美的。再者,达尔文在解释自然中贯彻了唯物
论的哲学。存在的只是物质;心灵、精神、上帝不过是表达神经复杂性奇妙结果的语词。托马斯.哈代在谈到自然时,对于抛弃目的性、反向性和精神的观点感到忧伤:
当我凝望黎明,池塘,
田野,牛羊,还有枯树,
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
像静坐在学校受罚的孩子;
它们发出的声响只是
(一度像是清楚的呼叫,但此刻却完全是嗫嚅)--
“我们惊奇,真的惊奇,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的确,自从达尔文以来,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但是依然叫人激动,给人启迪,令人崇敬;因为即使我们不能在自然中发现目的性,我们却能为了我们本身的需要确立目的。达尔文并不是对道德漠然的人,但他并不关心清除西方思想中有关自然的深度偏见。实际上,我认为可以用达尔文主义的精神来拯救我们苍痍的世界,因为这种精神否定了西方人的自傲所偏爱的一种观念,即我们要去控制、支配地球和地球上的生物,因为我们是一种预定过程的最终产物。
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需赞同达尔文。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理解他的信念和这些信念中的含义。这本书中的所有文章都是探讨“这种生命观”--这是达尔文自己在讲述他的新进化世界观时说的话。
这些文章,写于1974 年至1977 年。最初发表在《自然史杂志》我所开设的专栏上,这个专栏的名字就是“这种生命观”。这些文章涉及范围广泛,从行星史、地质史到社会经济史;但是通过进化论,即通过达尔文的观点,将这些问题串联了起来(至少我打算这样做)。我不是博学之士,倒像个好商人,我所知道的行星和政治知识都与生物进化有关。
我并不忽略记者的套话:昨天的文章只能用来包今天的垃圾。我也不打算糟蹋我们的森林去发表冗长而散乱的文集;象索依斯博士的《罗拉克斯》。我想我还是对树木留情的。不是出于虚夸,我惟想解释的是,收集这些文章都是根据许多人喜欢(同样许多人蔑视)的观察,这些观察同属于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达尔文从进化角度探讨的主题,这也是与我们自大的宇宙观背道而驰的一个主题。
第一部分探讨了达尔文理论本身,尤其是引发H.J.穆勒抱怨的基本哲学部分:进化无目的性,不是进步的,是物质性的。我通过一些有趣的奥秘来把握这个重要的信息;如谁是贝格尔号上的博物学家(不是达尔文);为什么达尔文不使用“进化”这个词;以及为什么他等了二十年才发表他的理论。
利用达尔文注意探讨人类的进化构成第二部分。我试图强调我们既有独特性又有与其他动物相关的统一性。我们的独特性是由于基本进化过程的作用,而不是由于任何通向高等生命的预先设定。
在第三部分,我通过利用一些复杂的进化论问题说明特殊的生物,从而探讨了这些问题。在一定水平上,这些文章是关于具有巨角的鹿,从体内食其母亲的飞虫,利用边膜进化成一种引诱鱼的蛤,以及120 年开一次花的竹子。在另一个水平上,这些文章涉及了适应、完美性和一些表面上好象没有意义的问题。
第四部分是用进化论来探讨生命史的图景。我们找不到稳定进步的迹象。这个世界在长期平静中间或有大规模灭绝和迅速生成的时期。我着重在两个重大的间断上,6 亿年前产生出绝大多数复杂动物生命的寒武纪“爆发”和2 亿5 千万年前一半海洋无脊柱动物灭亡的二迭纪灭。
从生命的历史,我转向生命居住的地方--地球的历史(第五部分)。我既论述了过去的英雄(莱尔,Lyell),也论述了现代的异端者(维利柯夫斯基,Velikovsky ),他们为最基本的问题而奋斗--地质史是否有方向性;地质变化是缓慢稳定的,还是迅速剧烈的;用生命的历史如何标定地质的历史?我在板块构造学和大陆漂移的“新地质学”中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潜在办法。
第六部分试图管中窥豹。我谈到一个简单的原则,物体的大
小影响物体的形状;并且认为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到极其广泛的发
展现象中,包括行星表面的进化,脊椎动物的脑,以及中世纪小
教堂与大教堂之间的形状差别。
第七部分由于顺序的不连贯会使一些读者惊异。我费力地将一般原理和特定的应用联系起来,再将这些原理与生命和地球的主要图景联系起来。这里我讨论了进化思想的历史。尤其是社会、政治观念对所谓“客观”科学的影响。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客观”科学不仅是一种科学自大的表现,而且带有政治意图。科学通过收集客观信息,通过摧毁古老的迷信而成立,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必然通向真理。科学家象普通人一样,在他们的理论中无意中反映了他们时代的社会和政治局限。他们作为社会的特权成员,通常要捍卫现存的社会等级,并将这种等级关系看作生物学上预定的。我叙述了其中的一般情况,通过讨论18 世纪有关胚胎学的一个不太明晰的争论,通过讨论恩格斯关于人类进化的观点,通过讨论Lombroso 关于固有犯罪,以及通过讨论来自科学种族主义根源的曲折故事。
最后一部分探讨了同样的主题,只不过将这个主题联系到当代关于“人性”的讨论中,这是错误使用进化论影响社会政策的一个主要例子。第一小部分批评了作为政治偏见的生物学决定论,有人根据这种理论提出我们的祖先是残忍的猿,人类的攻击性和侵占性是固有的,女性的被动是自然的表现,智商具有种族差别等,这些观点最近又泛滥了。我认为没有证据支持这些观点,而且这些观点所代表的是西方历史上长期悲凉的故事在最近的具体反映--指责牺牲者并给他们标上生物学上劣等的标记,或像孔多塞(Condorcet)所为,用“生物学作为同谋”。我既欣喜又不悦地讨论了最近新生的“社会生物学”研究及其新的预示,即对人性的达尔文主义的解释。我认为社会生物学的许多特定观点
都是基于决定论模式的缺乏支持的猜想,然而我却在社会生物学对利他主义的达尔文主义解释中发现了很大的价值,作为对我不同的倾向性的支持,我倾向认为,遗传给了我们易变性,自然选择并不决定严格的社会结构。
这些文章最初发表在《自然史杂志》专栏中,现在的改动不大,订正了一些错误,删掉了狭隘之见,并且使用了最新的信息。我攻击过论文集中吓人的东西--冗长,但是我的编辑裁刀面对任何单篇文章的内在连贯时,我又退缩了。至少我决没有两次使用同一引文。最后对主编Alan Ternes 和Gordon Beckhorn 致以谢忱和感激。他们接二连三的活泼书信支持了我,并且用留情的编辑之手最恰当地表达了他们的宽容和谨慎。我为所有真正动人的题目而感谢Blame Alan,特别是第十五篇文章的S 形曲线的骗局。
西格蒙特 .弗洛依德像其他人一样出色地表达了进化对人类生活和思想的深刻影响,他写道:
“在过去的时间里,科学之手对于人类朴实的自恋有过两次重大的打击,第一次是认识到我们的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大的难以想象的世界体系中的尘埃......第二次是生物学的研究剥夺了为人类特创的特殊优越性,将人类废黜为动物的后裔。”
我认为这种废黜的知识也是我们在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上对连续性的最大希望。或许“这种生命观”在它的第二个百年还能绽开鲜花,并帮助我们全面理解科学知识的限度和教益,而我们则像哈代诗中的田野和树木一样,继续惊奇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
1.达尔文的拖延
--------------
没有什么事比一些名人行为中长期而难以理解的停滞更能引发猜测的。罗西尼因《威廉.退尔》而达到他歌剧事业辉煌的颠峰,可是之后三十年他几乎什么也没写。多萝西. 塞耶斯在名望达到顶点时却背弃了彼得.温姆西勋爵,转而相信上帝。查尔斯.达尔文在1838 年就得出了全新的进化理论,然而过了21 年,由于R.华莱士的突然出现,才发表他的观点。
通过五年在贝格尔号上对自然的接触,达尔文的物种固定不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1837 年7 月,他航海回来后不久,便开始记第一本关于“递变”(transmutation)的笔记。这时达尔文已经确信进化的发生,他正在寻找一种理论来解释进化的机制,经过最初的猜想和少数不成功的假说,他在阅读一些显然不相关的书籍做消遣时,建立了他的中心思想。达尔文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1838 年的10 月,我为了消遣,偶尔翻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已经有了一定的准备,可以正确认识生存斗争。我马上联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变异会趋向于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淘汰,这一结果将导致新物种的形成。”
达尔文早就认识到动物驯养者所做的人工选择的重要性。但是直到马尔萨斯的斗争与拥挤的观点凝练他的思想之后,他才确定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动因。倘若所有生物产生的后代远比生存下来的要多,那么根据简单的假设,一般说,生存下来的更能适应当时的生活环境,从而自然选择指导了进化。
达尔文知道得出的是什么理论。我们不能将他的拖延归因为没有认识到他的成就的重要性。在1842 年,后来在1844 年,他写出了他的理论及其含义的基本纲要。他还给妻子作了认真的交代,假如他生前不能完成他的主要著作,希望她发表这些手稿。
他为什么等了20 年才发表自己的理论?我们今天的生活步伐的确极大地加快了,在交谈技巧和棒球比赛中,迟缓者必然成为牺牲品。所以,我们可能把过去正常的时期错误地看作漫长的阶段。然而,人的生命周期却是恒定的衡量尺度,20 年仍然是一个人正常事业的一半时间,纵然按照悠然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看,那也是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
通常的科学传记是有关伟大思想家的明显错误信息的根源。这类传记将伟大思想家描述成简单、理性的机器,是仅凭不停的努力,不受其它事情的影响,严格按照客观材料觅寻真理的人。因此,对于达尔文等了二十年的通常解释就是他的工作没有完成。他满意自己的理论,但理论是廉价的。他的理论只有等到汇集大量的支持材料才能发表。这需要时间。
但是达尔文在这二十年的活动所显示的情况,无疑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尤其是他花了整整8 年时间写了一部关于藤壶分类和自然史的四卷本专著。面对这一事实,传统的解释软弱无力,好像是达尔文感到在宣称物种如何改变之前不得不彻底地了解物种;而他只能通过对一个复杂的生物类群进行分类才能彻底地了解物种。但不能耗费8 年的时间,而且不能是在已经得出生物学史上最革命的观点的时候。达尔文本人在自传中这样评价他的四卷本著作:
“除了发现几个奇特的新类型以外,我搞清了各部分的同源......而且我证明在几个属中微小的雄体附着及寄生在雌雄同体的个体内
......虽然这样,我仍然怀疑,这项工作值得耗费那么多时间吗?”
导致达尔文推迟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做简单的解释,但是我感到有一件事情是确信的:恐惧的负面作用与增加材料的正面需要至少同样重要。然而,达尔文恐惧什么?
达尔文得出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时,才29 岁。他没有专业地位,只是因为在贝格尔号上的出色工作而博得同行们的赞赏。他不可能通
过宣扬他所不能证明的一种异端学说来危及自己有前景的事业。
然而他的异端学说是什么?信奉进化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部分;因为,在19 世纪中叶,与当时的流行观点 相比,进化并不是陌生的异端学说。确实有很多人公开而广泛地反对进化,但至少很多著名的博物学家承认或多或少地考虑过进化。
达尔文早年不寻常的笔记中可能含有问题的答案。这些所谓M笔记和N笔记写于1838 年和1839 年,当时达尔文正在作有关递变的笔记,这一笔记是他1842 年和1844 年纲要的基础,其中含有他有关哲学、美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思想。达尔文1856 年重读这些笔记时,称之“充满了有关道德的形而上学”。这些笔记中包含了他所赞同但却害怕发表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远比进化本身更要异端: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即认为物质是所有存在的原料,所有心智及精神的现象都是物质的副产物。没有哪种观点比认为心灵--无论多么复杂和有力--只不过是大脑的产物。更能动摇西方思想中最深刻的传统了。例如,注意一下约翰 .弥尔顿关于心灵与曾寄居的身体分离而比身体优越的观点:
呵,让我的灯火
在午夜时分的孤塔上闪烁,
这样,好让我时时看到那只熊;
与超凡的赫尔墨斯一道,或
借助柏拉图的精神,
去揭示世界和广袤地域的所有
已被丢弃的不死的心灵
她在那个人的身上存活。
这些笔记证明了达尔文的哲学兴趣并且认识到其中的含义。他知道他的理论与其他进化学说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中彻底的唯物论。其他
进化论者谈的是活力的力量,历史具有方向性,活力驱动,以及心灵本质上是崇高的,这些都是经过装饰可以被传统基督教勉强接受的概念。这样基督教中的上帝可以通过进化而不是特创来起作用。而达尔文谈的只是随机变异和自然选择。
达尔文在笔记中将唯物论彻底地应用到所有的生命现象中,包括他称为“要塞本身”(the citadel itself )的人类的心灵。如果心
灵离开大脑就不存在的话,那么上帝岂不过是虚幻发明出的一种虚幻?他在一本关于递变的笔记本中写道:
“爱上帝是有机构造的效果。噢,唯物主义者!为什么认为思想是大脑中的隐密比认为是物质万有引力的特性更美好呢?这是我们的一种自傲。是我们的孤芳自赏。”
这一信念太异端了,达尔文甚至在《物种起源》(1859)中将这一信念搁置一边,只是隐约提到“人类的起源和他的历史,将得到阐
明。”只有当他不能再隐瞒下去了,他才在《人类的由来》(Descentof Man)(1871)和《人类及动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1872)中表达了自己的一部分信念。而自然选择的共同发现者A.R.华莱士绝不会将这一信念应用到人类心灵的研究中,他将人类的心灵看作生命史中唯一的神的贡献。而达尔文在M 笔记本中最著名的断语则与两千年来的哲学与宗教决裂了:
“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说,我们想象的概念来自预先存在的灵魂,而不是来自经验--然而预先存在的是猴子。”
格鲁伯在为M 笔记和N 笔记所做的注解中指出,唯物论“当时远比进化更有毁灭性”。他列举了18 世纪晚期对持唯物论信念的人的迫害,并得出结论:
“在所有的知识领域都施加了压力,讲演被禁止,专职工作被禁止。出版物中充斥了(对唯物论的)谩骂和嘲讽。学者和科学家了解
这一点,而且感觉到了压力。有些人公开放弃了这一罕见的观点,有些人匿名发表文章,有些人以模棱两可的形式发表见解,而许多人则拖了很多年才发表著作。”
1827 年,当达尔文还是爱丁堡大学的学生时,就直接经历着这样的事情。他的朋友W.A.布朗在普林尼学会宣读了一篇带有唯物论观点的论生命和心灵的文章。经过多次争论,所有文章中对布朗的论文的引述,以及含有布朗打算提交文章的(以前会议的)记录,都被删除得一干二净。达尔文对这些颇为了解,他在M 笔记本中写道:
“为了避免走得太远,我虽然相信唯物论,但只能说感情、本能和天才的程度是遗传的,因为孩子的脑和双亲的脑类似。”
19 世纪最热心的唯物论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认识到达尔文的成就,并探讨了其中基本的内涵。1869 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的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
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传说,说马克思向达尔文题赠了《资本论》第二卷,(而达尔文拒绝了),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马克思与达尔文通过信,而且马克思对达尔文予以很高的评价。(我在唐恩Down House的达尔文故居中看到过达尔文收藏的《资本论》。马克思在上面提到他是达尔文“真诚的钦慕者”。书页并没有裁开。达尔文的德语不太好。)
达尔文确实进行了一场温和的革命。不仅在于他这么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还在于他故意避开公众对他理论中哲学含义的注意。他在1880 年写道:
“我认为(正确或错误地)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对公众不会有什么影响;而伴随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会更好地促进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科学之内。”
然而他的工作内涵与传统的西方思想是极大的断裂,我们很难将其纳入这种传统中,例如阿瑟.柯依斯勒之所以反对达尔文, 也是基于不愿意接受达尔文的唯物论,而且他还热衷于认为生命物质中含有特殊性(见《机器中的幽灵》和《产婆蛙案件》)。我承认对此我不太明白。疑惑和知识都应该坚持。我们难道因为自然中的和谐不是设计的就会降低对自然美的赞赏吗?难道因为有数百亿神经元在我们的颅骨内,我们心灵的潜力就激发不了敬畏和恐惧吗?
------------------------------------------------
2.达尔文在船上位置的变换,或五年伴在船长的餐桌旁
------------------------------------------------
格罗得.马克思总是用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取悦观众,如:“谁埋在格兰特墓里 ?”但是越是明白的问题通常就越有欺骗性。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对于谁设想出门罗主义的正确答案应该是约翰.昆西.亚当斯。当问到“谁是贝格尔号上的博物学家?”绝大多数生物学家会回答:“查尔斯.达尔文”。然而他们可能都错了。我们还是不要故弄玄虚吧。达尔文是在贝格尔号上,而且他关注的是博物学。但他之所以来到船上,是为了其他目的,而船上的医生罗伯特.迈考密克最初是正式的博物学家。这里面有一个故事, 并非是对学术史的挑剔注解,而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人类学家J.W.格鲁伯1969年在《不列颠科学史杂志》上发表的“谁是贝格尔号上的博物学家?”一文报道了有关的证据。1975 年,科学史家 H.L.伯斯坦试图解答由此产生的一个明显问题:假如达尔文不是贝格尔号上的博物学家,那他为什么在船上?
没有文献特地证实迈考密克是正式的博物学家,但有关的依据太明确了。当时的不列颠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医生兼任博物学家的传统,而且迈考密克受过这方面的专门教育。他虽然不出色,但还是称职的博物学家,并且在其他的航行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包括定位南磁极的罗斯号南极探测(1839--1843)。同时,格鲁伯发现了一封爱丁堡博物学家罗伯特.詹姆森写给“我亲爱的先生”的信,信中尽是建议贝格尔号的博物学家如何收集和保存样品。依照传统的观念,无疑只有达尔文才是这封信的接受者。幸运的是,受信人的姓名还在原来的信上,信是写给迈考密克的。
直说了吧,达尔文是作为船长费茨罗伊的伴侣随贝格尔号航行的。但是为什么不列颠的船长要带上一位一个月前才见过面的男子作为五年航行的伴侣呢?是19 世纪30 年代海军航行的两个特点使费茨罗伊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首先,航行持续很久,离口岸的时间很长,并且不易收到亲友的来信。其次(对于我们注重心理启发的世纪来说这一点显得很奇怪),不列颠海军的传统表明,船长与下级官兵没有什么社会接触。他通常独自进餐,与官员的会面主要是商讨船上的事宜,并且要以非常正式和正确的方式进行。
费茨罗伊偕达尔文航行时才有26 岁。他知道作为船长长期不能与人接触带来的心理伤害。贝格尔号的前任船长出海后三年,于1828 年在南半球病倒,并且自杀了。而且,正如达尔文在写给姐姐的信中证实的那样,费茨罗伊担心他那心理错乱的“遗传秉性”。他那著名的叔父卡斯尔雷子爵,1822 年割断了自己的喉管。实际上,费茨罗伊曾病倒过,并且暂时让出贝格尔号的的指挥权,当时达尔文在瓦尔帕莱索也病倒了。
费茨罗伊因为与船上其他人很少接触,他只能通过为自己安排一名“编外”的乘客来进行人际交往。但是海军部禁止携带私人乘客,甚至船长的妻子;没有明确目的的绅士伴侣也不许带。费茨罗伊已经带了一些编外乘客,一名工匠,一名仪器制造者及其他的人。但是他们都不能成为费茨罗伊的伴侣,因为他们不属于上流社会阶层。费茨罗伊是个贵族,他将祖先直接上溯到国王查理二世。只有绅士才能与他共餐,达尔文恰好是一位绅士。
但是费茨罗伊怎样能吸引一位绅士结伴进行5 年的航行呢? 只有提供别处无法提供的正当的实践机会方可。还有什么比博物学家更好呢?--虽然贝格尔号上已经有了一位正式的博物学家了。所以费茨罗伊在他的贵族朋友中招徕一位绅士博物学家。诚如伯斯坦所说,这是“一个解释他的客人存在的客气说辞,而一个有魅力的工作足以吸引一位绅士在船上呆很长时间。”达尔文的导师J.S.亨斯罗非常理解这一点。他在给达尔文的信中写道:“费茨罗伊船长需要一名男子,(我理解)主要是做伴侣,而不仅仅是采集者。”达尔文和费茨罗伊相见了,他们相处甚安,一拍即合。达尔文以费茨罗伊的伴侣身份出航了,在5 年的航行期间,主要与他进餐。另外费茨罗伊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试图在探险航行期间通过确立出色的标准来留下他的印记(达尔文写道:“这次探测的目的。是完成对帕塔哥尼亚和火地岛的勘查,,探测智利、秘鲁及其他太平洋群岛的海岸,并携带经纬测量仪环绕世界”)。费茨罗伊自己掏钱多带了一些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从而利用自己的财富和优越条
件达到了目的。一位“编外”博物学家正好符合费茨罗伊的提高贝尔格号科学声望的计划。
可怜的迈考密克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最初他和达尔文还能合作。但他们最终还是各自为政了。达尔文优势占尽,他受船长的宠幸,他有仆人,船停泊后,他有钱游历海岸,还能雇佣当地的采集者。而迈考密克只能呆在船上,还要恪守公职。达尔文个人的努力,超过了迈考密克正式的采集,而迈考密克则在不满中决定打道回府。1832 年4 月,他在里约热内卢“一病不起”,被送上返回英国的海军泰恩号回家。达尔文通晓婉转的表达方式,在写给姐姐的信
中谈到迈考密克“一蹶不振,是与船长有分歧,没有什么大的不适。”
达尔文并不在乎迈考密克的科学能力。 1832 年5 月,他在给亨斯罗的信中写道:“他是位落伍的哲学家,在圣亚斯,他自己说用了两个星期作基本的记述,而以后只采集特殊的材料。”事实上达尔文根本就看不起迈考密克:“我那位医生朋友是头蠢驴,我们的交往极为客套;现在他烦恼的是自己的舱顶究竟漆上浅灰色还是纯白色。从他那里我所能听到的只是这类话题。”
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了科学史的研究应该考虑社会等级的重要性。如果当时达尔文是商人的儿子而不是富有的医生的儿子,现在的生命科学将会有很大的不同。达尔文的富有使他可以毫无负担地自由从事研究。他由于糟糕的健康状况一般每天只能进行2 至3 小时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再去谋生的话,他大概完全不能从事研究工作了。现在我们又知道达尔文的社会地位在他的事业转折点上也起到过关键的作用。费茨罗伊更感兴趣的是就餐伙伴的社会荣耀,而不是他的博物学能力。
达尔文与费茨罗伊之间那些没有记载的就餐对话有可能隐藏了更深刻的东西吗?科学家有一个很强的偏见,将创造性的思想仅归因于经验依据。因此,在达尔文世界观的转化方面,海龟和鸣雀被看作最主要的动因,因为他参加贝格尔号航行时只不过是个天真朴实的神学学生,但是他回来后一年便开始记述有关递变的笔记。我猜想费茨罗伊本人可能曾是重要的催化者。
至少达尔文与费茨罗伊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不过由于绅士的友善和前维多利亚时期对情感的压抑等限制,使两个人以恰当的方式相处。费茨罗伊是位地道而热情的托利党成员,达尔文对辉格党也同样忠诚。达尔文小心翼翼地避免与费茨罗伊讨论当时下院正在审议的著名改革法案。费茨罗伊曾告诉达尔文,他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奴隶制的仁慈。巴西的一位最大的奴隶主曾招集他的奴隶,问他们
是否愿意获得自由,他们一致回答,“不”。当达尔文直率地表示怀疑这个在主人压力下回答的价值时,费茨罗伊恼怒了,他告诉达尔文,任何怀疑他的话的人都不配与他共餐。达尔文离开了船长,而与船员共餐,但费茨罗伊几天之后做出让步,并向达尔文正式表达了歉意。
我们知道达尔文面对费茨罗伊的顽固观念敢于挑战。但他是费茨罗伊的客人,而且,在特定的环境下,他是服从的; 因为在费茨罗伊时代,在海上,船长是无可争议的绝对君主。达尔文不能表达他的不满。所以5 年期间,一位最出色的人在任何留下的历史记录中保持着沉默。后来,达尔文在《自传》中回忆起“与一位船长和睦相处的困难,由于所有的人敌意地对待他,如同他敌意地对待其他人,
由于他所拥有的令人敬畏---或至少在我整个航行期间所具有的令人
敬畏,而极大地增加了。”
这时费茨罗伊的意识形态中不仅有托利党的政治,还有宗教。有时费茨罗伊也怀疑《圣经》句句真实,但他倾向将摩西看作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而且他消耗了许多时间计算挪亚方舟的大小。费茨罗伊的固定观点,至少在他生命的晚期,是“来自设计的观点”,即相信上帝的仁慈(实际上是上帝的真实存在)可以从生命结构的完整性中推导出来。而达尔文虽然也接受了完美构造的观点,却提出了自然的解释,这和费茨罗伊的信念不太矛盾。达尔文还提出了基于偶然变异和外在环境作用的自然选择进化理论---一种严格的唯物论( 同时基本上是无神论)的进化理论。19 世纪许多其他的进化理论更符合费茨罗伊的基督教类型。例如,宗教领袖们对于达尔文的坚定的机械论观点厌烦得很,而对于一般提出生命固有完美倾向的观点则好得多。
达尔文得出的哲学观点部分是由于费茨罗伊教条地坚持来自设计观点的一种反应吗?我们没有证据表明达尔文在随贝格尔号航行时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对基督教的怀疑和否定是以后的事情。航行过半时,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经常设想将来去干什么;我当然愿意做一个乡间牧师了。”他甚至与费茨罗伊合作了一篇题为“塔希提的道德状况”的文章,以期唤起对在太平洋传教工作的支持。但是怀疑的种子一定在贝格尔号航行的寂静时光中萌发滋长。设想一下达尔文的境况吧。他5 年来每一天都与一位无法与之争辩的、威严的船长共餐,这位船长的政治观点和对其他事物的态度和达尔文迥然不同。而且达尔文基本不喜欢这个人。谁知道5 年来连续的高谈阔论会使“寂静的练金术”如何冶炼达尔文的大脑呢,至少就激发达尔文确立哲学和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基石而言,费茨罗伊可能远比鸣雀重要。
费茨罗伊至少在生命的晚期,曾因内疚而烦恼。他开始认为是自己引发了达尔文的异端思想(事实上,我猜想从实际情况的角度看,可能远比费茨罗伊设想的更真实)。他有一种炽热的赎罪欲望,并开始重新维护《圣经》的权威性。在1860 年著名的不列颠协会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赫胥黎嘲笑了“油腔滑调的山姆”威尔伯弗斯),失态的费茨罗伊大步走向台去,高举《圣经》,大声叫道:“这本书,这
本书”。五年之后,他割断了自己的喉管。
-------------------------------
3.达尔文的难题:进化的艰苦历程
-------------------------------
作为一个概念,对进化的理解已经耗尽了上千位科学家一生 的时光。在这篇文章中,我谈论一个比较狭窄而有趣的小问题:理解进化这个词本身。我将追溯生物变化如何被称作进化(evolutio)。作为一次好古的纯粹词源探索,这个故事复杂而令人激动。但是太认真就危险了,因为正是这个词过去的用法致使外行们经常且依然普遍地误解了科学家们所讲的进化。
先从一个矛盾的地方开始吧。达尔文、拉马克和海克尔这些19 世纪英国、法国和德国最伟大的进化论者,在他们最初的著作中都没有使用进化这个词。达尔文使用的是“带有饰变的由来”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拉马克使用的是“转形” (transformisme ),海克尔则受用“递变理论” (Transmutations—Theorie )或“由来理论”(Descendenz—Theorie )。他们为什么不使用“进化”?而且他们的生物理论如何有了现在的名称?
出于两个原因,达尔文在陈述自己的理论时不使用进化一词。首先,在他那个时代,“进化”在生物学中已经有了特定的含义。事实上,“进化”被用来描述一种可能与达尔文的生物发展理论不太相同的胚胎学理论。
1744 年.德国生物学家阿尔布莱克·冯·哈勒(Albrechtvon Haller )发明了“进化”一词,用在他的胚胎由卵或精子中预先存在的微小个体发育而来的理论中(今天可能感到奇怪,这种理论认为,以后的世代发生都是在夏娃的子宫和亚当的睾丸中创生的,封存的像俄罗斯套娃,一个套一个,每一个夏娃的卵中有一个胎儿,而每一个胎儿的卵中还有一个更小的胎儿,等等)。这种进化(或预成)理论遭到渐成论者的反对,他们相信成体的复杂性来自最初无形的卵(有关这场争论的详细说明见文章25)。哈勒选择词藻时非常小心,因为拉丁文evolver①的含义是“展示”;的确(按照预成论),小胎儿从最初的肢体紧封中展示出来,并且在以后的胚胎发育中只增加体积。
而哈勒的胚胎进化似乎是达尔文的带有饰变的由来理论的阻碍。假如人类的全部历史预先存在于夏娃的子宫中,那么自然选择(或其他的作用力)怎么能改变我们预定好的寄居在地球上的历程?
我们似乎更迷惑了。哈勒的词汇怎么能变成意义几乎完全相反的用法?只有当哈勒的理论在1859 年前已行将就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随着理论的让位,哈勒用过的这个词方可用于其他的目的。
根据达尔文的描述看看,“进化”,即“带有饰变的由来”,并非从以前的专业词汇中借来的,相反,它来自本国语。在达尔文时代,进化已经成为一个常用的英语词汇,其含义与哈勒的专业用法不同。《牛津英语词典》将这个词追溯到1647 年H ·摩尔 (H. More)的诗句“外形的进化(展示)弥漫于世界广布的灵魂中”。但是这种“展示”的含义与哈勒的展示含义不同,它指的是“表现出一个事件序列中的规则顺序”,更重要的是,它含有进步发展的概念。《牛津英语词典》中继续写道。“发展的过程是从萌芽状态到成熟或完整的阶段”。因此,在英语中,进化与进步的概念紧密相联。
达尔文正是按照本国语的含义使用了进化一词,事实上,他是在书的最后才用这个词的:
认为生命及其若干能力原来是被注入到少数类型或一个类型中的,而且认为在这个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最美丽的和最奇异的类型从如此简单的始端,过去,曾经而且还在进化着;这种生命观是极其壮丽的。②
达尔文在这一段中选择了[进化]这个词是因为他要以生物发展的变迁与诸如万有引力这类物理定律的固定不变作比较。但是他很少使用这个词,因为达尔文显然否认当时公众使用的带有进步观点的我们称作进化的这个词。
在一个著名的警句中,达尔文提醒自己在描述生物的结构时绝不说“高等”或“低等”——因为假如一个阿米巴可以很好地适应它所生活的环境,就像我们适应我们的生活环境一样,谁又能说我们是高等的生物呢?所以达尔文不用进化一词描述他的带有饰变的由来理论,既因为这个词的专业含义与他的信念不同,又因为他不满意这个英语术语中所带的必然进步含义。
通过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这位勤奋的、在任何方面都很博学的维多利亚时期人物的倡导,“进化”才作为“带有饰变的由来”的同义词进入英语中。在斯宾塞看来,进化是涵盖所有发展的定律。而且,对于一位洋洋自得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人来说,除了进化,还有什么能主导宇宙的发展过程呢?因此,斯宾塞在1862 年的《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中给这个宇宙定律下了一个定义:“进化是物质及其消耗运动的整合,其中物质从不确定的、不一致的同质体变成确定一致的异质体。”
斯宾塞的工作在两个方面对于确立进化的现代含义做出了贡献。首先,斯宾塞在写作那部流行的《生物学原理》(1864——1867)中,一直使用“进化”来描述生物界的变化。其次,他不是将进步看作物质内在的能力,而是看作内部作用力和外部(环境)作用力“合作”的结果。这种观点非常符合19 世纪大多数生物进化的观点,因为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家很容易将生物的变化等同于生物的进步。当许多科学家感到需要一个比达尔文的“带有饰变的由来”更简明的词汇时,“进化”便被派上了用场。而且因为多数进化论者都将生物的变化视为趋向复杂性增加的过程 (即直达我们人类的过程),所以他们对于斯宾塞的概括性词汇的认识并没有破坏斯宾塞的进化定义。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进化论之父似乎在独自坚持生物的变化只能导致提高生物更适应所生活的环境,而不导致由结构复杂性或异质性的提高来界定的抽象、理想的进步——绝不说高等和低等。假如我们留意达尔文的警训,我们便会谅解今天科学家与普通人之间存在的许多迷惑和误解。因为在那些早就抛弃进化与进步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并将其视为最糟糕的人类中心说偏见的科学家中间,达尔文的观点已经取得了胜利。而许多普通人依然将进化等同于进步,并且将人类的进化不止是看作变化,而且看作智力提高,等级提高,或还有其他一些假设改善的标准。
现在比较广泛传播的反进化论文献,耶和华见证会③的小册子“人类来到这里是通过进化还是通过创生?”中宣称,“用最简明的话说,进化指的就是生命从单细胞生物,经过数百万年,以一系列生物变化的方式,进化到生命的最高状态——人类,仅仅是生物基本类型的变化不能被视为进化。”
这种错误地将生物进化等同于进步的观念,一直有着不幸的后果。历史上,它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滥用(达尔文本人有一点这种思想),这种臭名昭著的理论根据假设的进化程度排列人类种群与文化,并将(毋庸惊讶)白种欧洲人排在顶端,而将他们征服的殖民地排在底端。今天,这种思想仍然是致使我们在地球上傲慢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相信,我们控制着居住在我们星球上几百万的其他物种,而不是与它们平等相处。进化一词的变更情况已经讲明白了,然而却不能为之做些什么。我当然也非常抱歉,科学家们挑选一个含有进步意思的本国语词汇,来指称达尔文的虽然不太悦耳但却准确得多的“带有饰变的由来”时,确实存在着基本的误解。
①在德文、英文、法文中,进化为“evolution”。——译 注
②译文引自周建人、叶笃庄、方宗国译,叶笃庄修订《物种起源》(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5 年,第557 页,略有改动。—译注。
③19 世纪后期由查尔斯·T ·拉塞尔在美国创立的一个基督教派,认为“世界末日”在即、主张个人与上帝感应交流。——译注
----------------------------
4 .对达尔文理论的过早埋葬
---------------------------
在众多的电影《圣诞颂歌》(christmas Carol)①版本中,其中的一个有这样的场面,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要拜访一位要死的伙伴雅各布·马雷(Jacob Marley )时,看到一位尊贵的绅士坐在楼梯上喘息。斯克鲁奇问道:“你是医生吗?”“不,”这个人答道,“我是殡仪经办人,我与医生从事的是竞争性的行业”。知识分子残酷的世界肯定是竞争很激烈的。宣称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的死亡是引人注意的事件。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一直是要被埋葬的候选者。最近,汤姆·贝瑟尔(Tom Bethell )在一篇题为“达尔文的错误”(《哈泼斯》杂志,Harpers,1976 年2 月号)的文章中还提到“我相信,达尔文的理论正处在垮台的边缘,,,许多年前,甚至最热心的支持者,都在静悄悄地抛弃自然选择。”对我来说,这真是新闻;而且我虽然以作为达尔文主义者而骄傲,但我却不是自然选择最热心的捍卫者。我想起马克·吐温(Mark Twain)对预先发表的讣告所做的著名答复:“有关我死的报道太夸大其辞了”。
贝瑟尔的论据对于许多从事实际研究的科学家来说,是个奇特的警告。我们已经有准备看到在新材料的影响下一个理论的衰亡,但是我们不希望一个伟大而有影响的理论因系统陈述中的错误而垮台。几乎所有经验性的科学家都比较实在。科学家愿将学院哲学作为空洞的探讨而弃之不用。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可以直接凭直觉来思想。贝瑟尔并没有提供足以埋葬自然选择的材料,只引用了达尔文推论中的一个错误:“达尔文犯了一个动摇他的理论的严重错误。而这个错误最近才被认识到,,正是在这一点上,达尔文误入歧途。”
虽然我打算否定贝瑟尔的观点,我还是为科学家不愿认真探求论据的结构而感到惋惜。正如贝瑟尔所称,进化论的变化并不大。许多著名的理论都是由含糊的隐喻和类比联系起来的。贝瑟尔正确地发现了环绕进化论的废话。但是我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贝瑟尔看来,达尔文理论的核心已经腐坏,我却发现其中富含宝藏。
自然选择是达尔文理论的中心概念——最适者生存下来并将其优良的特性传播到整个群体中。自然选择是用斯宾塞的话“最适者生存”定义的。但这句著名术语的真正含义又是什么呢?谁是最适者?最适者是怎样确定的?我们通常看到的关于适应度的陈述无非是“差异的生殖成功”,即比起群体中其他的竞争成员来,生殖出更多的可以生存下去的后代。哇! 贝瑟尔像以前的许多人一样,该大叫了。这个系统陈述只从生存的角度来定义适应度。自然选择的关键句子的含义不过是“那些生存下来的生存”’——一句空洞的同语重复。[同语重复是这样的句子,如 “我父亲是个男人”,其中宾语(一个男人)不含任何信息,也不紧扣主语(我父亲)。同语重复比较容易确定,而它不是可以检验的科学陈述,即定义中陈述的句子不含可以检验的真实内容。]
但是达尔文怎么能犯这么一个重大而低级的错误呢?即使对他批评最严厉的人也没有指责过他愚钝。显然,达尔文必定尝试过另外的途径来确定适应度的差异,即不仅依据生存来作适应度的标准。达尔文提出过一个独立的标准,但贝瑟尔正确地指出达尔文是按照类比建立这个标准的,这真是一个危险不可靠的策略。人们可能以为像《物种起源》这样一部革命性的书籍的第一章可能涉及的是宇宙问题和一般性的论述。但不是。第一章谈的是鸽子。达尔文用了最初50 页的大部分篇幅论述动物驯化者保持优良品性的“人工选择”。他在这里确实在使用一种独立的标准。养鸽者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最适者并不是从生存的角度确定的。最适者之所以可以生存,是因为它们具备了所需的特性。
自然选择的原则建立在与人工选择类比的正确性上。我们必须像养鸽者那样能预先确定最适者。而不是根据以后的生存来确定。但是大自然不是动物驯化者,没有预定的目的来调节生命的历史。在自然界,生存者所具备的特性必然被视为“比较进化的”;在人工选择中,在驯化开始前,“优良”的特性便已经确定了。贝瑟尔认为,后来的进化论者认识到达尔文类比的失败,并重新将“适应度”仅仅定义为生存下来。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动摇了达尔文中心设想的逻辑结构。大自然没有提供适应度的独立标准,所以,自然选择是同语反复。
随即,贝瑟尔提到从他的主要论据中得出的两个重要推论。首先,假如适应度指的是生存,那么自然选择怎么能成为达尔文宣称的“创造性”力量。自然选择只能告诉我们“一个给定动物类型”如何“成为数量多的”类型;利用自然选择不能解释“一种动物类型如何逐渐变成另一种类型”。为什么达尔文及其他一些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人物那样确信无意识的自然可以与驯化者有意识的选择相比,贝瑟尔认为,工业革命成功的资本主义文化氛围,已经将任何变化确定为内在的进步。在自然中仅仅生存下来可能就是好的:“那么人们便开始看到,达尔文真正发现的只不过是维多利亚时期人们信奉进步的倾向而已。”
我相信达尔文是对的,而贝瑟尔及其同僚是错的:独立于生存的适应度标准可以用于自然界,而且进化论者一直这样用着。但是我首先承认贝瑟尔的批评可以针对进化论的许多专业文献中,特别是将进化视为数量变化而非性质变化的抽象的数量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只是从差异生存的角度确定适应度,探讨只存在于计算机磁带中的假设群体基因A 与B 相对成功的抽象模型有何用处?然而,大自然是不受理论遗传学家的计算限制的。在自然界中,A优越B 将通过差异生存来表达,但并不是由差异生存来确定,或至少不要这样去确定,免的让贝瑟尔等人获胜,达尔文失败。
我对达尔文的维护并不惊人、新奇,也不深刻,我只是认为达尔文以动物驯化类比自然选择是有道理的。在人工选择中。驯化者的欲念代表了群体的“环境变化”。在这样的新环境中。有些特性是优越的;(它们生存下来并通过我们驯化者的挑选传播开来;但这是适应度的结果,而不是对适应度的确定)。在自然界中,达尔文式的进化也是对变化环境的反应。这里,关键在于,一定的形态、生理和行为的特性,像是设计好了的生活在新环境中,所以将是优越的。这些特性,从工程师出色设计的标准角度看,而不是从生存下来及传播的经验事实角度看,具有了适应度。多毛的哺乳类动物进化出绒毛外表之前天气已经冷了。
为什么这个问题引起进化论者这么激烈的争论呢?还好,达尔文是正确的;生物在变化的环境中具有优越的构造及功能是适应度的独立标准。然而为什么有人认真地认为糟糕的构造与功能会取胜呢?是的,实际上许多人提出过。在达尔文时代,许多竞争的进化论主张最适者(具有最出色的构造与功能)必然被抛弃。曾经使用过我现在办公室的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阿尔丰斯·海亚特提出过族的生命周期观点,在当时很流行。海亚特宣称,进化的谱系像个体一样,具有青年、成熟期、老年和死亡(灭绝)的周期。衰落和灭绝是预定的。正是成熟导致衰老,构造及功能尚佳的个体死去,而脆弱谱系中迟钝、松垮的生物取而代之。另外一个反进化的观点直生论提出,一定的趋向,一旦产生,就不会
停止,由于构造与功能愈加成为劣势,所以必然导致灭绝。许多 (也许是绝大多数)19 世纪进化论者认为,爱尔兰麋鹿的灭绝是因为角无法停止进化的增长(见文章9),所以它们死掉,碰到树干或陷入泥潭。同样,剑齿“虎”的死亡通常被认为是由于犬齿过长,以致这种可怜的猫不能张开颌使用犬齿。
因此,并非贝瑟尔所称,生存下来的生物所具有的特性就是构造及功能更适应的。“最适者生存”并不是一个同语重复。这句话不仅仅是对进化记录的想像或理性的阐释。这句话是可以检验的。这句话胜过那种无法就生命性质的对立依据和不同态度间做出的权衡。这句话可以超越它本身字面上的局限。
如果我是对的,贝瑟尔又怎能声称“我认为,达尔文正处在被抛弃的过程中,或许是出于对这个可敬的老绅士的尊重,所以他依然安卧在西敏士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 )的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的旁边。正在做的只是慎重而温和地使他消逝。”他提到的“牛虻”有C ·H ·沃丁顿(C. H.Waddington)和H ·J ·穆勒,好像他们是观念一致的缩影。他从未提到我们这一代著名的选择论者,例如E ·O ·威尔逊(E.O.Wilson)或D ·詹曾(D.Janzen )。而且他引述新达尔文主义的奠基者杜布赞斯基(Dobzhansky)、辛普森(Simpson)、迈尔(Mayr)和J ·赫胥黎(J .Huxley)时,只是嘲讽他们关于自然选择是“创造力”的隐喻。(我并不是在宣称因为达尔文主义依然有声望所以才坚持它;我也是一只牛虻,相信没有批评的观念一致的确是风暴将至的信号。我仅仅是在报道,无论那是更好还是更糟,达尔文主义依然活着,而且还很兴旺,尽管贝瑟尔埋葬了它。)
但是为什么自然选择被杜布赞斯基比作作曲家,被辛普森比作诗人,被迈尔比作雕刻师,以及被朱利安·赫肯黎比作芸芸众生的莎士比亚?我不想为这些比喻的挑选作辩护。但是我愿支持这种倾向,即说明达尔文主义的本质就是自然选择具有创造性。就我所知,所有反达尔文理论都攻击自然选择。自然选择被视作如同刽子手一样的否定作用,是不适者的屠夫(而按照这样的非达尔文主义机制,适应的产生是由于获得性遗传或环境直接引入有利变异)。达尔文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其中宣扬的自然选择创造了适应。变异普遍存在,方向上是随机的。变异只提供原材料,是自然选择指导了进化变化的过程。自然选择保存了有利的变异,并逐渐形成适应度。事实上,就像艺术家从笔记、词汇和石头的原料中形成他们的创造,关于自然选择的隐喻并非不恰当。贝瑟尔由于没有接受独立于生存的适应度标准,所以他很难承认自然选择具有创造作用。
按照贝瑟尔的看法。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具有创造力的概念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社会及政治激发出的幻想。在英帝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乐观主义形成中,变化被视为内在的进步;为什么自然界中的生存不能等同于不是同语重复意义上而是更佳结构和功能意义上的更高适应度呢。
我竭力主张一个普遍性的论点,科学探讨出的“真理”通常是当时流行的社会及政治信念激发出的偏见。我曾就这个问题写过几篇文章,因为我认为通过揭示科学实践与人类所有的创造性活动相似,从而有助于揭开科学实践的神秘面纱。但是一般论点的真理,并不说明在任何特定的应用中都是正确的,而且我坚持认为贝瑟尔的应用就是一种极为错误的误用。
达尔文分别做过两件事情:他使科学界相信进化的发生,并且提出自然选择的理论作为进化的机制。我情愿承认大家都将进化等同于进步,从而使达尔文的同代人感到他的第一种观点悦耳一些。但是达尔文终其一生都未使人们信服他的第二项探讨。直到20 世纪4O 年代,自然选择理论才取得胜利。依我看,自然选择理论之所以没有在维多利亚时代被广泛接受,主要是这个理论否认在进化作用的内部存在一般的进步。自然选择是(生物)局部地适应变化环境的理论。自然选择理论没有提出更完美原则,不
保证一般性的改善;简而言之,没有提供理由来认可那种赞同自
然界存在固有进步的政治气氛。
达尔文独立的适应标准就是“改善的结构与功能”,但并不是当时英国人赞成的宇宙意义上的“改善”。对于达尔文来说,改善只意味着“面对直接的局部环境具备更好的结构与功能”。局部环境不断的变化:或冷或热,或干或湿,或成草原或成森林。自然选择导致的进化就是通过差异性地保持生物更佳的结构与功能,从而跟上环境的变化,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任何宇宙意义上看,哺乳动物的毛发都不是进步。自然选择可能产生了一种趋势,诱导我们设想更一般意义上的进步——脑容积的增加成了不同哺乳动物种群进化的标志(见文章23)。但是大的脑容在局部环境中才有用途;并不存在向着更大状态变化的内在趋向。而且达尔文还曾得意地表明,局部适应经常产生出结构与功能的“退化”,例如寄生动物解剖结构上的简单化。
如果自然选择不是进步的理论,那么它的声望便不是对贝瑟尔所说的政治见解的反映。我坚持认为,或许天真了些,自然选择理论现在有增无减的声望,必定与它成功的解释了我们所拥有的公认不太完备的关于进化的信息有关。我甚至猜想,查尔斯,达尔文还会伴随我们一些时光。
================================
《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2
=================================
2.达尔文在船上位置的变换,或五年伴在船长的餐桌旁
-----------------------------------------------------
格罗得.马克思总是用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取悦观众,如:“谁埋在格兰特墓里 ?”但是越是明白的问题通常就越有欺骗性。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对于谁设想出门罗主义的正确答案应该是约翰.昆西.亚当斯。当问到“谁是贝格尔号上的博物学家?”绝大多数生物学家会回答:“查尔斯.达尔文”。然而他们可能都错了。我们还是不要故弄玄虚吧。 达尔文是在贝格尔号上,而且他关注的是博物学。但他之所以来到船上,是为了其他目的, 而船上的医生罗伯特.迈考密克最初是正式的博物学家。这里面有一个故事, 并非是对学术史的挑剔注解,而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人类学家J.W.格鲁伯1969年在《不列颠科学史杂志》上发表的“谁是贝格尔号上的博物学家?”一文报道了有关的证据。1975年,科学史家 H.L.伯斯坦试图解答由此产生的一个明显问题: 假如达尔文不是贝格尔号上的博物学家,那他为什么在船上?
没有文献特地证实迈考密克是正式的博物学家,但有关的依据太明确了。当时的不列颠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医生兼任博物学家的传统,而且迈考密克受过这方面的专门教育。他虽然不出色,但还是称职的博物学家,并且在其他的航行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包括定位南磁极的罗斯南极探测(1839--1843)。同时,格鲁伯发现了一封爱丁堡博物学家罗伯特.詹姆森写给“我亲爱的先生”的信,信中尽是建议贝格尔号的博物学家如何收集和保存样品。依照传统的观念,无疑只有达尔文才是这封信的接受者。幸运的是,受信人的姓名还在原来的信上,信是写给迈考密克的。
直说了吧,达尔文是作为船长费茨罗伊的伴侣随贝格尔号航行的。但是为什么不列颠的船长要带上一位一个月前才见过面的男子作为五年航行的伴侣呢?是19世纪30年代海军航行的两个特点使费茨罗伊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首先,航行持续很久,离口岸的时间很长,并且不易收到亲友的来信。其次(对于我们注重心理启发的世纪来说这一点显得很奇怪),不列颠海军的传统表明,船长与下级官兵没有什么社会接触。他通常独自进餐,与官员的会面主要是商讨船上的事宜,并且要以非常正式和正确的方式进行。
费茨罗伊偕达尔文航行时才有26岁。他知道作为船长长期不能与人接触带来的心理伤害。贝格尔号的前任船长出海后三年,于1828年在南半球病倒,并且自杀了。而且,正如达尔文在写给姐姐的 信中证实的那样,费茨罗伊担心他那心理错乱的“遗传秉性”。他那著名的叔父卡斯尔雷子爵,1822年割断了自己的喉管。实际上,费茨罗伊曾病倒过,并且暂时让出贝格尔号的的指挥权,当时达尔文在瓦尔帕莱索也病倒了。
费茨罗伊因为与船上其他人很少接触,他只能通过为自己安排一名“编外”的乘客来进行人际交往。但是海军部禁止携带私人乘客,甚至船长的妻子;没有明确目的的绅士伴侣也不许带。费茨罗伊已经带了一些编外乘客,一名工匠,一名仪器制造者及其他的人。但是他们都不能成为费茨罗伊的伴侣,因为他们不属于上流社会阶层。费茨罗伊是个贵族,他将祖先直接上溯到国王查理二世。只有绅士才能与他共餐,达尔文恰好是一位绅士。
但是费茨罗伊怎样能吸引一位绅士结伴进行5年的航行呢? 只有提供别处无法提供的正当的实践机会方可。还有什么比博物学家更好呢?--虽然贝格尔号上已经有了一位正式的博物学家了。所以费茨罗伊在他的贵族朋友中招徕一位绅士博物学家。诚如伯斯坦所说,这是“一个解释他的客人存在的客气说辞,而一个有魅力的工作足以吸引一位绅士在船上呆很长时间。”达尔文的导师J.S.亨斯罗非常理解这一点。他在给达尔文的信中写道:“费茨罗伊船长需要一名男子,(我理解)主要是做伴侣,而不仅仅是采集者。”达尔文和费茨罗伊相见了,他们相处甚安,一拍即合。达尔文以费茨罗伊的伴侣身份出航了, 在5年的航行期间,主要与他进餐。另外费茨罗伊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试图在探险航行期间通过确立出色的标准来留下他的印记(达尔文写道:“这次探测的目的。是完成对帕塔哥尼亚和火地岛的勘查……探测智利、秘鲁及其他太平洋群岛的海岸,并携带经纬测量仪环绕世界”)。费茨罗伊自己掏钱多带了一些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从而利用自己的财富和优越条
件达到了目的。一位“编外”博物学家正好符合费茨罗伊的提高贝尔格号科学声望的计划。
可怜的迈考密克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最初他和达尔文还能合作。但他们最终还是各自为政了。达尔文优势占尽,他受船长的宠幸,他有仆人,船停泊后,他有钱游历海岸,还能雇佣当地的采集者。而迈考密克只能呆在船上,还要恪守公职。达尔文个人的努力,超过了迈考密克正式的采集,而迈考密克则在不满中决定打道回府。1832年4月,他在里约热内卢“一病不起”, 被送上返回英国的海军泰恩号回家。达尔文通晓婉转的表达方式,在写给姐姐的信中谈到迈考密克“一蹶不振,是与船长有分歧,没有什么大的不适。”
达尔文并不在乎迈考密克的科学能力。 1832年5月,他在给亨斯罗的信中写道:“他是位落伍的哲学家,在圣亚斯,他自己说用了两个星期作基本的记述,而以后只采集特殊的材料。”事实上达尔文根本就看不起迈考密克:“我那位医生朋友是头蠢驴,我们的交往极为客套;现在他烦恼的是自己的舱顶究竟漆上浅灰色还是纯白色。从他那里我所能听到的只是这类话题。”
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了科学史的研究应该考虑社会等级的重要性。如果当时达尔文是商人的儿子而不是富有的医生的儿子,现在的生命科学将会有很大的不同。达尔文的富有使他可以毫无负担地自由从事研究。他由于糟糕的健康状况一般每天只能进行2至3小时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再去谋生的话,他大概完全不能从事研究工作了。现在我们又知道达尔文的社会地位在他的事业转折点上也起到过关键的作用。费茨罗伊更感兴趣的是就餐伙伴的社会荣耀,而不是他的博物学能力。
达尔文与费茨罗伊之间那些没有记载的就餐对话有可能隐藏了更深刻的东西吗?科学家有一个很强的偏见,将创造性的思想仅归因于经验依据。因此,在达尔文世界观的转化方面,海龟和鸣雀被看作最主要的动因,因为他参加贝格尔号航行时只不过是个天真朴实的神学学生,但是他回来后一年便开始记述有关递变的笔记。我猜想费茨罗伊本人可能曾是重要的催化者。
至少达尔文与费茨罗伊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不过由于绅士的友善和前维多利亚时期对情感的压抑等限制,使两个人以恰当的方式相处。费茨罗伊是位地道而热情的托利党成员,达尔文对辉格党也同样忠诚。达尔文小心翼翼地避免与费茨罗伊讨论当时下院正在审议的著名改革法案。费茨罗伊曾告诉达尔文,他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奴隶制的仁慈。巴西的一位最大的奴隶主曾招集他的奴隶,问他们是否愿意获得自由,他们一致回答,“不”。当达尔文直率地表示怀疑这个在主人压力下回答的价值时,费茨罗伊恼怒了,他告诉达尔文,任何怀疑他的话的人都不配与他共餐。达尔文离开了船长,而与船员共餐,但费茨罗伊几天之后做出让步,并向达尔文正式表达了歉意。
我们知道达尔文面对费茨罗伊的顽固观念敢于挑战。但他是费茨罗伊的客人,而且,在特定的环境下,他是服从的; 因为在费茨罗伊时代,在海上,船长是无可争议的绝对君主。 达尔文不能表达他的不满。所以5年期间,一位最出色的人在任何留下的历史记录中保持着沉默。后来,达尔文在《自传》中回忆起“ 与一位船长和睦相处的困难,由于所有的人敌意地对待他,如同他敌意地对待其他人,由于他所拥有的令人敬畏---或至少在我整个航行期间所具有的令人敬畏,而极大地增加了。”
这时费茨罗伊的意识形态中不仅有托利党的政治,还有宗教。有时费茨罗伊也怀疑《圣经》句句真实,但他倾向将摩西看作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而且他消耗了许多时间计算挪亚方舟的大小。费茨罗伊的固定观点,至少在他生命的晚期,是“来自设计的观点”,即相信上帝的仁慈(实际上是上帝的真实存在)可以从生命结构的完整性中推导出来。而达尔文虽然也接受了完美构造的观点,却提出了自然的解释,这和费茨罗伊的信念不太矛盾。达尔文还提出了基于偶然变异和外在环境作用的自然选择进化理论---一种严格的唯物论( 同时基本上是无神论)的进化理论。19世纪许多其他的进化理论更符合费茨罗伊的基督教类型。例如,宗教领袖们对于达尔文的坚定的机械论观点厌烦得很,而对于一般提出生命固有完美倾向的观点则好得多。
达尔文得出的哲学观点部分是由于费茨罗伊教条地坚持来自设计观点的一种反应吗?我们没有证据表明达尔文在随贝格尔号航行时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对基督教的怀疑和否定是以后的事情。航行过半时,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经常设想将来去干什么;我当然愿意做一个乡间牧师了。”他甚至与费茨罗伊合作了一篇题为“塔希提的道德状况”的文章,以期唤起对在太平洋传教工作的支持。但是怀疑的种子一定在贝格尔号航行的寂静时光中萌发滋长。设想一下达尔文的境况吧。 他5年来每一天都与一位无法与之争辩的、威严的船长共餐,这位船长的政治观点和对其他事物的态度和达尔文迥然不同。而且达尔文基本不喜欢这个人。 谁知道5年来连续的高谈阔论会使“寂静的练金术”如何冶炼达尔文的大脑呢,至少就激发达尔文确立哲学和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基石而言,费茨罗伊可能远比鸣雀重要。
费茨罗伊至少在生命的晚期,曾因内疚而烦恼。他开始认为是自己引发了达尔文的异端思想(事实上,我猜想从实际情况的角度看,可能远比费茨罗伊设想的更真实)。他有一种炽热的赎罪欲望,并开始重新维护《圣经》的权威性。在1860年著名的不列颠协会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赫胥黎嘲笑了“油腔滑调的山姆”威尔伯弗斯),失态的费茨罗伊大步走向台去,高举《圣经》,大声叫道:“这本书,这本书”。五年之后,他割断了自己的喉管。
①原著为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译注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