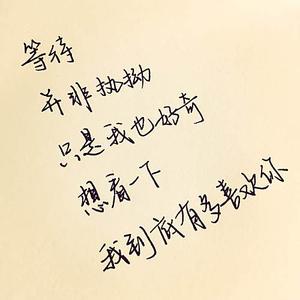一
草坪上,几个小孩在玩水。
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挽着裤管。后来,裤脚湿了,裤子湿了,上衣湿了。再后来,鼻翼上是水,耳垂上是水,发梢上是水,浑身上下,都是水。
这是初秋的下午,天已经凉了。水玩过,几个孩子又在玩“骑马打仗”的游戏。两两配对,骑在“马”上的孩子,与另一个骑在 “马”上的孩子,在“马”的跑动中,以脚角力,互相蹬踏。一两个回合,三五个趔趄,七八声嬉笑,个个便摔翻在地上。再起来,身上,泥一片,水一片,伤一块,痛一块,然后,闹一声,嚷一声,继续玩。
一个人,若没有从这样的童年走过来,一定不是从诗意中长大的。
二
有一年,大雪,到山上去追野兔子。

四野尽白。深可没膝的雪,覆了远山近水。四下里,好多野兔的足印,仿佛它们的挣扎和喘息还在,我们说,赶紧追!
追了半天,又冷又累又饿。我们四处找柴火。树上的枯枝,沟洞里的树叶,崖缝间的鸟窝,田鼠洞里的豆荚,统统搜罗了来,扒开一片雪,然后,点起了火。雪,以及寒冷,纷纷从火堆四周撤退。而我们,在温暖里,一边烤着火,一边烤着干粮,一边大声说笑,一边高声放歌。空旷的四野里,鸟都不敢飞过来,哪还有野兔子的踪影。
那一次,我们一个兔子没逮着。心底里,却捡拾回来无穷的快乐。
三
我有一个朋友,是位画家。
有一天,他邀我到郊外,干什么?看蚂蚁。他在一只肥硕的蚂蚁屁股上,轻点一丝朱红。整个上午,我们盯着这只红屁股的家伙,一会儿拖回一只空壳的麦芒,一会儿在巴掌大的地方逡巡一阵子,一会儿对着一根高挑的草疑神疑鬼,一会儿优雅地为另一只蚂蚁让路,一会儿又急匆匆地去打上一架。
我们两个人,仿佛是被它牵着,一会儿驻足在这一处,一会儿又蹲踞在另一处,一会儿手舞足蹈,一会儿又凝神屏息。我们看它,它一定也好奇地打量着我们两个傻傻的家伙。
被盯梢终究是郁闷的。那天,它突然钻进窝里,半天没出来。我们的心,在等待中,竟好像也被困在了幽深的地底,半天,没上来。赏玩一只蚂蚁,与被一只蚂蚁捉弄,都是一种欢喜。
四
大冬天,街上冷得难见一个人。到水果摊前买水果。不见摊主。只见旁边一个女人,上身是红红的羽绒服,下身是过膝的皮裙,高筒的靴子,背对着我,一边哼唱着,一边和着旋律,正翩翩独舞呢。
这么冷的天,真好兴致。
大姐,这儿的摊主呢?我问。她一转身。我便有些羞赧。看起来,人家好像比我都岁数小。然而,更令我吃惊的是,她朝我走过来,说,你买水果啊,我就是。
啊,你是摊主……我没有掩饰住自己的惊讶。嗯,我就是。然后,她熟练地为我称水果。这时候,我注意到她水果车上的标牌。天哪,她竟然出生在1961年。不是大姐,是大姨!
一个人的年轻,其实,应该是心境里不灭的诗意,以及,内在生命不尽的激情吧。
五
与人对酌,喝着喝着,人走了。开始还茶烟缭绕。后来,烟萎了,水凉了,气氛没了,心绪乱了。
此时,一朵白白的云飘过来,投在不知哪里的玻璃幕墙上,又反射落到杯子里。一刹那,杯里也有了大乾坤,一朵云,在杯中荡呢。赶紧再续一杯开水,云在水里,水在云里,云水升腾在茶烟里。轻啜一口,然后,小心翼翼放下,喜对一朵云,相看两不厌。
酌,与一朵云相对,多美多好的意境啊。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