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玄奘的后半生,是从势能高地走低的过程。
2、“偷渡客”的身份之所以没被追究,一是玄奘彼时处于势能高地,二是太宗自信包容的姿态,三是新生的系统需要“名士”提高势能。
3、玄奘势能的走低,是与旧系统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新系统局势没有明朗的情况下贴近某一集团。
取经归来:政治漩涡中的晚年玄奘
文/林 勇
又一次历经了一年多的九死一生,再次翻越过雄伟的葱岭群峰,贞观十八年(644年),玄奘终于抵达了丝路上的重镇-----于阗(今新疆和田)。魂牵梦萦近二十载的东土故乡,已经出现在并不遥远的天际,然而45岁的玄奘还是选择在于阗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比近乡情怯更重要的,是大师需要在这里处理几件更加紧迫的事情。
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决自己二十年来的“偷渡客”这个身份问题。众所周知,为了寻求真经,当年玄奘不顾禁令,毅然选择了非法偷渡这个不得已的方式离开了故国,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但这仍然是自己归国之前不得不要考虑再三的现实问题。玄奘委托一位前往长安的高昌商人,给大唐有关方面带去了一封亲笔信,信中玄奘坦率地承认过去的确是“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但也着重讲述了这些年里自己身在异国所从事的艰辛事业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如今“无任延仰之至”,内心已经迫不及待地希望能够重回祖国的怀抱。
在耐心等待了七八个月之后,长安的使者终于来到于阗,出乎玄奘意料的是,他等来的竟然是大唐天子李世民的敕令,在文书中,一代英主非但没有追究历史问题,而是充满着热情洋溢的期待,“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大唐正百废俱兴万象更新,正需要你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参与到祖国的建设事业当中,快快归国与我相见!
得到大唐天子的诚挚召唤,玄奘当然马不停蹄向着故国飞奔而去。
奠定事业基础的洛阳接见
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抵达长安西郊。此时唐太宗并不在长安城内,而是已经亲率大军北去讨伐高丽,正驻扎在洛阳,但是在出征之前,太宗已经交代了留守长安的宰相房玄龄,待玄奘归国之日该以何种规格接待,并且要求尽快安排玄奘前往前方军营,太宗需要亲自见到这位大师。得知玄奘已经到达城外的消息,房玄龄赶忙通知官员先将玄奘安置在西郊一宿,因为第二日官方将要举行欢迎大师归国的盛大入城仪式。
有大师从西天而来的消息已经于民间不胫而走,长安百姓纷纷自发上街观望,“自然奔凑,观礼盈衢,更相登践,欲进不得”,长安沸腾,人群拥挤,几乎发生严重踩踏事件。在房玄龄亲自主持、百官全体出席之下,二十五日,载誉归来的玄奘进入了当时的世界之都-长安城。次日,官方又在朱雀大街举办大型展览会,公开展示玄奘带回来的六百五十七部经书和一百五十粒如来佛肉舍利,长安城再次陷入癫狂之中。然而此时,饱经了风沙洗礼和佛学浸润的玄奘,倒是出奇的平静,在弘福寺中“独守馆宇,坐镇清闲”,他在静静地等待着接下来的人生。
短暂休整之后,二月一日,玄奘再次动身东去,前往洛阳接受天子的接见。和小说或者影视剧中那些唐僧的形象完全不同,海归的中年玄奘内外兼修,极具个人魅力,这在与唐太宗的洛阳初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让阅人无数的大唐天子也是一见倾心。太宗对身边的人称赞说,“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竣,非唯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非但不比传说中的那些古代贤人差,简直要超越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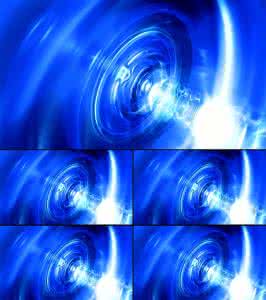
得到天子的赏识,自然是令人振奋之事,但是太宗接下来的几项请求却着实让玄奘大为吃惊。太宗先是征求玄奘意见,是否愿意还俗跟随自己当首席顾问,辅佐天子治理天下,这当然超出了玄奘可以接受的范围,玄奘的回答也堪称得体、精彩,“玄奘少践淄门,服膺佛道,孔教未闻”,我从小入佛门求佛理,对于治理国家所需要的那些儒家学问,实在是才疏学浅,完全不能胜任当您顾问的工作,并且还作了一个比喻,“无异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陆,不唯无功,亦徒令腐败也”,就像把水里的船搬到岸上当车使,这是个双败的选择。太宗还是舍不得这样的杰出人才,又提出希望玄奘可以跟随自己一起去出征高丽,以便随时交谈畅快讨论,玄奘仍旧加以礼貌地回拒。
唐太宗毕竟是英明天子而不是霸道总裁,绝不强大师所难,而是高度尊重大师的自我选择。在理解了玄奘的译经弘愿之后,就将当时长安的皇家寺院弘福寺作为将来的译经场所,并且在经费、人员、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做了妥善的安排。洛阳会见,无论对于太宗还是玄奘,都是一次相当成功和愉快的体验,双方坦诚交流、互相尊重。三月初,玄奘回到长安,五月就正式投入了后人所熟知的宏大译经工作之中。
在贞观君臣间建立的深厚人脉
翻译经书探究佛理,可以说是玄奘毕生的心愿最高的理想,前半生千里迢迢万里跋涉,都是为了后半生的这项工作做的艰苦付出和扎实铺垫。从贞观十九年起,一切条件都已经具备,玄奘全身心地将人生的重心放置于这项伟大的事业之中。译经事业的巨大成功,奠定了玄奘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之所以能完成这一前无古人的伟业,前期的长期积累和玄奘的个人努力、坚持以及天赋,当然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也绝对不能忽视当时整个外部环境给予译经工作的广泛支持,能争取到这样的良好外界环境,同样和玄奘的苦心经营分不开。
这种支持首先就是来自天子唐太宗,这是最关键的因素,也是玄奘归国后立刻赶往洛阳面奉天颜的原因。凭借着过人魅力和执着理念,玄奘很快就取得了太宗的信任,并建立了良好私人关系。洛阳会见“谈叙真俗,无爽帝旨”,双方话题广泛,兴趣投机,无所不谈,太宗十分认同大师的译经宏愿,并明确表示译经方面的一切需要由国家支付,有任何困难找房玄龄解决,用我们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佛经翻译”被列为“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这也一举提升了海归玄奘在当时朝野之间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从而获得崇高的社会声誉。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六月,正在陕北行宫玉华宫(今陕西宜君县内)避暑的唐太宗,邀请玄奘前来面见。玄奘还在路上,太宗就几次命人传令,请玄奘不必赶路,注意保重身体,十分关切。二人相见,玄奘呈上新译的《瑜伽师地论》,太宗观后大为欣赏,并当即下令由国家出钱把《瑜伽师地论》分抄九份,发往全国重要寺庙保存,供人阅览传抄。玄奘也适时请求太宗作序,太宗欣然答应,亲自撰写了著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并下旨这篇序放置于所有汉译佛经之首。同年长安慈恩寺落成,玄奘被任命为第一任住持,译经场所迁往更为宏大的慈恩寺,十二月,太宗专门派政府高级官员以九部乐的最高礼仪欢迎玄奘入驻慈恩寺,并亲自带领太子及众臣在皇城安福门恭送。
不但得到当朝天子的尊重和大力支持,玄奘与各级官员也建立起了良好的公私关系。大唐宰相房玄龄由于直接分管保障译经的工作,当然与玄奘之间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同时房玄龄也格外敬重法师的学养和人品,于公于私都是玄奘的最佳搭档。同样,太宗身边的几位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等人,也是玄奘的大力支持者和崇拜者,在将《大唐三藏圣教序》颁布全国时,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都上书颂扬太宗德化与护持三宝,同时称赞玄奘西行求法和翻译之精,更以佛教徒的身份欢欣庆幸。除了中央高级官员,地方官员进京也纷纷争相求见玄奘,比如永徽二年,玄奘就亲自主持了瀛洲刺史、蒲州刺史、穀州刺史和恒州刺史四名官员的受菩萨戒仪式,几日后四人各舍钱财,并修书感谢玄奘的授予戒法。
在君臣朝野之间,玄奘都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声誉和威望,这对他的译经工作可谓是百利而无一弊。同时,除了君臣,我们还应该注意另一个地位特殊之人,也就是未来的君主、如今的太子李治。由于一场内部变故,原本排名靠后的晋王李治于贞观十七年被立为太子。受父亲和家庭影响,尽管个人比较偏好炼丹求仙的道教,但是在大多数场合李治也表现出对于佛教的尊重,同时对玄奘也格外敬重。长安慈恩寺就是李治为了纪念生母长孙皇后所创建,建成之后又迎请玄奘主持,在慈恩寺落成度僧日,官方活动结束之际,太子李治还携太子妃亲自登门至玄奘法师房,并作诗贴于房门。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十五日,唐太宗又邀请玄奘入宫,两人继续讨论佛法和印度见闻。五月,在一次谈话过程中,太宗突感身体不适需要休养,将玄奘留于宫中,希望在康复以后能够继续两人之间的叙谈。不料,太宗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于当月二十三日病逝于翠微宫,这期间玄奘始终陪伴在太宗身边。太宗的离世,对于玄奘是个重大打击,不但失去的是一位自己的重要支持者,更是一位能够深入交流的有缘人。
政坛上的一场狂风暴雨
出世的玄奘,其人生旨趣全然都集中在佛法学理之上,对于世俗权力几乎没有任何野心,但大师同时又是一名对俗世有着融通智慧之人,当然明白应该如何维持友善的人际关系和营建的良好工作氛围。能理解接纳自己的太宗虽然离去了,但是无论是新君高宗李治还是朝堂上的一班有着深厚旧谊的老臣,仍旧能够继续执行资助译经工作的原有政策,永徽初年,玄奘更加专心于自己的译经,“自此以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
就在玄奘埋首于佛典经书之中时,一场空前的政治角力却正在迅速弥漫开来。还是受到太多民间文艺作品的影响,后人往往将贞观之后的这场政治斗争,统统都归结到武则天的“女皇梦”之上,而忽视了高宗李治这个人以及当时政治权力结构之中的先天内在不稳定元素。
我们知道,太宗的三位嫡子: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原本李治是最没有接班可能,然而李承乾和李泰之间的一场兄弟相争,使得他们两败俱伤双双出局,李治却渔翁得利。李治能胜出的一个条件,就是年纪轻排名后,还没有来得及形成私人小集团,这个条件对于李治能当上太子很重要,但是缺少自己的干部队伍,对于将来当天子却又成了不利因素,加之太宗早就意识到李治性格偏于柔弱,所以在晚年,太宗就着手组建了一个未来的辅政团队,这个团队以长孙无忌为首,包括长孙的心腹褚遂良、太子的老师于志宁以及老资格军队将领李勣,这几位对于太宗当然都是忠心耿耿、政治过硬,特别长孙无忌还是李治的亲舅舅,太宗希望这样一个团队能够继续真心诚意地辅佐自己的儿子当好天子。
高宗李治刚上台的永徽初年,一切大权都还掌控在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手中,权力二元结构隐藏着巨大的内在危机,而高宗日益年长成熟,政治自主意识逐渐增强,长孙却并没有任何还政放权的迹象,就这样,危机在一步步走向引爆边缘。
永徽五年(654年),高宗又一次向五品以上高级干部表达了自己的不满“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以前先帝的时候,我看你们一个个能说会道,政治气氛很是活跃,为什么今日大家都不说话了,难道到我这就没话说了吗?想必在表达这番不满的时候,高宗已经能够意识到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沉闷局面,根源在于下面众臣个个都清楚,掌权的不是您年轻的皇帝,而是长孙大人,谁知道哪句话该说还是不该说、说轻了还是说重了。
辅政的长孙无忌以及他那个旧臣集团已经成为横亘在君主与众臣之间的一道巨大障碍,而此时正享受着大权独揽的长孙无忌也没有任何收手的意思,一个天子无论如何“昏懦”,这都是很不愉快的感受,都是要试图打破的僵局,但是永徽初年高宗所能利用的政治资源的确非常稀少,只能等待。
直到高宗的老相好、正在感业寺里当尼姑的武媚娘再度出现,高宗终于等来了自己的好帮手,夫妇两个联手,以废立皇后为名,展开了对于旧臣集团的坚决出击,这是我们在武则天的故事中都十分熟知的了。永徽六年(655年),王皇后遭废,武昭仪如愿成了武皇后,王皇后身后的旧臣集团遭受重创。从实质上来说,“废王立武”事件就是高宗李治,通过老婆武则天将权力从旧臣集团手上抢夺到自己手上,当然后来这权力又意外地落入武则天之手,这只能说是最初大家都没有意料到的一个事情发展方向,无论武则天是否出现,高宗与旧臣集团之间的冲突都很难避免。
突如其来的“吕才事件”
以玄奘的敏感和洞悉能力,当然应该能够感知到朝堂上的这股强劲风暴,但是自己只是专心学问从未染指权力之争,只要谨慎行事,即使长年河边走或许也能侥幸鞋不湿。然而政坛漩涡的巨大威力,还是在永徽六年将玄奘和他的译经事业拖下了水。
就在“废王立武”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大家刺刀见红的时候,当年五月,一本名为《因明注解立破义图》的三卷本著作横空出世,作者是尚药奉御吕才。尚药奉御是五品职官,专门负责管理宫内的医药,还要替皇帝皇后亲自品尝各种药材,这位吕才之前名不见经传。在书中(原书已佚,该书序保留在《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吕才说自己从玄奘几个弟子那里得到了他们翻译出来的《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本》,在看了这两本译本之后,吕才认为其中的义疏错误很多,他一共收集了四十余处互相矛盾之处,全部罗列出来,以供批判。
如果说仅是对于翻译质量进行商榷,那么还都是在学术争论范围之内,尽管在这之前连这样对于玄奘的学术质疑都很少见,然而吕才接下来的言论就相当不客气了,以大字报的语气对玄奘展开了指名道姓的攻击,“法师等若能忘孤鬼之微陋,思句味之可尊,择善而从,不简真俗,此则如来之道不堕于地,弘之者众,何常之有?必以心未忘于人我,义不察于是非,才亦扣其两端,犹拟质之三藏”,你们如果态度严谨一点又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错误之处呢,特别是作为项目负责人,玄奘大师竟然能允许这样的低级失误出现于其中,很不能理解,说明你们的水平也不怎么样,以至于让“如来之道”“堕于地”。如同在舆论界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吕才的著作立刻引发巨大反响,“媒衒公卿之前,嚣喧闾巷之侧”。
这一场从天而降的风波,应该是玄奘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特别是这位吕才的身份,作为一名在宫中可以和天子皇后近距离接触的服侍官员,外人无法确知他写作这篇质疑文章的真实用意以及更深的背景,就像一千三百年后同样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上海小官僚,出手就是一篇打着学术批判的名义的论新编历史剧的论文,却隐藏着深不可测的政治目的。面对汹汹舆论,玄奘一方最初选择了沉默应对,不做任何回应,或许他们希望这个时候朝廷上的高级官员或者是天子本人出面平息这场来势凶猛的攻击。
然而出自朝廷的援手始终未能来到,玄奘所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任由事态发展的话,搞不好自己会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那样一来未完成的译经大业将半途而废。七月玄奘弟子、慈恩寺译经僧之一的慧立“闻而愍之,因致书左仆射燕国于公”,实在看不下去了,直接写信给燕国公、左仆射于志宁,希望于老能出来说句公道话。可以相信慧立的这封求救信是出自玄奘本人的授意,而燕国公于志宁则是李治为太子时候的老师,也是几位地位崇高的顾命老臣之一,与玄奘有着长年的深厚交谊,但是和其他几位老臣相同,在“废王立武”事件上,于志宁站在了王皇后一边,属于高宗武则天夫妇的对立面。
收信后,于志宁出面将这一事件当朝提出,以自己的威望和资历暂时压制了吕才等人的持续挑衅,但是风波仍未得到彻底平息。到了十月,太常博士柳宣又致书译经团队,让他们对于吕才的质疑给予正面回应,不要默不作声或者去寻求朝廷大臣的背后支援。收到柳宣之信三天之后,玄奘弟子明叡终于以个人名义作出答复,回信中指出了吕才的学术错误,并且明确宣示吕才来者不善动机不纯。又三天之后,柳宣把明叡的回信拿给吕才过目,这一次吕才依旧不依不饶,直接上奏高宗。十一月,高宗下令吕才前往慈恩寺与众译经僧人直接辩论,而由于志宁、杜正伦等人组成观察团,监督辩论。面对吕才有限的佛学和语言知识,早就称雄于印度各大辩论赛的玄奘,赢得毫无悬念,吕才很快败下阵来,“词屈谢而退焉”。
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吕才事件”终算是告一段落,但是玄奘当然知道自己绝不是最终获胜者,无论吕才发难的动机和背景如何,在自己受困无助之时,只能去向旧臣集团的燕国公于志宁求救,仅凭这一点,他就犯了政治大忌,就将会彻底失去高宗和武则天的信赖,玄奘如今已经掉进了一个两难的处境当中。
次年年初,玄奘主动上书高宗,请求朝廷派遣官员监督自己译经。高宗很快回应,下旨以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中书侍郎杜正伦六人组成监督团队,负责对玄奘译经工作的督导,“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这六个人中,于志宁、来济和杜正伦此后都被当作旧臣集团彻底打倒,而许敬宗和李义府则是著名的武则天的政治打手,从这份名单就可以看出这个监督译经的工作组的真实目的。史书上记载,玄奘在接到这份旨令后,“允慰宿心,当对使人悲喜不觉泪流襟袖”,当场就留下了“感动”的热泪。
形同拘禁的东都之行
永徽六年的“吕才事件”对于玄奘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大师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高宗已经不是太宗,自己在高宗的心目中地位也绝不能再和贞观时代相提并论,为了译经事业,自己也需要努力调整与高宗以及武则天之间的相处之道。
显庆元年(656年)十月,武则天即将生产,产前心理波动忐忑不安,请玄奘入宫为之祈福。玄奘十分卖力,并提出如果产下男孩,希望能够让他出家,由自己亲自剃度,高宗欣然答应。十一月初五,皇子李显诞生,到十二月初五皇子满月,一个月之内玄奘连续上书五次,称颂备至。同一时间,玄奘还说在显庆宫发现一只赤雀,天降祥瑞,“赤雀呈符,示周王之庆”,历史上周文王出世的时候也是有赤雀出现。这样的对于皇权的主动示好,在玄奘历来的行事当中相当罕见,也可以看出此时大师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急于调整与皇权之间的关系的紧迫心情。十二月初五,李显满月,玄奘亲自为新生皇子剃度,从此与“佛光王”李显建立了名义上的师徒关系。
显庆二年(657年)二月,高宗、产后的武则天启程移驾洛阳,并带上了新生的“佛光王”李显和他的师父玄奘。这次洛阳之行,一共呆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里,高宗和武则天住在皇城之北的洛阳宫,而玄奘则被安置在了宫城西苑的积翠宫,其间仅在二年十月接玄奘入宫供养三天,以及十二月短期入宫,绝大部分时间则是对玄奘不闻不问。
玄奘老家在今洛阳附近的缑氏县,借此次洛阳之行的机会,玄奘曾返乡祭扫父母之墓,又发现由于年久失修,父母之墓已经坟垄傾毁,玄奘向高宗提出想请假回老家改葬父母,高宗答应,但起初只给了三天假期,这显然太不合理,玄奘只能再次请求,“又婆罗门上客今相随逐,过为率略,恐为耻笑”,我身边好几位来自外国婆罗门的僧人跟随,搞得过于简略的话,恐怕被外宾嗤笑,有损国家颜面。高宗这才批准由国家拨款,为玄奘父母重修坟墓,风光了许多。
九月二十日,玄奘上书,请求高宗允许自己前往洛阳附近的嵩山隐居,安心翻译。然而这个请求却被高宗严厉拒绝,并亲自回信“道德可居,何必太华叠岭;空寂可舍,岂独少室重峦?幸戢来言,务复陈请”,哪里都可以译经,跑去嵩山干什么,这样的请求,以后提都不要提了。看到皇帝反应如此激烈,玄奘赶忙写信道歉,先是说收到高宗的亲笔信如何感动掉泪,并表示以后再“不敢更请”。
不久之后,又因为一件事情,玄奘再次惹怒高宗,被严重警告。显庆二年年底,玄奘“在积翠宫翻译,无时暂缀,积气成疾”,长年艰苦的翻译工作让已经年近六十的玄奘身体患病,然而此时虽然都身在洛阳,但与皇帝分居两处,平时高宗也不闻不问,更没人会去向高宗主动反映玄奘的健康状况,玄奘本人也不好去向皇帝要求派御医给自己治疗。在这种情况之下,病情沉重的玄奘私自离开积翠宫去寻求治疗。玄奘生病没人汇报给高宗,但私自离开驻地的消息却很快就被高宗所掌握,“帝闻之不悦”,立即派人前来调查。玄奘只能又一次去信,详细解释前前后后,说是自己恐有不测死在宫里,玷污了皇家之地,语气相当凄凉。高宗了解到实情之后,接玄奘入皇宫休养几日,又送回了积翠宫。
“吕才事件”过后,玄奘已经完全失去高宗信任,而且很可能被视作是潜在威胁,尽管玄奘试图努力补救这样的紧张关系,但是显然在这方面他很难成功。高宗一年多的东都之行,之所以带上玄奘,看管的意思非常明显,在洛阳,玄奘几乎失去行动自由,形同软禁。
落寞的玉华寺终曲
显庆三年(658年)正月,高宗武则天一行启程返回长安,玄奘同行,但是等回到长安之后,玄奘却没有再回慈恩寺,而是在当年七月被派往新落成的西明寺,原先身边的随侍弟子大多也没有被允许跟随,只有新度的十几名僧人。
而西明寺也只是玄奘的短暂过渡之地,第二年显庆四年(659年),玄奘上《重请入山表》,表中称“今讵不任专译,岂宜滥窃鸿恩,见在翻译等僧,并乞停废”,这几年自己这个翻译团队的成绩很差,没有什么成果,浪费国家经费,请求停止这个项目,队伍解散,而自己则希望能够前往位居陕北偏僻之地的玉华宫居住,“时翻小经,兼得念诵”。玉华宫是从前的行宫所在之地,当年唐太宗曾经迎接玄奘居住于此,在这里有着两人之间美好的往昔时光,由于地处偏远,太宗之后高宗已经不再前往该地,永徽二年下诏“改宫为寺”,玄奘希望能够逃离长安这个政治中心,到安静的玉华寺渡过最后的一段日子。
为什么玄奘会在此时提出迁往玉华宫呢?
其实,只要看一下这一年政坛上的血雨腥风,就能理解法师此时内心的悲凉。这一年,高宗和武则天的政治打手们已经大开杀戒,四月,许敬宗诬长孙无忌谋反,高宗下诏削长孙的太尉之职,流放黔州,同时有人控告于志宁、褚遂良(已死)等人党附长孙无忌,私底下结成反革命集团,于志宁被罢官流放,褚遂良之子也在流放途中被杀。五月,长孙无忌之子被杀于流放途中,七月长孙无忌本人在流放地抑郁症发作,自缢身亡,一场针对前朝老臣的大规模政治清洗席卷政坛。十月,玄奘终于获准离开长安,前往玉华寺。
幸运的是,高宗对玄奘还算是网开一面,这可能是通过这几年的仔细考察,高宗和武则天也的确相信玄奘只是一个纯粹的佛教中人,只专心于自己的学术方面,并未插足任何一方的政治势力,既然自愿前往偏僻,也就不再具有任何政治威胁,而且随着长孙集团的彻底失势,天下大局已定,玄奘还是愿意去翻译经书,那也就不再为难大师了。
从显庆四年(659年)到麟德元年(664年),玄奘在玉华宫度过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五年。值得庆幸的是,尽管远离政治中心,不再有从前的官方提供的各种优越条件,然而在玉华宫却少了太多的尘世纷扰,终于可以安静下来专注于译经,正是在这最后的几年,玄奘完成了他所有译经中部头最大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翻译。
在完成了《大般若经》的翻译之后,65岁的玄奘已经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麟德元年初,玄奘对弟子们说“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经部甚大,没惧不终,人人努力加勤,勿辞劳苦”,这是玄奘一生中头一次讲出这样不自信的话,但也是对子弟们的鞭策、交代。正月初九,在跨越一条小水沟之时,玄奘不慎摔倒,此后就一直卧床休息。二月初五夜半时分,守护身旁的弟子问“和上(尚)决定得生弥勒内众不?”,玄奘淡然回答:“得生”。这是玄奘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两个字。当晚大师圆寂。
二月初三,长安的高宗就已经得知玄奘病重的消息,二月初七,派遣御医赶往玉华寺,但这时玄奘已经在前一日圆寂。消息传来,高宗哀叹“朕失国宝矣”。
玄奘大师圆寂以后,遗体被安置在长安大慈恩寺翻经堂两个多月,直到四月十五日才下葬,虽然有很多道俗百姓前往瞻仰告别,但是却没有任何朝官前去祭奠。身为前朝国师,当朝皇子的僧师,享有崇高社会声誉的一代宗师,高宗竟没有赐予任何谥号与追荣,也没有僧人或者俗人撰写塔铭,相当于今日大人物去世后组织上没有给予任何官方说法,这在当时都显得很不寻常。四月十五日,下葬白鹿原,除了由官方提供经费外,也未见任何官员出席。反倒是在三月初六的时候,高宗就下旨暂停翻译,解散了译经队伍。这种官方的集体失声,或许正是玄奘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玄奘法师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人物之一,他传奇的一生已经被历史永远铭记,但很多时候后人只记得毅然西行求法的那个执着身影,以及载誉归国后长安城满城的鲜花与赞美,只记得慈恩寺大雁塔内的高朋满座宾客如云。在刚回到长安之初,全城沸腾之时,玄奘仍然冷静地独坐于寺内,“独守馆宇,坐镇清闲”,那一刻他一定相信他有掌控自己人生的能力,在唐太宗倾情相邀之时,他也绝无旁骛,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依然自信。只是等到永徽六年之后,一步步恶化的外部环境,可能才使得玄奘意识到身不由己的苦衷,权力场里残酷争斗的险象环生,或许要比那取经路上九九八十一难中的任何一难,都让人更加生出无力之感。
那个陷于困境中而又失去自我掌控能力的玄奘形象,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并不多见,但只有加上这个形象,才是大师完整的一生。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行程……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