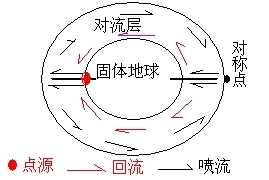年轻时候的阿赫马托娃
(文/吕正惠)
阿赫马托娃(1889~1966)和她的朋友帕斯捷尔纳克(台湾译作巴斯特纳克,1890~1960)、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一起被西方视为苏联时期代表性的诗人。西方评论界在谈论他们时,往往强调他们在苏联体制下如何受到迫害、他们的艺术如何不见容于苏联,似乎他们诗歌的主要价值就在这里。西方的评论未必错,但只强调这一点,实际上严重歪曲了他们的真面目。在读了乌兰汗先生所译的阿赫马托娃诗选(除了本书所收的长诗,还包括她许许多多的短篇抒情诗)之后,我尤其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我相信,阿赫马托娃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她的成就比起同时期的西方著名诗人,如叶慈、梵乐希、里尔克、艾略特等人,恐怕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阿赫马托娃很早就以她的深具贵族气质的情诗,建立起她在俄罗斯诗坛的地位,在很长的时间里,西方评论家也以此作为评价的重点。一直要到一九六〇年代以后,大家才赫然发现,她后期的诗作才是她艺术的高峰。我初读她的《安魂曲》时,完全不能相信,诗可以写得这么简朴、但又这么感人(有一个罪犯写信给阿赫马托娃说,“我被那种能刺伤人的纯朴所震撼”)。试看第二、三两节:
静静的顿河静静地流,
黄色的月亮跨进门楼。
月亮歪戴着帽子一顶,
走进屋来看见一个人影。
这是个女人,身患疾病,
这是个女人,孤苦伶仃。
丈夫在坟里,儿子坐监牢,
请你们都为我祈祷。(第二节)
……
不,这不是我,是另外一人在悲哀。
我做不到这样,至于已经发生的事,
请用黑布把它覆盖,
再有,把灯盏拿开……
夜已到来。(第三节)
第二节以民谣式的曲调表现了深沈的忧伤,第三节却用“黑布覆盖”和“把灯拿开”展现了全然黑暗的世界。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探监的人成了号码(第三百号,见第四节),而“犯人”:
……一张张脸是怎样在消瘦,
恐惧是怎样从眼睑下窥视,

苦难是怎样在脸颊上刻出
一篇篇无情的楔形文字。(尾声)
因此,表面朴实的文字呈现了极为复杂的内涵,从而使人间成为炼狱,这就把人类的某一特殊事件(1938年至1939年斯大林的大清洗)提升为一种人类的象征,曾经受苦难的人在读到这些诗作时,都会深受感动。阿赫马托娃还未定稿时,曾把其中两节读给一个丈夫被逮捕的妇女听,那妇女说,她既觉得自己很幸福,又觉得自己很不幸,并且知道她已得到某种解脱。整组诗就这样的口耳相传,不知为多少人所背诵,用以自我抚慰,就这样一直传播开去,终于在一九六三年,在德国出现了纸面版。阿赫马托娃在题词中说:“我和我的人民共命运,和我的不幸的人民在一处。”《安魂曲》使阿赫马托娃从一个倾诉自我爱情的诗人,完全蜕变成一个“民众的诗人”,成为一个所有受苦受难的人可以在她那里找到抚慰的诗人。
阿赫马托娃的手迹这种诗人角色的转变,是她自我选择的结果。当苏维埃革命发生后,她选择留在国内,而不像她的许多朋友(其中还包括她当时热恋的情人),流亡到西方。为此,她写过好几首诗,其中最早的一首是这样的:
我听到一个声音。他宽慰地把我召唤:
“到这边来吧,”他说,
“放弃你那多灾多难的穷乡僻壤,
永远地离开你的俄国。
我会洗掉你手上的血迹,
清除你心中黑色的耻辱,
我要用新的东西抵消你的委屈
和遭受打击的痛楚。”
可是我淡然地冷漠地
用双手把耳朵堵住,
免得那卑劣的谰言
将我忧伤的心灵玷污。(1917)
一九六五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阿赫马托娃名誉博士,她到英国参加颁赠典礼时,见到她非常喜欢的艾萨克·柏林,她对柏林说:无论有什么在俄国等着她,她都会回去。苏联政体只不过是她的祖国的现行体制。她曾生活于此,也愿长眠于此,作为一个俄国人就应如此。阿赫马托娃一点也不想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不管祖国现在处于什么状况。作为一个俄罗斯人,她只能面对所有俄罗斯人必须面对的命运。她还在另一首诗中说:
我永远怜悯沦落他乡的游子,
他像囚徒,像病夫。
旅人啊,你的路途黑暗茫茫,
异乡的粮食含着艾蒿的苦楚。(1922)
将近四十年后(1960),一个流亡海外的朋友(也可能曾经是她的情人)给她写了一封信,说“这里不需要我们任何人做任何事,道路对外国人来说是封闭的。所有这一切你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了:‘别人的面包发出蒿草的味道’。”第二年,阿赫马托娃写了《故乡的土》这一首诗:
我们不把它珍藏在香囊里佩带在胸前,
我们也不声嘶力竭地为它编写诗篇,
它不扰乱我们心酸的梦境,
我们也不把它看成天国一般。
我们的心里不把它变成
可买可卖的物件,
我们在它身上患病、吃苦、受难,
也从来不把它挂念。
是啊,对于我们来说,它是套鞋上的土,
是啊,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牙齿间的沙,
我们踩它、嚼它、践踏它,
什么东西也不能把它混杂。
可是,当我们躺在它的怀抱里,我们就变成了它,
因此,我们才如此自然地把它称为自己的家。
因为她生活在故乡的泥土中,所以她不但与俄罗斯人民一起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共同受苦,还和俄罗斯人民在抵抗纳粹侵略的卫国战争中共同奋斗。
在列宁格勒的围城战中,她透过录音,向列宁格勒的民众广播,要大家坚定地保卫列宁格勒。她和普通妇女一般,手上提着防毒面具,身背小挎包,站在住屋的大门口值勤。她写了许多爱国诗歌,包括当年传诵一时的四行《宣誓》:
今天和恋人告别的少女,
也愿把痛苦化为力量。
我们面对儿女,面对祖坟宣誓。
谁也不能迫使我们投降。
她的这种爱国热情,在本书所选的三组战争诗中很容易看得出来,这里就不再多举例子了。
经历了三十年代末的弥漫全国的恐怖大清洗,经历了四十年代初的全民热血参与的卫国战争,始终和自己的祖国站在一起的阿赫马托娃,终于把她深邃的历史眼光锻炼成熟了,于是开始写作她的抒情史诗《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这部耗去她最后二十多年光阴的、不断修改的长篇诗歌,就成为了她一生苦难和创作的桂冠。
我已经把《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仔细读了三遍,坦白讲,并没有完全读懂。乌兰汗先生在译诗中加了不少注解,又在译后记中对此诗提供相当详细的解说,对我帮助不少。我又参考了其他资料,才算勉强掌握了全诗的结构和用意之所在。一般认为阿赫马托娃是个杰出的抒情诗人,但苏联著名评论家楚科夫斯基却说,她是一个历史画的大师。从《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来看,确实如此。阿赫马托娃选取了三个时间点:一九一三年旧俄罗斯帝国即将崩溃的前夕、斯大林恐怖统治的高峰期、苏联卫国战争从最艰固的阶段即将转入反攻的关键时刻,她用这三个历史的重要关头,写出了一首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史诗,并把自己的一生织入其中,形成历史剧变和个人命运紧密结合的大叙事诗。这么宏大的企图,在二十世纪重视个人内心世界的诗歌创作中是难得一见的。
《安魂曲》书影我们可以说,因为阿赫马托娃始终坚持站在祖国的大地,和祖国人民同其命运,她才能时时刻刻站在历史的洪流中。当然,被这个洪流冲着走,她的一生也就充满了苦难,但也因此,她才真正地认识到、体会到二十世纪的人类命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才能写出这么了不起的作品。如果不怕女性主义者责骂,我们还可以说,这样的作品由一个女性来完成,只能令人更加尊敬和赞叹。
但是,这样说,也还只是涉及阿赫马托娃叙事的大架构是如何完成的层面,还不足以呈现她的诗歌的感人的气质。这种气质,主要还是来自她独特的抒情性。试看《野蔷薇花开了》组诗的第三节“梦中”:
我和你一样承担着
黑色的永世别离。
哭泣有何益?还是把手伸给我,
答应我,你还会来到梦里。
我和你,如同山峦和山峦……
在人世间不会再团聚。
但愿子夜时分,你能够穿过星群
把问候向我传递。
独立来看这一节,这是暗含了某种情节、某种戏剧性的抒情诗。也许,诗人和她的情人因为政治理念不得不分手,一个留在国内,一个流亡国外,从此天涯海角,永不相见─或者,只能在梦中相见。作者的语调极富悲剧性:你和我“一样承担着”“黑色的永世别离”,我们都是历史造化的牺牲者,然而,我们不得不如此。这就是历史的悲剧,这许许多多的历史造成的个人小悲剧,合起来就是一个历史的大悲剧。它写的既是个人,又是集体,既是俄罗斯,又是二十世纪的所有人类,因为这正是二十世纪历史的主流─人类大冲突、大断裂的时代。因为这样,这个历史是没有“英雄人物”的,它涉及每个个人,同时,也可以说,每个平凡人都是“英雄人物”,都是“主人公”(主角)。所以,我们可以说,阿赫马托娃不只是二十世纪俄罗斯的史诗作者,因为她的诗涉及了二十世纪的全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讲,她才是最具代表性的二十世纪的伟大诗人。请看《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的最后一节:
卡马河就在我的面前
上了冻,结了冰,
有人问一句“你去何方?”
不待我动一下嘴唇,
疯狂的乌拉尔就震动了
条条隧道,座座桥梁。
一条道路为我展现,
多少人沿它走去未返,
儿子也是顺着这条大道被带走,
在西伯利亚大地上
在威严而又水晶般的寂静中
这条殉葬的路途遥远。
俄罗斯为死亡的恐怖所袭击,
知道复仇的时期,
她垂下干枯的眼睛,
将双唇紧闭,她从我的面前,
向东方走去。
乌兰汗在译后记说,诗人以交叉的手法既写了未来,又回忆了过去。疏散,去乌拉尔,去塔什干,去西伯利亚。面对着西伯利亚历尽沧桑的茫茫大路,诗人发出无限的感慨。她说:“多少人沿着它走去未返”。短短的一句话中包含着说不尽的内容,但诗人没有讲具体历史事件,如十二月党人被流放,俄国革命者服刑,红军到前线打击外国武装干涉者,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时被冤枉的忠诚干部押往集中营,包括她儿子被流放,都走过这条道路。现在她还走这条路,但历史却完全不同,旧的俄罗斯已经死亡,祖国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即将获得新生,她也在长期的苦难之后,看到未来的希望。这一节诗可以说是历史命运与个人命运完全交融的最佳例证,充分显现了阿赫马托娃深刻的历史感受。
因此,我建议,阅读本书,可以先读《安魂曲》、战争组诗,再读其他组诗,最后读《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这样,最终就可了解《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为什么被视为阿赫马托娃一生的最高杰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从各种数据知道阿赫马托娃的代表作是《安魂曲》和《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我买了不少苏联诗歌的译本,却难得看到《安魂曲》的全译本,而且完全看不到任何《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的片断译文。二〇〇七年,我买到乌兰汗两卷本的《俄罗斯文学肖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惊喜地发现,其中的诗歌卷就包含了《安魂曲》的全译本,和安娜马托娃的许多短篇抒情诗。
正如前文所说,我读了这个译本,才知道阿赫马托娃是个伟大的诗人。遗憾的是,乌兰汗在阿赫马托娃的简介中说,他已译了《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但一时找不到译稿,只好“俟之他日”了,真是让我大失所望。二〇〇九年春天,我意外认识了大陆俄罗斯诗歌翻译家谷羽先生,他从大陆来台北,在中国文化大学任客座教授。透过谷羽先生的介绍,竟然能够和乌兰汗先生联络,并承他同意,把《安魂曲》、《没有英雄人物的主人公》及阿赫马托娃其他长诗,合编在一起出版,真是感到无上的光荣。乌兰汗先生的译文,从前面所引诸例,就可看出其水平,不需要我来赞美。在这里,谨向他致上崇高的敬意,与诚挚的谢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