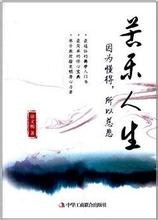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有时候别无选择,只好让他作品里的主角死掉,因为他们死了,才能取得发言的正当性。例如,文豪雨果无疑是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但却不是无条件的支持,大革命时没落贵族,甚至在道德极端主义挂帅下也杀死同志,使他很有意见。于是,在他描写法国大革命的杰作《一七九三年》里,他还设定了这几个主角:
——一个是保皇党的将军朗德纳克侯爵,他能征善战,打仗时绝不手软,但有次他被革命党追击,他已从古堡中逃掉了,古堡着火燃烧,有3个小孩被困火堆中呼救,于是他又折回火救小孩,结果他被革命党俘辱。
——当地革命党最高的司令官郭文乃是个子爵,他是朗德纳克侯爵的侄子,他虽然也是贵族,但忠于共和政府,而且也战功彪炳。他看到侯爵为了救3个小孩而宁愿自己被捕处死这一幕而深受感动,认为“在革命之上,还有人的无限仁惑”,于是他私下将侯爵释放,将自己关起来请罪。
——在司令之上,有个更高阶的执政公安委员会代表西摩达因,西摩达因出身农夫及牧师,还做过郭文的家教老师,他不得不判郭文死罪,但就在郭文上断头台的同时,西摩达因这个革命家也击枪自尽。
《一七九三年》这部著作,将郭文子爵及西摩达因这两个杰出的革命家都安排了死亡的下场,其实这部小说里他们还真的非死不可,因为只有他们死亡,他们两人那种高尚的人道含义才得以凸显。在小说里,主角的死亡乃是他们取得发言地位的契机。
不久前,阿尔及利亚裔法国籍作家雅斯米纳·卡黛哈(Yasmina Khadra)写了一部讨论恐怖主义的小说《攻击》。一个出身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医生,他表现优异,进入了以色列人的主流社会,成为了特拉维夫医院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有一天特拉维夫发生恐怖攻击事件,他还参加了抢救。但过后警方才通知他,那个炸弹客乃是他挚爱的妻子。由于他们夫妇都已进入了主流社会,他根本不相信妻子会去做炸弹客,一定是受到什么人的蛊惑,于是他遂展开了他的追踪之旅,他一步步深入,对自己族人的悲惨命运了解愈来愈深入,最后终于明白了他的妻子好日子不过,却宁愿去当个牺牲自己也要炸死别人的自杀炸弹客的原因。最后这个医生躬逢其会地参加了以色列杰宁的巴勒斯坦人宗教集会,当时发生了所谓的“杰宁大屠杀”。以色列出动武装直升机、以飞弹火箭攻击群众,医生也死了。
《攻击》这部小说,乃是探索恐怖主义炸弹客心路历程的作品。卡黛哈如果不把主角医生安排成死亡,这本著作一定会被抨击为是在替恐怖主义张目。只有将他安排成死亡,人们才会以怜悯之心去看待恐怖主义的来龙去脉。
因此,在小说叙述上,让主角死掉是有意义的,让主角死掉,人们的怜悯心才会被激发,这个怜悯心等于替已死的主角搭建起了说话的平台。怜悯是死者才会有的特权,它帮助死的人占住了发言位置。
而这种小说中的叙述策略,在真正的现实里亦然。历史上有些重要人物,正是因为他们的死亡才能够成为伟大的明星。切·格瓦拉因为死亡才得以不朽。基于同理,美国将本·拉丹杀掉,他们以为除掉了心腹大患,殊不知由此一来等于帮助本·拉丹取得了不朽的受难名声,本·拉丹从此进入历史,变成了一个记号。本·拉丹在活着时打不过美国的卫星和特种海豹部队,但这场仗在他死后还会一直打下去,美国可以赢得今天,但未必会赢得永远。死亡对有种人不是生命的结束,反而是生命转个弯又活了回来,而且活到永远。
1967年美国及玻利维亚特种部队俘虏了切·格瓦拉这个当年的头号公敌,他们决定“这个人不可以让他活着,他必须立刻死亡消失”,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就把他乱枪射死,今天美国又以同样的理由将本·拉丹打死,美国不知道,它们其实是培植了一个永远的对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