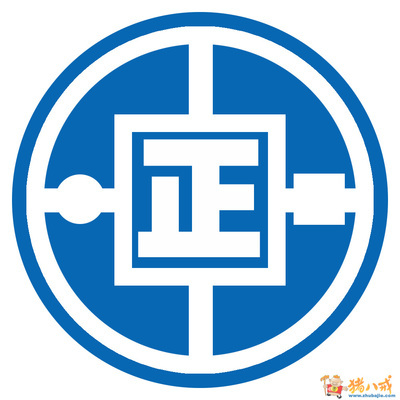图片来自网络
选自隐语(微信号:yintalking)
本文已取得隐语授权
文丨江隐龙
自从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引发“白话文运动”之后,近代中国人已经渐渐失去了古汉语的语境,而诸如黄遵宪提倡的“我手写我口”等诗歌通俗化的运动,又反复清洗着普通人对于古典诗词的热爱,极大的消退了适合中国风生根发芽的土壤。虽然有抗日时期短暂的中兴以及一批老派革命领袖的偏爱,但古典诗词终于在文革前后被列入“四旧”,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古典诗词才渐渐从绝境中走出。只是,此一时彼一时,中国人从语句词汇、表达方式到逻辑思维都已经不再适合古典诗词的写作,尽管在思想相对解放之后,诗词依然成为人们很重要的一种文化需求。
有需求自然就会有供应,文化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经济。然而缺乏了足够的底蕴与手法,怎样多快好省地制造大量中国风的文化产品呢?一个捷径便是用典。在一句平常的句子中夹杂大量常出现于古典诗词的词汇,便可以强行营造出“古典”,如若词作者的文字功底不差,一首中国风歌词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创作出来。
比如方文山入选高考考题的名曲《青花瓷》:
总体来说,这几句歌词都是非常简单且逻辑性不强的白描手法。素胚,笔锋,牡丹,檀香,宣纸,走笔,这一系列中国元素被简单罗列在四名歌词中,如同将一件精心准备但并不合身的汉服强行套在了“一如你”三个字身上。如果所有的文字通通都罗列古文,那整首歌将会非常不接地气,而方文山的常用手法便是用“我”、“你”或“谁”这几个富有现代气息又非常有代入感的人称代词拉近观众与作品的距离。这样的例子很多:
方文山绝大部分中国风歌词的套路几乎都同此理:以古典词汇的罗列形成中国风的“气场”,而后用人称代词点题引入故事(主要是爱情故事),之后便依据歌曲的主题继续罗列,只要词汇量足够,写出来的词便容易自洽——显然,方文山是一个非常善用词汇的人。
而这种词汇的堆积,正是最浅显的“用典”。当然,还没到引用典故的深度,只是在现代语境下引用古代的人与事:现代人用电脑码邮件,歌词里的人就用毛笔宣纸再鱼雁传书;现代人抬头看灰机灰过,歌词里人的便仰首月正明听老树昏鸦。因为观众的平均古典文学水平大为下降,所以不需要用深典,仅用词汇便足以营造中国风。
方文山通过《东风破》打开了中国之后,一时间整个华语乐坛都坐不住了,于是有了SHE《长相思》中直接引入李清照《声声慢》作为RAP词,有了林俊杰的《江南》TANK的《三国恋》以及后弦《苏州城外的微笑》等一大波中国风。抛开《长相思》的“拿来主义”不谈,这些歌曲的“古典词汇罗列+人称代词”模式几乎如出一辙:
并不是说这些中国风的歌词是抄袭,只是方文山已经建立了一个极致的模式,想另辟蹊径翻越,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同时,精致的诗词曲赋已经被唐宋文人写完了,从元朝到共和国的作者一样也很难翻越李白杜甫这两座大山,便同此理。可惜的是,《东风破》之后,方文山自己几乎没有能力写出更好的作品,而其它中国风词作者的水准,却几近一蟹不如一蟹。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很多,登上春晚舞台、由郭敬明操刀的《蜀绣》就是其中一例。
△李宇春与《蜀绣》有着奇妙的自洽感
这段歌词,与方文山流相同的是大量古典词汇的罗列,不同的是长时间没有出现人称代词,直到最后,用古意更浓一点的“伊”代替了“她”。这样的词是好还是不好?
可以说,方文山的写法不是圭臬,但郭敬明的词比起方文山开创的“古典词汇罗列+人称代词”模式无疑是一种退步。大量空洞而繁华的古典词汇可以在外行人眼中缔造出错乱的古意,但完全无利于歌词情节的推动;诸如“羽毛扇”、“红酥手”等作为典故看似比词汇更难,但与主题无关,属于纯粹为用典而用典,等同于“装逼”。
后弦的歌词也未见深刻。比如《西厢》中的“写下当年的你的我,水调歌头词一首。”这其中的“水调歌头”,未见其用典之意,几乎可以断定只是因为“水调歌头”作为词牌比较出名;否则此情此景,至少“雨霖铃”或是“钗头凤”都比“水调歌头”的意向为佳。
至于伊能静的《念奴娇》,“美人如此多娇,英雄连江山都不要,一颦一语如此温柔妖娇,再美的江山都比不上红颜一笑”之语,简直令人不知所云,其艺术价值更在《西厢》诸曲之下了。
后又有理科生用代码算出了《全宋词》中的99个高频词汇,极大促进了古典词汇罗列的流水作业进程,只要代入相应数列,就能自动生成“宋词”——比如《清平乐·圆周率》:
如此词文,倒打不了真正宋词的脸,却一定能打《蜀绣》之流的脸。
这不是郭敬明、后弦、伊能静等人的过错,方文山自己的败笔也不少,比如为林俊杰写的《醉赤壁》:“你那千年眼神,是我醉醉坠入赤壁的伤痕”,或是为刀郎写的《大敦煌》:“我用佛的大藏经念你的名……我用菩萨说法图为你演出……我用飞天的壁画描你的发”,这样的水准只能用五个字来形容:
强行中国风。
事实上,作为中国风歌曲中里程碑式的《东风破》,是颇有可圈可点之处的。《东风破》的叙事相对完整,其中的寂寞离合之感通过“犹记得那年我们都还很年幼”、“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等词句的烘托让人感到自然朴实。虽然名为中国风,但《东风破》并没有太多刻意引用古典词汇的手法,偶然出现的“酒暖回忆思念瘦”中的“瘦”字或化典于李清照的三瘦之语,尤其显出笔力。这样的中国风,以故事为核心,借中国风叙事,笔法自然——或许也是因为《叶惠美》筹备时,方文山对中国风也只是偶然为之,并不指望能火;心态平和,笔法自然也如行云流水了。
如果不算那一个“瘦”字,《东风破》的用典程序也仅仅在于古典词汇的引用,但此词却意境幽婉不俗,这源于其手法已经达到了用典的高度,便是“水中着盐,饮水乃知其味”。南宋的魏庆之曾编有《诗人玉屑》一书,对用典之事云:
《石林诗话》中亦言:
所言之意,便是写诗,不能刻意用典,实在要用,也要用得别人看不出来。回过头看看方文山所写的“大藏经”、“菩萨说法”、“飞天的壁画”之词,实在是大红补丁,不值一看。
自古以来的一切音乐歌曲,最初是随口唱出一时的思想情感,腔调并未定型;后来腔调统一成格律,便成了词曲。后有文人配合此曲填词,一曲多词的情况便出现了——宋词的发展便由此而来。清代戏曲作家方成培于《香研居词麈》中言:“古人缘诗而作乐,今人倚调以填词”,大体上符合中国古典诗词发展的趋势。周杰伦与方文山之间的配合,除《发如雪》外均是先有周杰伦之曲后有方文山之词,也便是此理。
有趣的是,性情如周杰伦,在其《红模仿》一曲中自己写道:
在探索中国风歌词的路上,方文山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所创的“古典词汇罗列+人称代词”模式,事实上是以白描打底,以人称代词点睛,使得歌词可以迅速“古今合一”。不过,如此浅层次的用典能将中国风推动到何方,的确是个疑问;如果用典始终只是为了烘托环境,那歌曲也很难有更深层次的内涵。
古人喜用典,有时不仅仅为了表达上的含蓄,也有政治上的因素。南宋洪迈于《容斋随笔》中说过一段话:
说到底,诗以言志,中国风歌曲不可能也不应当一直徘徊在儿女情怀之中,而缺失了更高的追寻。但是,并不代表郭敬明的《蜀绣》之流就应当遭受鄙夷——说到底,观众不能以一个文人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商人。畅销书作者的文风不是自己决定的,而是愿意花钱的读者的平均水平决定的,在经商之余,作者能创作出一些好作品便是好事,创造不出也决不能苛责,毕竟他没有提高大众审美水平的义务。
中国风歌曲的提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是一件好事。如果又一对李白杜甫成型了,后人要怎么去写呢?
关于世界万物的文艺百科不全指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