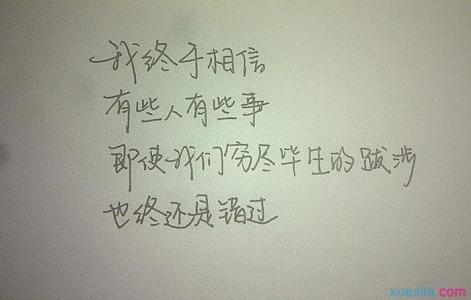终于看完了《萨摩亚人的成年》,读了译序,初版序,再版序,一至五章,九,十,十一,十三,十四章,以及附录一至五。

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萨摩亚人生活全景图,尽管她的研究对象集中于青春期的少女身上。米德试图寻找到一个反例来验证,当代西方社会青少年的叛逆,烦躁完全是文化性的因素,也就是试图将生物性因素从青少年叛逆的研究当中清除出去。而最终米德也成功找到了这样一个反例,即萨摩亚人的青少年期。
从个人的理解出发,我一直在试图为萨摩亚人寻找着可能的辩解。因为我难以想象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能够和社会性自由不发生冲突,所以我猜测所谓的性自由是否是指亲吻,拥抱,或者其他肢体的亲密动作,但不包括性交?否则,一个性自由的社会,为什么米德却甚少提到性自由有可能所带来的一些现实又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孤儿泛滥,比如性病传播,亦或是其他。这些问题是不存在?还是米德有意隐藏了?虽然后者的可能性并不大。再如,同性恋能够和基督教信仰不发生冲突,我为此寻求的辩解是,所谓的同性恋,大概应该是指同性年轻人之间为了寻求性渴望上的满足,而互相进行的一些手淫。抑或米德指的就是同性之间的爱慕和依恋,如果却是如此的话,从米德在附录中所提供的数据来看,同性恋在年轻人中的比例如此之大,但就上述这两点,就足以带给萨摩亚人社会毁灭性的灾难。
但为什么萨摩亚人依旧能够如此安逸,似乎没有什么挫折的存在呢?我猜测,是否他们的这一切和他们的文化是相配套的?萨摩亚人随性,自然,从来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情感需要,或者情感追求。无论是对什么事物都是如此,包括对生和死的观念。夫妻二人不是因为产生了强烈的爱情而在结婚,人们也不会为了什么名利或地位就拼命竞争。用一个直白一些的词讲,就是一个无欲无求的民族,包括对生死也是无欲无求,因为他们认为死亡不过是顺天命罢了。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这两件事是不矛盾的。米德说,我们必须把萨摩亚人缺少深情厚爱这一情形作为所有解释的第一条,因为他们对那种情景早已习以为常,以至于这种习惯已经成为他们人生态度中的基本成份-p136。接着这句话往下讲,我觉得,这种习惯也已经成为了他们文化中的基本成份。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性也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在他们的思维当中,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了。快乐,温和,随性,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萨摩亚社会的单元化使得他们在履行上述这一文化的时候,不会遇见什么阻力,“无欲无求”的社会,也不会因为某个职位拥有特别的待遇和权力,于是人们就拼了老命的争取。米德所说的“缺少深情厚爱”,应该是包括了爱情,亲情,也包括了对利益,权力的“爱”。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可以很容易的遇见他的未来,就是几乎没有发展的原地踏步。从这个角度讲,西方社会的复杂,所带来的人们不论是积极或者消极的竞争,确实成为了一个良好的推动力,推动着这个社会滚滚向前。
萨摩亚人因为从童年时代开始就目睹了各样的性交,分娩,死亡,因此在他们的思维当中,这一切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我们却选择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向他们隐藏了这一切我们认为是肮脏与可怖的事情。我们还堂而皇之的冠以被隐藏这一切的孩子的年龄段一个好听的名字——“童年期”,与之相对的就有“成年期”,中间衔接过渡的就是“青少年期”了。在青少年时期,孩子们开始接触成年世界当中所谓的“肮脏”的事物,包括性,权力交易,等等。在一切的不适和冲击中,叛逆与反抗自然的形成了。他们一面发现世界不再是小时候的那样美好,一面却蠢蠢欲动的试图成为这个新世界的一员,用他们幼稚又冲动的意识评价身边的一切,并为此作出“孩子气”的反应。这是我们这个多元化,并且极复杂的社会所形成的一种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只适合于我们这个现代社会,它能够帮助孩子在这个现代世界当中找到立足之地,并灵活应对各样社会事务,却一点也不适合与萨摩亚人的社会,就像萨摩亚人的教育方式一点也不适合于现代社会一样。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又一次回到了普同论的观点上,没有绝对的“好”的文化供我们选择。
萨摩亚人有他们的放纵,私欲,一切关于人类本来属性中的罪恶,他们也不是没有,只不过他们的社会简单宽松,随性自由,因此诸如嫉妒,纷争,仇恨一类的恶被大大的弱化了而已,但是另一方面关于对长辈的尊敬,对性的操守也随着宽松的文化而显得令人刺眼。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强大的道德伦理下所约束的各样道德操守,如果我们再能够少一些为了竞争与生存所带来的仇恨,那我们的世界,岂不会是更美好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