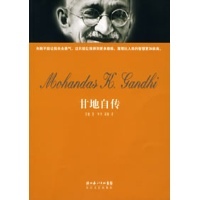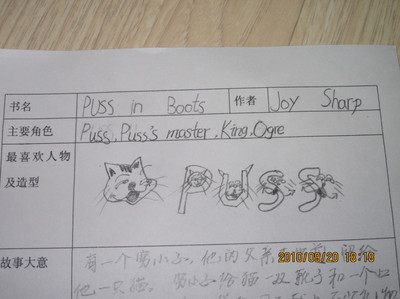《归去来兮》这书描述了这样的玉米地,这样的阡陌纵横,这样的鸡犬相闻,在另外的眼睛里,寻常得无法不忽略,普通得不足挂齿。然而对于我,十八岁前所司空见惯的草木虫鱼,隔了十多年的距离再来看时,觉得处处都给人愉悦、欣喜。且不必说青山如黛,且不必说绿水悠悠,即使是扶锄而过的老者,即使是浸润着泥土味道的晚风,都似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之感。
附近的房屋疏疏落落,待学生作鸟兽一般的散尽,便有曲尽人终,万籁俱寂的感觉了。我极少听歌,如果听,大多数时候便是红楼梦的主题曲,一遍遍的,似乎是无休无止的循环往复的放下去,仿佛一个失恋人的倾诉和发泄。事实上,我的心中是无所谓欢喜忧愁的,我只是愿意在这样安静的地方听这样干净的声音罢了。在悲剧美与喜剧美的比较与选择中,我更愿意让前者来打动我。
夕阳从此山坡滑到彼山坡,复制出千年前的名句“草色山光残照里”,也复制出“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它不惊心动魄,但是容易令人触景生情,起兴衰之感,发浮萍之叹。我很想在任何一条小路上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走下去,很想有人同行,戏说一段悲欢离合,八卦一些爱恨情仇。忆及当初,高中时代尚有铿锵三人行,每天起早贪黑披星戴月。流转长沙时也有算有个环肥燕瘦的组合,磕瓜子吃麻辣从不寂寞。再后来做了深圳游子,千里之外居然也能够延续童年的缘分,彼此一个晚上在一起,一句话不说也不觉得尴尬。而现在我是彻底的落了单。劳燕分飞像一个一定会发生的定律,无论我怎么回首,那人再也不会在灯火阑珊处。
我所可恨的,这一辈子文不文武不武也就罢了,如何弄得个琴棋书画诗酒茶一样不通,人生一晃若许年,我记不清我都干什么去了。倘若能在晚风中弄几声横笛,拉一段二泉映月,画几枝疏影横斜,该是多么修身养性的事。而我,搬一把椅子,沐天地之清风,除了吃还是吃罢了。大观园中众姑娘芦雪庵烧鹿肉,林黛玉认为该为芦雪庵遭此大劫一哭。倘若她遇上我,又该为这夕阳野色一哭了。
传说中有很多同行奋斗在进城的路上,而我的理想,则是将这回家十五分钟的车程变为回家五分钟的步程,因为等公交车始终是件很麻烦事,除此之外,再没有更高刻度的追求。倘若不能,便安安生生的受用这阳光,这雨露,这鸟倦飞而知还的黄昏,在粉嫩的天真的脸的包围中老去,想来这样的生活也不输给城市繁华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