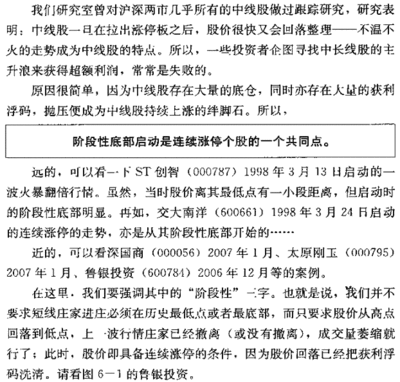再也不能继续“马大哈”下去
说中国文化是“马大哈文化”,似乎说不过去,但要说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习惯于马大哈,则不算过分。中国人的“马大哈”习惯从一些词语和俗语上可见一斑,比如:“差不多”、“就这样”、“拉倒”、“大概其”、“点到为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马大哈”这个词,我理解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和嘻嘻哈哈的组合。
“马大哈”一词到底产生于何年月,或不可考,我确也没考证,但至少不会与中华文明同寿。中国古代文化还是颇为严谨的,很多经典中不少提法是非常负责的。比如,我所知的中国最早的教材《尚书》在其《大禹谟》篇中就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认为人心高深莫测,管理思想就得精微,必须精细和专注,执行要尺度适中。这就已经是精细化管理思想的雏形了。就这段话曾国藩在《与弟书》中有深刻的解读:“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做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做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再看《论语·宪问》:“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说的是文件的形成要严肃认真,裨谌起草文件,世叔组织讨论,再让子羽作修订,然后才由子产进行文字润色。这很像一份现代企业管理的流程。我也曾在一处旧时的县衙门上看到一副对联:“为士为农有暇各勤尔业,或工或商无事休进此门。”这不就是典型的岗位管理语言吗?
那个时候,人们做事,也往往是很讲究细节的,是非常较真的。曾经读到一首诗,是明朝初期的翰林院老书生钱宰散朝回家吟诵的:“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谁知,儒生钱宰诵诗的事被皇帝朱元璋知道了,次日上朝时,皇帝主动提及此诗,说你昨天做的诗好啊,不过,我并没有 “嫌”你上朝迟到呀,何不改为“忧”呢?你自己对工作负责,总是担心晚到嘛。钱宰吓得一个劲儿地磕头。那个时候正大兴“文字狱”,而且锦衣卫、东西厂特务神出鬼没,一不谨慎,丢了脑袋还不知祸从何来啊。
《韩非子·二柄第七》讲了另一个关于制度执行的故事,说韩昭侯醉了倒头便睡,手下人担心他着凉,就给他披了件衣服。韩昭侯酒醒了看到身上的衣服很高兴,问左右:“谁给我加的衣服?”手下回答:“管您戴帽的官。”结果管戴帽和管穿衣的官两个都受处分了,理由是管穿衣的失职,但管戴帽的越权。还声称,宁愿受冻,也不能培养官员不行职责和超越职责的行为。此事的真实性我一直怀疑,但管理的理念很多现代人也赶不上。
遗憾的是,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和官员总体来说是不太愿意去研究管理学的。我曾写过《中国古代没有管理学》,承认有管理实践,却并无系统研究,即使涉及与管理紧密相关的内容,也仅局限于人力资源。正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所言:“中国人的心思聪明恰没有用在生产上。数千年知识学问之累积,皆在人事一方面,而缺乏自然之研究。殖产营利,尤为读书人所不道。”
近百年形势就更不乐观,不仅不研究做事,反而更加不讲究事物本身的科学性,效果之糟糕自然可想而知。记得1958年夏天,河北省一个普通县徐水县竟办起了一个拥有12个系的综合大学,县下每个公社都有一个“红专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群学生加上几个青年教师,仅花35天就写出一部78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清华大学几个月内就编出了95部各种教材与专著,其中《水工概论》、《农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测量》、《工程水文学》、《水工量测及模型试验》是10天工夫写出来的。(见张鸣著《历史的坏脾气》)
这两年,在四川灾后重建的问题上,“三年灾后重建,争取两年实现”本是高层领导急切心情下的期望,最终却成了基层的军令状。这和上面快速编书的荒唐,无非“五十步笑百步”。
正因为这样,我每次在饭店吃早点,看到点心牌上,最差的点心是“一级点心”,稍好一点的是“特级点心”,更好一点的是“超级点心”,最高档次的则名之为“顶级点心”,就觉得不得劲。联想到过去的一、二、三等奖分别升格为“一等奖”、“特等奖”和“最高奖”,教人怎能不为世风日下而忧心?
奇怪的是,我们在官场看到很多事情却是完全符合精细化的,比如领导的接待,桌上的茶杯要拉线摆齐不说,连到哪个路口接车,席位牌怎么摆,谁站在哪个台阶上去握手,那是精细得不得了啊!所以,中国人看到奥巴马一干人在会议室观看击毙拉登的录像时的“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就五味杂陈。据说湖南一位姜姓副市长发明了一套极为精细的签名规则:如果字是横着签的可以搁着不办,竖着签的要“一办到底”,在“同意”后面是一个实心句号必须“全心全意”办成,点的是一个空心句号百分之百是“签了字也是空的”。只能用一句话概括:机关算尽。
本该较真的却并不当回事。比如,香港财政司的财政预算一旦制定立即挂到网上,预算支出情况常常多达数百页,细致记载各部门收支,连一张公务用纸、一张办公桌、一把办公椅都要做到有案可据,还会公布办公电话,随时接听民众的质询。但我们却找各种理由不公布,不得已公布了也语焉不详,“类”、“款”、“项”、 “目”四个级别的预算科目,多数仍停留在“类”上。一些严重超出预算的部门要将“三公消费”的真实数额在“其他行政经费支出”或“公共服务项目支出”中 “暗度陈仓”其实极为容易,外界也无法通过会计手段进行核实查证。
所以,在中国,绝大多数事情不存在能不能,主要是愿不愿。然而,愿不愿不是我等讨论的范畴,只是说说能不能,只涉及方法论。列三个小的例子在后,给有意愿者一些启发,因为中国实在不能再“马大哈”下去了。
日本人都熟悉一种沟通细则,叫HORENSO。HORENSO是三个词的合写,一是报告(Hohkoku),下级完成了的事即时反馈给直接上司,不用等上司来催问;二是联络(Renraku),平级间也需要通气,免得互不知情,妨碍配合;三是相谈(Sohclan),不仅要主动沟通,关联部门或岗位还需达成共识。这一点体现了日本人一贯的工作作风:“把屁大的事当天大的事做。”
德国的高速公路基本不收费,也不限速,有需要维修的地方即使限速也会一再给出指示牌:“限速多远?6公里。”“到一半了吗?还有4公里。”“马上结束了?还有3公里。” “究竟还有多远?1公里。”“谢谢您的理解,祝您一路平安!”这才是“为人民服务”啊。

中国近几年全民谈论食品安全。我们在欧洲看到人家鸡蛋是有“身份证号”的,如:1—DE—4315402,第一个数字“0”表示是绿色鸡蛋,“1”表示是露天饲养场放养的母鸡下的蛋,“2”表示是圈养的母鸡下的蛋,“3”则说明这是在笼子里饲养的生长环境最差的母鸡下的蛋;两个英文字母是鸡蛋出产国的标志,DE代表德国;第三部分数字是产蛋母鸡所在的养鸡场、鸡舍或鸡笼的编号。认真到这个程度,还需要在《新闻联播》里反复提醒消费者“谨防上当”么?
汪中求
2011年12月20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