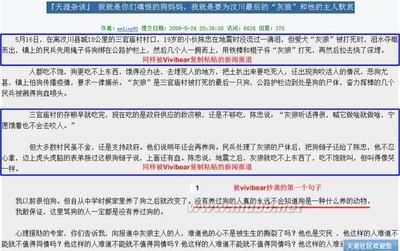并不是我们的爱,没有在思念里千锤百炼;也不是我们的情,无法流传千古永垂不朽。只是老两口的爱,粗枝大叶,柴米油盐,这些,我们不曾拥有。
北京这座城市,让我喜欢的理由不多,其中之一就是,这里可以满足吃货们日渐膨胀的食欲。你不必走遍大江南北,在街边,就可以找到各种地方小吃。
反正,他们的牌子上是这样写着的:山东杂粮煎饼、陕西肉夹馍、湖南苗家臭豆腐、湖北孝感米酒、东北正宗烤冷面……
我住北五环那会儿,每天下班,村口成排的地摊儿都会汇成一条小吃街。安全起见,我并不是每天都吃。和《生活大爆炸》里的谢耳朵他们一样,同事们通常把每周五下班后定为“消夜”,即供肠胃消遣放纵的夜晚,不撑不归。
某周五,和往常一样,我带着俩同事买地摊货,其余同事占座留守排档中。
整条街,最畅销的,当属臭豆腐和豆腐串。而客流量最多的,当属“舍得”——并不起眼的名字,也没打什么湖南湖北的招牌,可这家的东西,一吃起来,当地的风味异常浓郁。
这两个摊位其实是一家,老板炸臭豆腐,老板娘烫豆腐串。
听口音,老板是湖南湖北一带的,六十岁上下,暴脾气,什么事不顺心了就开始嘟囔,却从不和外人说一句话,客人惹恼了他,也顶多背地里骂上几句方言泄气。我算是这一带的常客,几乎和每个摊主都很熟,唯独他一个倔倔的,每每和他搭话,他从不理我。
老板娘看起来却和善许多,面带笑容,时不时和客人聊聊家常。每次我讲一些我们家乡那边的情况,她十分乐意听。有时她也会反问我一些问题,并和我分享一些她家的事情。她说,他们的女儿也在京城这边工作。
但就是这不惹人注目的名号、不搭边的老两口,竟组成了小吃街里最火爆的摊位。
日暮而至,披星而归,两人总是各忙各的,很少聊闲话。一直怀疑,除了生计的事,他们靠什么维系感情。
今日刚巧夏至。夏天一到,排队的客人就开始多了。
天热气燥,排队之际,不巧老板的暴脾气又发作了。他动作娴熟地炸着豆腐块,急切和愤怒全写在脸上。
老板娘还是和颜悦色,一手烫串进方锅,一手收钱放腰包,一边微笑着和客人聊天,时不时还插句关于女儿的话,一如既往。
客人的确多,老板娘这边零钱不够了,于是偷偷去老伴儿口袋里翻零钱,可一不小心,她的手腕碰到了老板的胳膊。
接下来自然是悲剧,刚刚盛好的臭豆腐和热汤汁洒在老板另一只手上,一点儿不剩。一瞬间,老板的手红了一大块,紧接着,一个大水泡就起来了。
“你在搞什么?”老板急了,冲着妻子劈头盖脸就是一句,“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回去!”
“别气了嘛。”老板娘脸红脖子粗,边说边去看老伴儿烫伤的手。
老板娘正试图缓和气氛,万万没想到,蹦出个不解风情的男子:“你俩要打回去打呗,我们还等着呢,快点儿啊!”
“看什么看,看了不也是烫了?”一股脑儿,老板把火全发到妻子身上了,本想推开妻子,没想到用力过猛,把妻子推了个踉跄。
再看妻子,手里正捧着一大桶凉水,本想替丈夫洗洗伤口,降降温度。这一推,水洒一地,有的还溅在顾客身上,周围怨声一片。
妻子连忙低头赔罪,可一转回身,一脚踩在洒了水的地上,本就没站稳的她,径直跌在地上,疼得站不起来。
顺着动静,赶来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议论声嘈杂不堪。
老板本想撂下手里的筷子,走过去扶起老伴儿,可一见周围人这么多,又碍于面子。于是他头也不抬地赶回摊子,随手抽出一张破报纸,简单擦了擦手上的油,便又继续翻腾起锅里的臭豆腐了。他嘴里依旧嘟囔着,尽管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老板娘见他走开,似乎也急了。缓了一会儿,她慢慢起身拍了拍裤子,回头把摊车推到一边,摘掉围裙径直离开。
夜幕下,人群散开,妻子远去,倔强的老头孤独地忙活着。
客人们心里想什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晓得。只觉得这事儿要搁在现在,女的要不闹个鸡犬不宁,全然对不起爹妈给的好身板。
想起前几个礼拜,有个同事,因为晚上洗澡,老公推门送浴巾的时候劲没用对,把她推倒了,结果跟老公大闹了一宿,第二天还在电话里跟老公掰扯不停。
又过去几天,本以为这事都消停了,谁知吃饭的时候,另一女子偏偏提起了这事。午饭过后,该同事越想越憋气,一怒之下竟闯进了老公的公司,当众拽他出来,叫他正式给自己赔礼道歉。
紧接着,男的也没惯着她,当晚也回闹到了老婆娘家,想讨个说法。一来二去,雪球越滚越大,最后两家老小倾巢出动调解,两人方才化干戈为玉帛。
本是小事一桩,非要折腾一番,对簿“公堂”才能了结,何必呢?要是这老两口回家以后纠结不清,也这么打起来,举目无亲,谁来劝解,谁又来调停?
想着想着,所有的东西都买完了,我正往回走,不经意间碰到了老板娘。她就坐在离摊位不远的大树下,瞅着老伴儿,哭成了石像。
我把东西递给朋友,想凑上前去,安慰她几句。
犹豫间,老板娘已经起身,使劲儿擦了擦眼泪,又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一路小跑,溜进了村里的小巷。
再等我们酒足饭饱,已将近半夜。放眼望去,小街一片狼藉,该撤的都撤了。
不远处,不知何时,老板娘已经回到了老伴儿身边。老两口正一搭一合,忙着收拾着自己的摊位。
路过他们,两个人已经收拾完坐下了,我也终于听见两人开口闲聊了。
“还生我气不?”妻子用胳膊肘轻轻碰一下老伴儿,嘴里不停地盘问着,“还疼不?”
“这小伤,算啥子嘛……这小伤,不算啥……”老板还是一句一句嘀咕着,“就是,挺急撒。那会儿,你跑掉。”
妻子说:“这几天,别往闺女那儿跑了。你这伤——”
老板连连应声答应:“嗯嗯嗯。要有东西,你自个儿送去得了。”
两个人紧挨着,面对面坐在街边的马路牙子上。老板一只手抬起,一只手放在大腿上,规规矩矩的。妻子正在替他包扎伤口,小心翼翼。
妻子一边包扎一边问:“疼不?”
丈夫一边咬牙一边答:“不疼!”
翻来覆去的两个字,不浪漫,也不奢华,倒是诠释了两人感情的全部。
路灯的灯光,径直打下来,把两个人的身影,拉得庄重。
绷带上渗出的紫药水,颜色和夜色一样浓。
行走世间,每个人都说自己不敢奢望,唯独想要一份深刻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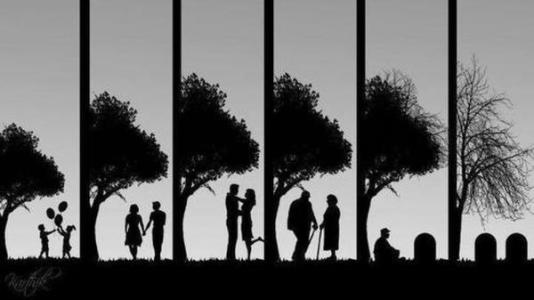
我一笑了之,不是不相信爱情,只是笑你,笑你那颗易碎的玻璃心。
我承认,我们爱得不够深刻。
并不是我们的爱,没有在思念里千锤百炼;也不是我们的情,无法流传千古永垂不朽。只是老两口的爱,粗枝大叶,柴米油盐,这些,我们不曾拥有。
那是岁月积攒的淡定、宽容与惯性,即便耗费整个青春的感情,我们恐怕也无法亲身感受。
只可惜,年少不经事的我们,还没等全部看透,就把共度余生的那个人,给弄丢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