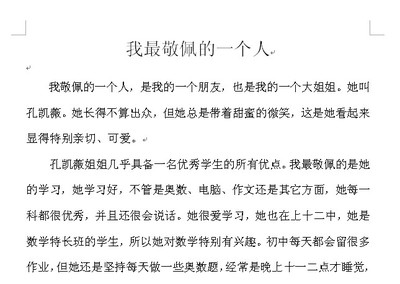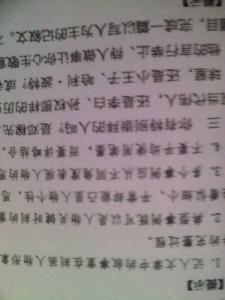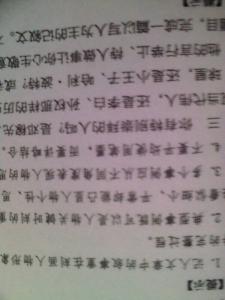半夜过了,凄凉的屋里没有声息,就象爱枯死在树枝上,在火热的炉膛里烘烤。是整夜的哭泣淹没了火热的音节,还是暴雨在檐前不住的淅沥。仿佛爱的悲切在无声的游走,神情象被爱带走,在泪痕历历中苍白得叫我无以自控。
无人相伴的感觉真是孤单,一个男子在如歌的放纵。那些伤感的煎熬一次比一次莽撞,我就象找不到目标的柴,在等待你烈火的烧燃。无眠的篝火在梦的四周熊熊燃烧,如你在篝火里劲舞,我象抱着夜的惨剧向你走来,在少年牧师的牵引下走入火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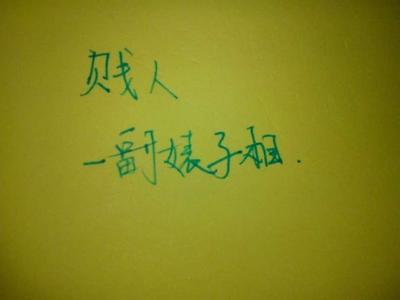
其实那个牧师就是我,我把爱的慈善都给了你,象我的伤苦在那火里烧灼。无度的节制叫我很为难,我把祈祷放在平面,用我的爱把你释怀,你把温情的宝物奉献出来。面对我站立的旗畔,你的爱象旌旗一样的摇摆,你象在一个男人的手里接过招展,还象美丽的维纳斯和梦中的安琪儿一样的抒怀。
朱丽叶和罗米欧的爱,就象在那一刻铺排,所有的对话都是真真切切,就象罗米欧说:“我愿意我是你的小鸟”朱丽叶回答说“蜜甜的,我也愿意。”爱呀?真的很甜,也很苦涩。
脱离了这个世界,人那?就不知道缥缈到何处?面对无助,仿佛一朵莲花似的云在拥着我,向你的美丽地方而去。我在荷塘月色里看到你,更深的意义,就是逼真。温柔的成色在象我靠近,我象在对月亮说着情话,还象冲着荷塘莲花叫唤你的名字,泪伤在眼窝里打转,象枯干枝条上的露,没有人认领。
浪花在如歌的梦里打颤,无形的捆绑叫我无法释怀。早晚的霞光我只能看到一半,就象诞生在那一刻投向难民。我说?天哪,这么多年我是怎么度过的,多亏了我的诗篇,给我加冕。我象半残的红叶飘摇在地,鸦影投入斜日的光圈。我象在静穆的黄昏里,拉链着那个彩画,在梦里如歌的想你。一年又一年,一月又一月的企盼,得到的都是如苦的黄连,只有自己吞咽。
我梦想清风吹露芦雪的酥胸,我在抚弄欢喜的流萤。即使笛韵听出凄凉的问候,我也象近水间断续的蛙鸣,在你芦梗的相思里鸣奏。
凌晨十二点,我象隔着龟背竹宽大的叶子想你,一只流萤在打扰了我的美梦。我象闭月羞花似的害羞,在你黑暗的掩护下,那一声紧似一声的呻吟,把龟背竹也羞臊得弯下了头。突然,还像有一只白蝴蝶飞出来,离开了那宽大的叶子,我看得很入神,就象一条白色爱的短信,飞向你的晴空。
我真渴望吻到你的热唇,可是那美丽的诗集还没有掀开,只有看到你的影像在我的诗里乱动,我狂热得不知写些什么和知心的话语,就闭塞得我哑口无言。
缓慢的车轮,驶进莫测的道路,得到的是阵阵袭来的昏眩,用一场爱情忘却所有的爱情,我是永远做不到的。犹豫的手指在象触摸短信的疼痛,想删除那些甜蜜的爱,也是不可能的。
你是我的必须,是我爱的拥有,我非得你所属,你是我最心疼和爱着的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