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一度是个活的很绝望的人。坚信上帝已死,人类无法被拯救。过于敏感的天性让我的身体和心灵如动物的触角那般敏锐深入并感知这世间的一切。我讨厌一切肤浅的快乐,简单的幸福,它们在我眼里都是那么的吹残可破,随时都可能被这世界的一丁点儿绝望瞬间摧毁。
我不喜欢正能量,不喜欢任何的至理名言,成功捷径。这些对我来说实属生活中最无趣的谎言,和生命的真相毫无关系。
有关生命的真相,有一个死了很久的人和我说:“你,就是真相,这个世界除了你没有别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是许多年之后的某个夜里突然想起这话,觉得挺有道理。我就是这样,始终记不住道理。那些每天滔滔不绝说道理的人在我看来都是那么虚弱。如坐在高级商务会所里大谈特谈人生之道的“成功人士”一样,他们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有人说:“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像一个能把美酒变成水的邪恶漏斗”我想,从某些角度来说,语言或许是最无力的存在吧!有关真相的所有表达都无法通过语言,通过语言我们只是能发声罢了。那些一直在谈道理的说话者,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呢?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内里爬满了虱子”我总是能透过那华美,看到那满是虱子的内里。也不知道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妈妈说作为一个女孩儿,我过于沉静了,世界不会喜欢的。我说我只是想更真实一点罢了,世界的沉重既然无法逃避,我为什么要假装轻松呢?轻松快乐有什么好呢?在伪善和恶之间,为什么不面对恶呢,它难道不是更接近真实吗,而伪善呢,充满媚俗且自欺的讨好罢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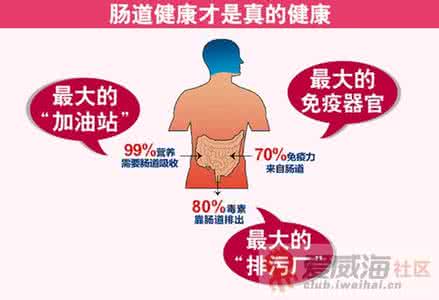
的确,人的一生会因为敏感、任性这样一些浓烈的品质而与生活碰撞得更多,更剧烈。我想我们的生命都太过于残缺了,我的敏感、沉重、不讨喜就是一直伴随着我的残缺!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似乎都在说“我是一个很乐观的女孩儿,和我待在一起很舒服,充满正能量。”这样的说法实属对我的“自我认知”莫大的嘲笑。谁不知,“正能量”这三个字是我多么忌讳的呢!我如何就从妈妈口中的“沉静”女孩一下子成了朋友口中的“轻松明朗”的存在呢?这个问题让我充满疑惑,难道我也开始“伪善”,开始假装幸福,练习微笑,无奈的斩断了自己那深入到黑暗里的触角了吗?仔细回忆过去,这些似乎都不曾发生。我还是那个喜欢真实的人,如一个带着厚重盔甲征战南北的士兵,义无反顾的投入到一场又一场关于真相探寻的厮杀中。而观战之人的感受竟然在这潜移默化中就此千差万别。这些于我而言都是始料未及的。
生命真的很漫长,很多事情我们唯有等待,比如我们要很久很久才能等来一份真爱,要很久很久才能与这个世界,与自己和谐相处。本性里的那些残缺让我们总想逃离,然而却又是这些残缺让我们成为最特殊的存在,无论沉重深刻也好,轻快活泼也罢,我只是在按自己的本性生活。对我而言,沉痛和轻快是一回事儿,都是附着于敏感本性的存在。如同廖一梅所说:“世界之大,你始终违反不了你的本性”。所以,我仍讨厌正能量,如果它试图杀死我的敏感!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