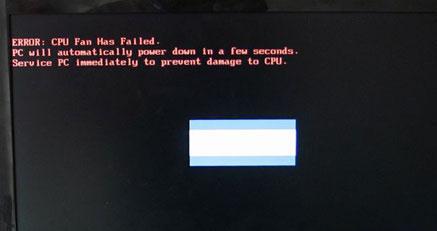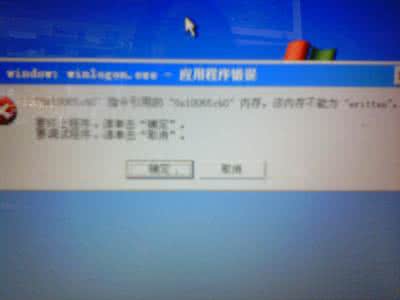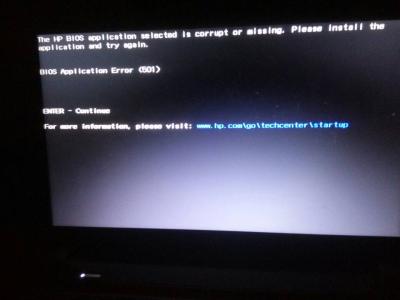宏
梦见20年前的你,很突然。
几个大男孩一摆溜儿勾肩搭背着。一袭的军大衣,一脸儿的桀骜与不屑。英姿勃勃,步态翩翩。经过,一如临风的玉树,美哉少年!
那个1米8个儿的,是你。侧头,斜眼,嘴角一抿一笑,带点儿色。进门,不“报告”,一声那尖利的口哨就先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亲密无隙。
我为师,然只长你们几岁。青春,就是一朵朵吐蕊绽瓣的花儿,明艳、恣意、傲慢,不在意别处风光与他人的揣想,自顾自地飞红溅香。那日月,同挽手并肩,共登高野餐,掏心掏肺地了然于义。
有一种磁吸并共振的感觉。一课余,都纷然约至,谈诗论文。www.250rz.com而你,不知从哪儿窃来的段子,一板三眼地打趣,一脸儿坏相。更记得那“结拜”:宛若真的回到了三国,四人举酒于缤纷的桃树下,你,摘了一枝桃花,豪气又潇洒。
也怄气来着,因我的恨铁不钢与你们的嬉皮笑脸。像车轮战,轮流与一个,或一个跟一伙。却又俨然骑着竹马过家家的娃儿,绷脸、掉头之后又是装鳖、抱团儿。你,最小,也最皮,一遇到类似龃龉,不是以小动作打哑谜,就是一股弯弯扭扭的腔调:干~嘛~呢?于是又亲又热了。似乎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不散不离不弃。
都是一群的傻,笑,却像一朵花。
又纯又痴又狂,惹来了多少个蜚短流长,眼红了躲在角落里的那个偷看的她。只因,当年都“18”,是兄弟,不负那情义年华。
琴
那是在一所中专任教。有美工、医护、写作共七专业,千十号人。我主讲新闻。而校琴室却是我心灵的寄居。
琴室百平米大,一排的砖木结构,孤立于诺大的操场的一角,像个别院。琴数十台,是幼师生必“工”的“利器”。除器乐课外,大多时候,琴室的黯然总与操场的空旷天然缄默着。
那时,我大学刚分配,一身的书卷气和浪漫的想象。可现实骨感——课时的负荷与期待,总使一些心绪纠结成水火,成风雷。不便书与言。
于是,琴,走进了情感。常常,歌谱、手抄本一摊,耸肩,仰头,轻重徐疾地运指,似乎风拂旷野、雨打芭蕉了,嘈嘈切切错错,强劲且浓烈。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回还”的决然与慨然。偶有小文发表了,也弹。那是“东风一夜花千树”的喜气,天高云淡,落英缤纷意竞千。似乎一个个音符、指法、音色都成了思想、感情、形象的附着物了;或,遥相的呼应。
初始,是门忘了上锁,我大摇大摆地去。可心曲激荡着,要,门却把了“将军”。这时,我不得不“贼”,打一虚掩的窗,跳进去。偶尔,会忘了带谱子,就想当然地去编。曲、词、弹、唱像根根带金丝线的银针,迸发、穿梭并刺绣,心闲手敏意远。欢欣时,轻快舒缓,活力溅射;伤心处,高亢激昂,梨花带雨。有回,一幼师女生问:啥歌?蛮好听哦。令我又多一“思”:歌者,心也。
好在,器乐、声乐师懂我,赠了一把琴室钥匙,还低下身段邀我“走市”。
“走市”是方圆一带的俚语,是说红白事的主家请锣鼓、歌舞、戏曲去扬威助兴的民团。去了,我吼得浑然自我、忘我、无我,颇具高原牧歌的风采。
可惜,这些埋藏心底的青春,醒来,也只是个突然的梦了,是消逝的电波。年关一梦,我瞟了一眼20年前的琴室。室内,我自如弹唱着,一如王。

 爱华网
爱华网